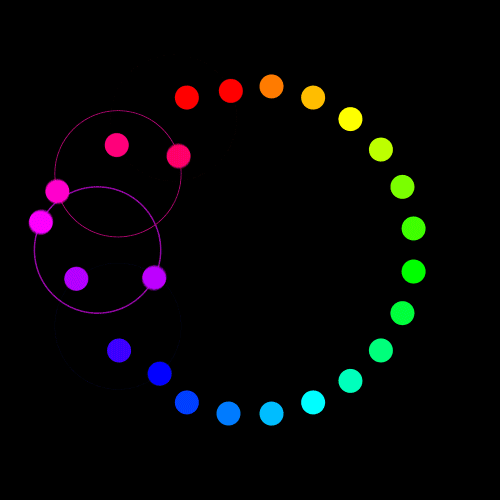简介
要是我真的疯了,也没什么,我不在乎。摩西·赫索格心里想。
有些人确实认为他疯了,他自己也有一阵子怀疑过他的精神是否还正常。而现在,他的举止虽然仍有点怪诞,可是他感到信心百倍,轻松愉快,身强力壮,而且自以为慧眼超群。他整天给天底下的每个人写信,已经入了迷。这种信他越写越来劲,因此自六月底以来,他无论跑到哪里,随身必定带着一只装满信件的手提旅行箱。他带着这只箱子,从纽约到玛莎葡萄园,但立刻又转了回来;两天后,他飞往芝加哥,接着又从芝加哥前往马萨诸塞州西部的一个乡村,然后就躲在那里发狂似地没完没了地写起信来。写给报章杂志,写给知名人士,写给亲戚朋友,最后居然给已经去世的人写起来,先是写给和自己有关的无名之辈,末了就写给那些作了古的大名鼎鼎的人物。
伯克夏一带正是盛夏季节。赫索格独自待在一幢老大的旧房子里。往常他十分讲究饮食,现在则靠啃光面包、罐头豆和干乳酪充饥。有时,他会跑到杂草丛生的花园里去采摘悬钩子,心不在焉地小心翼翼地把它们那长满刺的藤蔓牵起来。他睡的是一张没铺被单的床垫——这是他久已弃而不用的结婚时的床——有时他就裹着大衣睡在吊床上。花园里,四周围着他的是长得高高的杂草、刺槐,还有小枫树。晚上醒来睁开眼,只见点点星光近似鬼火。当然,那不过是些发光体,是些气体:无机物、热量、原子,但在一个清晨五点和衣躺在吊床上的人看来,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若遇心血来潮,突然想到什么新主意时,他就赶快跑到厨房——他的总部——去记下来。砖墙上的白漆已开始剥落,有时候,赫索格就用袖子抹去桌上老鼠咬下的碎屑,他不动声色地感到奇怪,野鼠怎么会对蜂蜡和石蜡这么感兴趣。凡是用石蜡封口的果酱瓶、蜜饯罐之类,都被它们咬得千疮百孔,生日用的蜡烛啃得只剩下烛芯。老鼠还光顾了一条面包,咬进一个洞,在里面留下自己的形状。赫索格涂上果酱,吃下了没有咬过的另外半条。他和老鼠也能分享食物了。
不管什么时候,他脑子里总有一角对外界敞开着。清晨,他听到乌鸦叫,觉得它们的聒噪十分悦耳。黄昏时,他听到的是画眉的啭啼。晚上则有猫头鹰的悲鸣。当他被脑子里的信弄得激动起来,走进庭园时,他会看到玫瑰花绕在水笕上,或者是看到桑树以及在它枝头使劲啄食的小鸟。白天,天气炎热,黄昏时红霞似火,四周灰蒙蒙的一片。他睁大眼睛放眼望去,什么也看不清,几疑自己已经半瞎了。
他的朋友——他过去的挚友,和他的妻子——他的前妻,曾对人散布谣言说,他的精神已经失常。这是真的吗?
他绕着这座空房子走了一圈,在一扇布满蜘蛛网的灰蒙蒙的窗子上,看到了自己的脸影。他看上去显得出奇地安详。一道光线从他的天庭,经过笔直的鼻子,照到他深沉宽厚的嘴唇上。
到春深时分,赫索格觉得再也受不了啦,他要进行解释,说出事情始末,要阐明自己的观点,为自己辩护,澄清事实真相,以正视听。
当时,他正在纽约一所夜校里给成年人上课。四月间,他的课讲得头头是道,条理分明,可是到了五月底,就开始有点东拉西扯,语无伦次了。他的学生这时也明白,他们从赫索格教授那里大概再也学不到多少“浪漫主义的由来”了,他们只等待着怪事的发生。果然,赫索格教授课堂内的礼节日见减少。他整天若有所思,说话时常有毫不自觉的坦率。到了学期末,他讲课时经常会久久地呆着说不下去,有时甚至干脆停了下来,喃喃地说声“对不起”,伸手从怀中掏出钢笔,使劲地在一些碎纸片上写起来,弄得讲台也吱吱嘎嘎作响。他全神贯注,眼圈发黑,苍白的脸上七情尽露。他在说理,在争辩,在经受着痛苦。他仿佛想出了一个了不起的变通办法。他似乎在神游四方,又像在钻牛角尖。他的渴望、固执、愤怒——他的眼睛和嘴巴的表情,把这一切都默默地暴露无遗。人们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全班学生都等着,三分钟,五分钟,鸦雀无声。
起先,他做的笔记并无一定形式,全是片言只语——零星的废话、感叹词、曲解了的成语和语录,或者借用一句他去世已久的母亲所说的意第绪语,叫“Trepverter”,即大错铸成后所讲的悔不当初的自谴自责语。
例如,他写道:死亡——死去——再活——又死——活。
没有人,就没有死亡。
以及:你的灵魂要下跪吗?也有好处。擦地板。
还有:对付傻瓜要用他的傻办法,免得他自以为聪明。
对付傻瓜勿用他的傻办法,免得汝亦似他为傻瓜。
两者试择其一。
他又记下:据沃尔特·温彻尔告知,巴赫在创作安灵曲时套着黑手套。
对这些杂乱无章的笔记,连赫索格自己也不知道该作何感想。他只是屈从于一时产生这种想法的激动而已,有时他不禁犯起疑来:这也许就是精神崩溃的一种征兆吧?但这并没有使他感到害怕。他躺在十七街上一套租来的公寓房间的沙发上,有时候把自己想象成一座专门制造个人沧桑史的工厂。自己的一生,从出生到死,都一幕幕呈现在眼前。他在一张纸上承认:我无话可说。
他把自己的一生从头至尾细细考虑了一番,觉得没有一件事做对。他这一生,像俗话说的那样,是完蛋了。但既然这已无从着手,那也就没有什么可悲哀的了。躺在那霉得发臭的沙发上,他神游遥远的过去,十九世纪,十六世纪,十八世纪,从十八世纪里,他终于找到了一句自己颇为欣赏的话:悲哀是懒惰的一种。
他脸贴沙发躺着,继续进行自我评价。他算是个聪明人呢还是个大笨蛋?唉,照目前的情况看,他实在不能自认是聪明的了。其实,他的性格并不乏聪明机灵的素质,只是他选择了爱空想的一套而已。结果被那班骗子刮得精光。还有呢?啊,他掉头发了。他看了那班头皮专家们登的广告,心里既老大怀疑,可又暗暗希望他们说的是实话。头皮专家!唉……他以前本是个美男子呢!现在,他的脸一望而知是个受尽打击的人。但他还是自己讨的打,是授人以柄的结果。这使得他进一步去考虑一番自己的性格。这究竟是属于哪一种性格呢?喔,用时髦话说,这是一种自我陶醉狂,一种色情受虐狂,一种背时的性格。他的临床症状是沮丧抑郁,但还不是最严重的,还没有成为狂郁症。世上比他更糟糕的残废人多着呢。要是你按照当今世上每个人明显的所作所为,认为人类是病态的动物,那赫索格是否更加病态,格外愚昧,特别堕落呢?
不。那他算不算聪明呢?要是他有权力欲,性格上偏执些、霸道些,他的聪明就会更有效用了。他有妒忌心,但对竞争并无特别兴趣,所以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偏执狂。那他的学问怎么样?现在他也不得不承认,他实在不太像个教授了。不错,他还是认真的,也颇有一股子幼稚的热心和诚意,但他绝不可能成为一个有系统有学识的学者。他的博士论文《十八、十九世纪英法政治哲学的自然状况》,是个出色的开端,以后还成功地写了几篇论文和一本叫《浪漫主义和基督教》的书。但除此以外,他的那些雄心勃勃的计划,便都一个个胎死腹中。凭着他早年取得的那些成就,他不管在找工作还是搞研究经费方面,从来都没有遇到过困难。纳拉甘塞基金会这些年来就一共给他拨款一万五千美元,资助他继续研究浪漫主义。可是这一研究的成果——八百多页毫无中心的杂乱无章的议论——装在一只旧皮包内,现在正静静地躺在壁橱里。想起来就叫人伤心。
他身旁的地上撒满了纸片,因此有时他就屈身伏地而写。
此刻他记下:我的生命并非痼疾,而是一种长期的康复过程。是自由主义中产阶级的修正本,是改良的幻影,是希望的毒药。
他突然想到了消化系统有抗毒能力的米特拉达悌。企图暗害他的刺客不知底细,犯了错,只用了少量毒药,结果并没能毒死他,只把他弄得酩酊大醉。
一切皆有用。
他重又继续做着自我检讨。他承认自己本是个坏丈夫——两次婚姻都如此。他待第一个妻子戴西很糟糕。第二个妻子马德琳则要把他搞垮。对儿女,他虽然不乏慈爱,但仍是个坏父亲;对父母,他是个忘恩负义的儿子;对国家,他是个漠不关心的公民;对兄弟姐妹,虽然亲爱,但平时很少往来;对朋友,自高自大;对爱情,十分疏懒;论聪明才智,自己愚昧迟钝;对权力,毫无兴趣;对自己的灵魂,不敢正视。
他对于自己能够毫不含糊地、实事求是地进行严格的自我批判,感到十分得意,于是就反举双手,双腿一伸,在沙发上伸了个懒腰。
尽管如此,我们每个人不是仍有不少迷人之处吗?
爸爸,一个可怜人,他的笑貌能把小鸟引下枝头,能把鳄鱼引出泥淖。马德琳则不但风姿迷人,而且容貌漂亮,才智超群。她的情夫瓦伦丁·格斯贝奇,虽然粗眉大眼、心狠手辣,但依然有其迷人之处。他下巴宽大,长满一头火红的铜色鬈发(他用不着头皮专家),装着一条木头假腿,走起路来一高一低,煞是优美,宛如一名在威尼斯运河上撑平底船的船夫。赫索格自己的迷人之处也着实不少,只是他的性功能被马德琳搞垮了。连吸引女人的能力都已消失,还有什么希望恢复正常?正是在这一方面,他感到自己几乎像个尚未康复的病人。在性生活这种玩意儿上争高比低,实在无聊。
几年前,由于遇上了马德琳,赫索格替自己的生命史写下了新的一页。马德琳是他从教会里抢出来的——他们认识时,她刚皈依了宗教。为了讨取新婚妻子的欢心,他辞去了一份极为体面的教职,并且动用从他那迷人的父亲那儿继承来的两万元遗产,在马萨诸塞州的路德村买了一幢很大的旧房子。在这环境幽静的伯克夏附近,他还有朋友(瓦伦丁·格斯贝奇夫妇),按理说,在这儿他本当可以安下心来,写出他《论浪漫主义社会思潮》的第二卷的。赫索格离开学术界,并非因为他在那儿混得不得意。恰恰相反,他的声誉极好,他的论文颇有影响,已被译成法文和德文。他早年那本出版时不大为人注意的书,现在已在多处被列入必读书目,受到年轻史学家的推崇,认为它是新史学的楷模,是“一本使我们深感兴趣的历
史”。那就是说,这是一本入世的,根据古为今用的观点来考察过去的史书。和戴西结婚后,他一直过着虽属平凡,但极其体面、安定的助理教授生活。他的第一本书,通过客观的研究,阐明了基督教和浪漫主义的关系。第二本书中,他显得倔强了,野心稍露,立论也较以前大胆。平心而论,他性格上实在有着许多百折不挠的地方。他意志坚强,能言善辩,对历史哲学特别爱好。娶了马德琳,辞了教职(因为她认为他应该如此),隐居路德村后,他对威胁凶险、*主义,对异端邪说,对酷刑苛判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才华,“破坏之城”对他特别有吸引力。他曾计划写一部如实总结二十世纪革命运动和群众动乱的历史巨著,观点和法国政治学家托克威尔大同小异,认为人人平等和民主进步不仅会普及于全世界,而且还会永恒持久地发展。
但现在,在这个问题上,他不能再自欺欺人了。他对此开始大加怀疑。他的雄心壮志遭到了严重的挫折。黑格尔给他带来了不少麻烦。早在十年前,他以为自己就已把黑格尔的契约和文明两个观念弄通了,但现在看来并没有搞对头。他越想越苦恼,越不耐烦,越生气,而就在这时候,他和妻子的关系也非常奇怪地有了变化。马德琳对现状已感到不满。起初,她不想让她的丈夫一辈子做个平平凡凡的教书匠,要他辞职,可是乡居一年后,她改变主意了。她认为自己年轻美貌,聪明能干,而且生气勃勃,善于交际,绝不该在伯克夏这样的穷乡僻壤埋没掉。她决定要读完她的斯拉夫语研究生课程。于是,赫索格便给芝加哥写了谋职的信。他还得给瓦伦丁·格斯贝奇找个工作。瓦伦丁原是个电台广播员,曾在皮茨菲尔德城电台播放唱片音乐节目。马德琳说了,你不能让瓦伦丁和菲比这样的人孤零零地留在这令人伤心的乡下啊。赫索格所以决定去芝加哥,因为他是在那儿长大的,人头熟。果然,他在市区大学找到了教职,瓦伦丁也在闹市区一家调频电台谋到了一份教育指导员的差事。在路德村的房子——用老头子千辛万苦挣得的两万块钱买来的房子——连同图书、英国的骨灰瓷器和新置的家具等等,都一并封了起来,丢给蜘蛛、鼹鼠和田鼠去享用了!
赫索格一家就这样搬到中西部来了。但在芝加哥住了大约一年后,马德琳觉得实在合不来,决定要求离婚。赫索格不得不同意。他能有什么办法呢?这件事使他深感痛苦。他爱妻子,更舍不得和小女儿分开,但马德琳坚决不愿再和他保持这种婚姻关系,他只得尊重她的愿望。奴隶制早已消亡了。
这第二次的离婚,给赫索格的打击实在太大,他感到自己快要垮了。平日给他们夫妇看病的芝加哥精神病专家埃德维医生,也认为可能他还是去外地走一走的好。于是,他和市区大学校长商量,说一待精神有好转,就会来任教。然后便带着向哥哥瑞拉借来的钱,到欧洲去了。并不是每一个有精神病危险的人都花得起钱去欧洲休养的。大多数人不得不继续工作,每天上班,每天依旧乘地铁。要不就喝喝酒,到电影院干坐着活受罪。赫索格应该感到心满意足了。一个人除非死于横祸,总有一些事值得庆幸的。事实上,赫索格心里的确很感激。他在欧洲也不全闲着。他代表纳拉甘塞基金会在那儿作文化访问,并在哥本哈根、华沙、克拉科夫、柏林、贝尔格莱德、伊斯坦布尔和耶路撒冷作公开演讲。可是第二年三月回到芝加哥时,他的健康状况比十一月去时还要坏。因此他对校长说,他也许还是待在纽约的好。回到芝加哥后,他并没有去看马德琳。由于他的举止怪僻,她认为对她的威胁太大,因此事先就通过格斯贝奇警告过他,叫他不要走近哈珀街的房子,因为警察已存有他的照片,要是发现他到那个街区,就会逮捕他。赫索格一向不工于心计,所以直到现在他才看清,马德琳为了要摆脱他,事先作了多么周全的准备。在赶走他之前六个星期,她要他以两百元一月的租金,在游艺场附近租了一幢房子。搬进去后,他搭了书架,清理了庭园,修好了汽车房的门,还装了防风窗。仅在她提出离婚前一个星期,她还帮他洗熨了衣服。可是就在他离家那天,她就把他的这些衣服扔进一只纸板箱,然后砰的一声把它抛下地下室的阶梯。她需要让壁橱腾出更多的地方放东西。诸如此类的事发生不少,是悲,是喜,还是残忍凶狠,那完全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了。直到婚姻的最后一天,赫索格和马德琳之间的关系,态度都是相当认真的。也就是说,双方都能尊重对方的不同意见、性格爱好和提出的问题,并能协商解决。就拿她向他提出离婚这件事来做例子吧。她态度端正,语气温柔,这是她擅长的一套。她说她已把这件事从各个角度考虑过了,结果不得不承认失败。他们已没法再很好地相处下去。最后她还承认自己也有某些不是之处。当然,赫索格对此不是毫无思想准备,可是他原来还以为他们的关系正在改善哩。
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他正在后院安装防风窗。院子里的番茄已经受过入秋以来的第一次霜冻。青草长得又软又密,每当深秋早晨,上面挂着根根蛛丝,煞是好看。露水已浓,久久凝而不散。番茄藤已变黑,颗颗鲜红的番茄绽开裂纹。
他看到马德琳出现在楼上的后窗,她正在侍候女儿琼妮睡觉。随后,他听到浴室里的水声。不久,就从厨房门口传来她喊他的声音。湖面吹来一阵风,使赫索格手上的那块窗玻璃也抖索了一下。他小心翼翼地把它靠在走廊的墙上,脱下帆布手套,但没有摘去头上的贝雷帽,好像预感到自己马上要外出旅行似的。
马德琳的父亲是个著名的剧团经理人(有时被誉为美国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虽然马德琳恨透了他,但她的这一套本领,想是和那位老人的职业一脉相承的。今天这场面,她就是凭着自己那演剧天才,准备多时才粉墨登场。且看她脚穿长筒黑袜,高跟鞋,衣服的料子是中美洲来的淡紫色印度织锦缎,配上猫眼石耳环,戴着手镯,洒了香水;头发也是新做的,宽大的眼皮上涂着浅蓝色眼膏。她的眼睛是蓝的,可惜色泽被那经常变色的眼白给大大冲淡了。她的鼻子自眉间而下,挺直修长,在情绪特别激动时会微微抽动。但在赫索格看来,就连这一毛病也是可贵的,他对马德琳的爱已近乎把他给征服。她生性专横,他既然爱她,自然只好逆来顺受了。就在那凌乱不堪的客厅里,两个素以自我为中心的人面临摊牌阶段——赫索格现在是身在纽约,躺在沙发上追忆这些往事——她的那个“自我”胜券在握(她为这一重大时刻筹划在先,渴望已久,眼看就要如愿以偿,给予狠狠一击),赫索格的“自我”泄了气,完全处于被动地位。要说他将要受苦受难,那是活该。他恶贯满盈,罪有应得。就是这么回事。
在靠窗的玻璃架上,摆着各种供装饰用的小玻璃瓶,有威尼斯的,有瑞典的。这些摆设是屋子里原来就有的。这时阳光照在它们上面,映出彩霞万道。赫索格看着那波光,那彩线,那光怪陆离、纵横交错的道道霞光,尤其是映在马德琳身后墙上的那一抹耀眼的白光。只听见她说道:“我们没法再共同生活下去了。”
她的台词长达数分钟,措词优美,显见久经排练。而他,看起来好像也对这场演出的开幕等待多时了。
他们的婚姻不可能再继续下去。她从未爱过他。马德琳这样对他说。“我不得不对你直说,我从未爱过你,这是痛苦的。而且,我以后也决不会爱你。”她说,“因此,我们继续这样相处下去是毫无意义的。”
赫索格说:“可是,马德琳,我确是爱你的啊!”
他这么一说,马德琳顿有所悟,优越感上升,渐渐喜形于色。她变得神采奕奕,容光焕发。她的眉毛,她那拜占庭式的鼻子,上下抽动,真是眉飞色舞。红晕从她的前胸、咽喉一直泛上双颊,越来越浓,那对蓝蓝的眸子,显得更美了。她欣喜若狂,如醉如痴。赫索格突然想到,这是她把他打得如此惨败,她的虚荣心得到如此充分满足后,把她风发的意气横溢到她的才智中去了。他意识到,他这是在目睹她生命中最辉煌的一刻。
“你应该继续保留着这种感情。”她说,“我相信你说的是真心话。你确实是爱我的。但我想你应该明白,承认这次婚姻的失败,对我自己来说,也是很丢脸的。我把我的一切都贴进去啦,我已经被这件事搞垮了。”
搞垮了?她还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哩。看她那样子,真算得上一位演员,只是激情更露而已。
赫索格虽然脸色苍白,心情痛苦,但身体仍然结实,此刻他正躺在沙发上回忆往事。时值纽约的春日黄昏,城市春意盎然,可以嗅到河水的气息。落日的余晖中惹人注目地点缀着新泽西的阵阵煤烟。身犹硬朗的赫索格(他的健康实在是一种奇迹,他尽量要使自己生病却生不起来)正在闭门思过。他在想,如果当时我不是那样洗耳恭听马德琳的那套教诲,而是朝她脸上狠狠掴上几个耳光,事情会怎么样呢?或者干脆把她一拳打翻在地,抓住她的头发,拖得她尖声直叫,在房间里打滚,然后用鞭子把她的屁股抽得皮破血流。如果他真的那样揍了她,现在会是怎样呢?他真该撕破她的衣服,扯下她的项链,在她脑袋上报以老拳。他叹了口气,制止了自己的这种精神暴力。他生怕自己暗地里真的信奉上这种残暴行径了。但假如他当时对她说要她离开呢?房子毕竟是他的呀!要是她没法和他生活在一起,干吗不是她离开呢?怕人说闲话?用不着被几句闲话吓跑。这种做法可能有点荒唐,甚至会招来痛苦。但丑闻闲话对社会终究还是一种贡献。只可惜当时在那间摆着闪光瓶子的客厅里,他从未想到自己应该坚持立场,据理力争。他那时也许仍然希望以他的品格、他的温顺来感动她,使她回心转意。他毕竟是摩西——摩西·埃尔凯纳·赫索格——一个好人,又是马德琳的特别恩人。他为她做了一切——一切!目录
- 名称
- 类型
- 大小
光盘服务联系方式: 020-38250260 客服QQ:4006604884
云图客服:
用户发送的提问,这种方式就需要有位在线客服来回答用户的问题,这种 就属于对话式的,问题是这种提问是否需要用户登录才能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