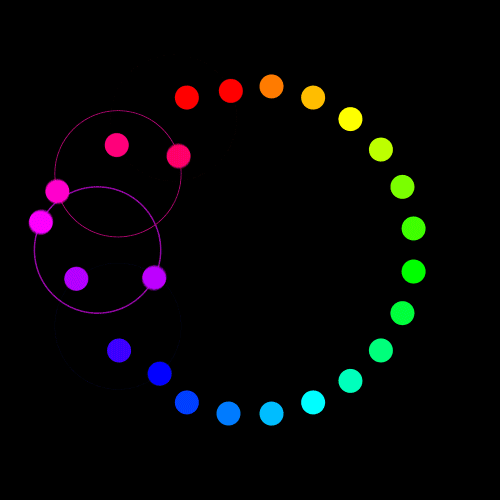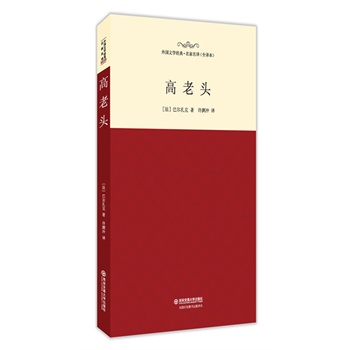简介
《高老头》是《人间喜剧》中深具影响力的一部小说,同时也拉开了《人间喜剧》的序幕。本书是巴尔扎克小说创作的*峰,有着现实主义作品的重要特色。
小说以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巴黎为背景,通过描写面粉商人高里奥大爷与两个女儿之间的故事、青年拉斯提雅的野心“奋斗史”等,细致入微地刻画了统治阶级的卑鄙与罪恶,抨击了物欲横流、丑恶人性的社会现实,暴露了金钱支配下资产阶级的人格沦丧和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目录】
一沃克公寓/1
二贵族之家/41
三花花世界/69
四亡命之徒/115
五高家二女/157
六老人之死/195
译者后记/215
【免费在线读】
一沃克公寓
这座为普通人提供膳宿的公寓是沃克大妈的产业。公寓在圣贞妮薇芙新街的下段,新街到弓箭街是一个斜坡,坡度很陡,而且高低不平,很少有马车经过。这些杂乱无章的小街斜道,在慈悲谷修道院和先贤祠两座大建筑物之间,反倒显得悠闲安静。这两座大楼庄严肃穆的圆形屋顶洒下了金黄的光彩,也投下了阴沉的暗影,改变了这里的环境和气氛。这里,路面上的铺石都是干巴巴的,没有污泥浊水,墙脚下长满了小草。*无忧无虑的人到了这里,也会像过路人一样感到忧从中来。车子的吱吱嘎嘎声似乎都是一件大事。房屋看起来阴沉沉的,高耸的围墙使人觉得像是监狱。
一个走错了路的巴黎人到了这里,只看到普通人寄宿的公寓和办事处,只看到穷困潦倒、奄奄待毙的老头子,想寻开心却不得不拼命干活儿的年轻人。巴黎没有一个街区比这里更叫人恶心,甚至可以说,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而圣贞妮薇芙新街作为这幅苦难图的框架,真是再合适不过了。为了使读者有个深刻的印象,不管用多么灰暗的色调,多么严酷的字眼,都不会太过分,就像参观古罗马的地下墓穴一样,一步一步走下墓道,越走光线越暗淡,导游的口气越说越枯燥。这个比喻真是再恰当不过了。其实谁能说得出:枯萎的心灵和空虚的脑袋,到底哪一样更可怕呢?
公寓的正面朝着一个小花园,侧面靠着圣贞妮薇芙新街,形成一个直角。在公寓和小花园之间,沿着房子的正面有一条两米宽、连环形的砾石地,前面又有一条铺沙小路,路旁有天竺葵、夹竹桃、石榴花,都种在蓝白两色的陶器盆里。顺着小路就会走到一扇大门前,门上挂了一个招牌,上面写着“沃克之家”,下面还有“供应膳宿,欢迎男女客人光临”的字样。
白天,进门要先按栅栏上装的门铃,铃声不大好听。从栅栏向外看,可以看到铺沙路的尽头,对面墙上画了一个绿色大理石的神龛,看得出来又是当地街区画家的艺术品。在神龛凹进去的地方,有一座爱神的雕像,雕像上五颜六色的油彩,象征派的爱好者一看就知道是巴黎的风流病,而这种病不消走几步就可以找到医治的地方。神像底座上刻的字已经看不清楚,但是总会使人浮想联篇,是不是1777年伏尔泰荣归巴黎时,群众的热情高涨,为他的丰功伟绩立下了这座纪念碑呢?碑上刻的字是:不管你是谁,爱神都是你的老师,现在是,过去是,将来应该还是。
天快黑了。栅栏门换上了门板,栅栏后面的公寓有多长,小花园就有多宽。花园两边都是墙,一边是沿街的墙,另一边是左邻右舍的分界墙。分界墙上爬满了一大片常春藤,仿佛从上到下都包裹了起来,特别吸引过路人,成了如画的景色;沿街的墙种了一排果树,葡萄藤爬满墙,虽然收成和成色不尽人意,但沃克大妈和房客谈起来又兴致勃勃。沿着每一堵墙都有一条狭窄的小道,通往一片菩提树的浓荫。沃克大妈是在宫方家出生的,总把“菩提”说成“不提”,虽然房客多次纠正,也不起什么作用。在这两条平行的小路中间有一大块方地,上面种着长生花,旁边是剪成圆锥形的果树,再靠边种的是莴苣或香芹。在菩提树荫下,有一张漆成绿色的圆桌,周围还有几把椅子。在炎热的夏天,连鸡蛋都会被阳光烤熟,但是有钱人还要坐在树荫下喝咖啡。
房子似乎本来就是为开公寓而盖的,底层*间屋子由靠街的两个窗子照亮,由一个落地玻璃门进出。这间屋子就是客厅,隔壁是间餐厅,隔开餐厅和厨房的是楼梯间。楼梯的踏板每一级都是木板嵌上擦亮的彩色方砖。客厅的陈设叫人看了难受:几张沙发,几把椅子,都是陈旧不堪的,有些沙发罩磨得漏了底,有些却又磨得发亮。客厅中间是一张圣安妮时代的圆桌,桌面是云花石的,上面放了个白瓷茶具柜,柜子上的金色花纹大半已经磨损掉了,这种柜子今天还可以随处看到。房子的地板相当糟,护壁板也只有半个人高,隔墙板上糊了上光的漆纸,纸上画着《特勒马克》即尤里西斯远征洛亚,十年未归,他的儿子特勒马克万里寻父的故事。的故事,英雄人物穿着华丽的彩服。在两扇铁栅窗之间的壁板上,房客们看到的是款待尤里西斯之子(就是特勒马克)的盛宴。四十年来,这张画引起了房客的说笑,他们自以为高人一等,而现实中的地位却低人一头。看到画上丰盛的酒席,而自己却只能维持不饿肚子。奈何!壁炉是石块砌成的,炉床干干净净,说明没有重大的事情是不会生火的。壁炉架上摆了两个花瓶,瓶里插满了纸花,外面盖了个玻璃罩,却掩盖不了纸花放得太久的陈旧颜色。花瓶中间摆了一架灰蓝色云石的座钟,叫人看不上眼。这*间屋子发出一股说不出的怪味,也许可以叫作公寓味,像是封闭多年的老房子,潮湿腐朽,变酸变烂,使人感到寒冷,臭气触鼻,连衣服也挡不住气味的侵蚀;闻起来有残羹剩菜的味道,或下人的房间、低级的办事处、贫民救济所的汗味。如果要描写这种怪味,那得发明一个方法来计算、估计这些老老少少的房客叫人作呕的品质,和污染空气的独特气息,才能说得清楚。其实,这种恶心的味道,如果比起隔壁的餐厅来,也不那么难闻,甚至不比夫人们的小客厅相差太远呢。
餐厅全装上了护壁板,原来的油漆颜色现在已经看不清了,露出了木板的本色,上面留下了一层层油污的痕迹,画出了无以名状的形状。靠墙摆了几个碗框,手一碰就会感到黏糊糊的,里面放了几个发暗光的长颈大肚玻璃瓶,几块带有波纹织锦的圆垫子,几沓杜奈出产的蓝边厚瓷盘。在一个角落里放了一个分格的小柜子,每一格都标了号码,让用膳的房客放他们的餐巾,不是油渍斑斑,就是酒味扑鼻;还有一些老家具稳如大山,安然不动,显然放在哪里都不合适,但是不能处理掉,就像医院里无可救药的病人一样,公寓对这些老古董也下不了狠心。例如带顶棚的晴雨表,每逢下雨,顶棚就会张开伸出去;还有叫人看了倒胃口的木刻版画,偏偏还要配上一个黑漆描金的木框;又如镶嵌了铜鳞的挂钟,一个绿色的火炉,几盏油和灰尘混成一片的油灯,一张铺上漆布的长桌,布上的油渍厚得足够让一个爱开玩笑的食客用手指在上面留名纪念;还有几把缺胳膊断腿的旧椅子,几块放在门口擦鞋泥用的草垫子已经藕断丝连,踩不断却又踏还乱了;还有几个差劲的小脚炉,洞眼有的圆、有的扁,结合的地方也已经松动,连嵌接的小木头都烤焦了。怎么办呢?要说出这些家具多么陈旧、腐朽,怎么裂开、摇晃,如何被虫蛀、残缺不全、阴阳怪气、毫无用处、一动就要散架,那需要太多的文字了,会使读者觉得没有兴趣。性急的人更受不了。只简单补充一句:红色的方砖地被鞋底磨得高低不平,或者上色不匀,显得有厚有薄。总而言之,房子笼罩在穷苦的气氛中,没有一点诗意;而节衣缩食、饱受折磨的贫困却都集中在这里。虽然还不是一塌糊涂,也已经是遍体鳞伤;虽然还没有千疮百孔、衣衫褴褛,但是迟早要腐烂崩溃,变成一摊烂泥的。
这间餐厅的黄金时间是早晨7点钟左右,沃克大妈的猫比女主人还早,抢先跳到食品柜上,闻了闻盖着碟子的几大碗牛奶,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这是它早晨的例行公事。然后女主人出场了,她戴着罗纱网眼便帽,露出了一圈没有梳理好的假发,脚上穿的是一双皱得像鬼脸似的拖鞋。她的脸有点显老,也有点显胖,脸中央突出一个鹰钩鼻;她的双手滚圆,身体丰满得像一个踏实的教徒,胸脯鼓得太显眼,并且摇摇晃晃。餐厅闻起来有股霉味,暗示投机倒把的不法作风;而沃克大妈呼吸着这暖洋洋的臭气,一点也不觉得倒胃,反而感到神清气爽。她的脸孔叫人觉得新鲜,仿佛见到秋天的*次霜冻。她的眼角皱皱褶褶,表情变化很快,刚刚还是想讨人欢喜,满脸笑容的舞女,忽然翻脸不认人,瞪眼竖眉,成了逼人还账的讨债人。总而言之,她这个人就是公寓的化身,公寓也是她放大的形象。监狱不能没有警卫,这二者是缺一不可的。这个苍白肥胖的女人就是公寓生活的产物,正像伤寒病是医院的漏网之鱼一样。她外面穿的羊毛围裙,遮住了用旧裙子改成的内裙,但线缝开裂的内裙露出了棉絮。
你们可以走遍海上,写尽墨水,想要说个清楚明白——但是无论你们走了千里万里,写了千言万语,无论你们这些海洋探险家人数多少,兴趣多大,总会发现这片海洋还有新的处女地,有没人知道的龙潭虎穴、奇花异草、奇珍异宝、奇禽怪兽。总有一些你们文学探海家闻所未闻,或者难免遗漏的东西。“沃克公寓”就是一个这样千奇百怪的地方。
高里奥大爷是个六十九岁的老头儿,1813年不做生意了,住到沃克大妈的公寓里。他先住的是谷杜尔太太那一套,每年付一千二百法郎的膳宿费。那时,多付或者少付五个金币,对他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据说沃克大妈预收了他一笔赔偿费,就把那一套三间房修整一新,其实不过是增加了一些便宜家具、黄布窗帘、绒面木架沙发、几张胶画,还有连乡下小酒店都不用的糊墙纸而已。那时,大家对高大爷还有几分敬意,对他的称呼是高先生。也许他花起钱来不太在乎,大家以为他是个不会管理钱财、老实可欺的房客。他初来的时候衣装一应齐全,是一个从生意场上退下来好好过日子的大商人。沃克大妈很喜欢他那十八件精工细作的半荷兰式的衬衣,装饰颈部的花边用两根别针扣住,别针之间有一根细小的金链子,每根别针上又有一个大钻石,这就特别引人注目了。他平常穿一套浅蓝色的衣服,一件弯弓似的蓝白两色背心,鼓起一个梨形的大肚子,肚子一鼓一缩,垂在肚子上的粗金链子就一起一落。他的鼻烟盒也是金的,里面还装了一圈头发做纪念品,是不是泄露了他走桃花运的秘密?当沃克大妈说起他是好色之徒的时候,他的嘴角上会露出愉快的笑容,仿佛抓到了他心头的痒处。他的柜子里装满了大大小小的银器,大妈好意帮他整理时都看花了眼,什么长柄勺,调羹小勺,杯盘碗盏,油瓶汤罐,各种盘碟,镀金餐具,还有些不太好看,却又舍不得丢掉的东西。这些东西使他回想起家庭生活中的往事。
“这一件,”他拿起一个盘子和一个上面有两只斑鸠互相亲热的小碗盖,对沃克大妈说,“是我妻子在结婚一周年的时候,送给我的*件纪念品。可怜的好人!她把结婚前省下来的钱都用在这上头了。你看见没有,大妈,即使把这些东西埋到土里去,我也要用手指头把它们挖出来,怎么舍得和它们分手呢?谢谢上帝!我这辈子每天早上都可以用这个小碗喝咖啡了。还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呢?我托盘里的面包可以吃好久哩!”
在这*个年头的大部分时间里,高里奥经常是每星期在外面吃一两次晚餐。后来,不晓得怎么搞的,改成一个月只进城吃两次了。高里奥先生在外面用餐的习惯很符合沃克大妈的利益。因此当他越来越按时的在公寓用餐时,不能不引起沃克大妈的不满。这些小人国的人物*令人讨厌的习惯,就是以为别人和他们一样小气。不幸的是,到了第二年年底,高里奥先生证实了关于他的流言蜚语,他居然要求沃克大妈让他搬到二楼去,可以把膳宿费减少到九百法郎。他要节省开支,甚至整个冬天都不生火。沃克大妈要他预付膳宿费,他倒爽快地答应了。从此以后,沃克大妈就叫他高老头。至于他的经济情况为什么会下落到这个地步,那就只好任人猜想了。要想猜破也不容易,简直有点像是探险。正如那个假伯爵夫人说过的,高里奥大爷是个不太说话、假装正派的人。根据那些头脑空洞,无话可说又要随便说话的人自以为是的逻辑,闭口不谈私事的人一定没干好事。这个与众不同的商人居然沉默寡言,一定是个骗子;这个对女人殷勤的老头,一定是一个好色鬼。沃特能就在这个时候住进了公寓。根据他的观察,高里奥大爷有时去证券交易所做公债买卖,蚀本之后,用一个金融界相当流行的字眼来说,他就做起“投机生意”来了,有时他又是个赌徒,每天晚上要去赌场碰碰运气,赢他十来个法郎;有人说他是警察局雇用的暗探,但沃特能认为他做暗探不够机敏;有时还有人说高里奥是个守财奴,放高利贷,出借小额贷款,又有人说他做奖券生意。总之,说法五花八门,一句话,他几乎成了罪恶之源,无耻之尤、无能之辈,简直是神秘莫测了。不过,无论把他的行为说得多么坏,罪恶说得多么大,名誉说得如何扫地,他还没有令人讨厌得到了扫地出门的地步,并且还是照付他的膳宿费。再说,他有人所不及的用处,谁都可以对他发脾气,发泄自己的好脾气或坏脾气,谁都可以和他开玩笑或者说冲撞的话。虽然众说纷纭,但是比较可靠而且大家都能接受的看法,还是沃克大妈说的:“这个老头子保养得那么好,身体这样结实,眼睛看得清楚;和他在一起可以寻开心,其实是个放荡不羁的人,只是趣味与众不同而已。”
下面沃克家的寡妇举了一个事实为例,说明她并不是无中生有,诬蔑诽谤。在那个带来晦气的伯爵夫人不费分文地白吃白住了六个月,却又溜之大吉之后,有一天早上,大妈还没起床,忽然听见楼梯上有绸子长裙窸窸窣窣的响声,还有小巧玲珑的少女轻快敏捷的脚步声,一阵风似的飘进了高里奥未卜先知就半开半关的房门。胖厨娘希尔微马上来告诉老板娘:一个漂亮得不太正经而又打扮得有如天仙的女人,穿了一双没有污泥沾染的斜纹薄呢半筒靴,从街上一溜烟似的走进了厨房,向她打听高里奥先生住的是哪套房间。沃克大妈厨娘赶快去门外偷听,只听到几句温存体贴的言语,他们的谈话就结束了。高里奥先生送客的时候,胖厨娘希尔微立刻拿上菜篮子,假装要上市场去买菜,其实是要跟踪这一对情人。
“大妈,”她回来时对老板娘说,“高里奥先生一定是阔气得不得了,才会走到这一步的。你想想看,在断头街转弯的地方,有一部漂亮的马车在等他们,我还看见女客上车呢。”
吃晚餐的时候,沃克大妈特意去把窗帘拉上,免得阳光刺了高里奥的眼睛。
“高里奥先生,光艳照人的东西都喜欢你,连阳光都追上你了。”她暗示早上的女客人,“哎哟!你的口味真高,她的确很漂亮!”
“那是我的女儿。”他说话时露出了一股得意的神气,房客们都看出了老头子的自负,还加上爱面子。这事过了一个月后,高里奥先生又会了一次客。他的女儿上次来穿的是晨装,这次来是在晚餐后,穿的是去社交场合的衣服。房客们正在客厅里闲谈,看见这个金发女郎身材苗条,风度高雅。她太出色了,怎么可能是高老头的女儿呢?
“来了两个!”胖厨娘说。她没有认出客人就是上次来的那一位。
几天之后,又来了另外一个女儿,身材高大,体态匀称,皮肤深色,头发漆黑,眼睛灵活,她也要见高里奥先生。
“来了三个!”希尔微说。
第二个女儿*次也是上午来看父亲的,过了几天,又在晚上穿了舞装,坐着马车来了。
“来了四个!”沃克大妈和胖厨娘希尔微一起说。一点也没看出,她就是上次来时没有打扮的那个女客。
那时高里奥还付一千二百法郎的膳宿费。沃克大妈觉得一个有钱人养上四五个情妇也不值得大惊小怪,甚至认为他把情妇说成是女儿,说法也很高明。他把她们叫到沃克公寓里来,她也不说他不循规蹈矩。只是这些漂亮的情妇说明了,她的房客从前为什么不把她放在眼里。
第二年年初,她就不客气地说他是一只大公猫(情夫)了。后来,等他的身份降低到只付九百法郎的时候,有一次碰到一个女客下楼,她就毫不客气地质问他是不是把她的公寓当成销魂场所了。高里奥大爷告诉她这个女客是他的大女儿。
“你难道有三十六个女儿吗?”沃克大妈尖酸刻薄地问道。
“我只有两个。”她的房客很客气地回答,就像一个破落户一样只敢逆来顺受。
快到第三年年底时,高里奥大爷还要减少开销,搬到三楼去了,每月只交四十五法郎。他不再吸鼻烟,不再请理发师,头发也不再扑粉了。当高里奥大爷*次没有扑粉就出现时,沃克大妈吃了一惊,甚至叫了起来,因为他的头发灰绿色,肮里肮脏。他的外貌受到内心忧虑的折磨,不知不觉地变得一天比一天难看,不但不能增加用餐人的食欲,反而成了餐桌上倒胃口的阴沉面孔。那时大家不再怀疑:高里奥大爷是个放荡不羁的老风流,他的眼睛受到春药的恶性影响,若不是医生本领好,恐怕早就保不住了。他的头发颜色令人讨厌,也是生活荒唐,毫无节制,还要吃药继续荒唐下去的结果。高老头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使这些翻来覆去的闲言碎语越听越像是真的。他的衣服穿旧了,他就买十四个苏一码的白布做衬衫。他的金刚钻石、金鼻烟壶、粗金链子、金银珠宝,都一件一件不见了。他不再穿浅蓝的衣服、舒适的套装,不管冬天还是夏天,都穿栗色粗呢外衣,粗毛背心,灰色斜纹厚布长裤。他变得越来越消瘦了,腿肚子不再鼓起来。满足于过普通人的好日子而胖起来的脸,起了很多皱纹,额头也画上了皱褶,两腮陷了下去。
在他住到圣贞妮薇芙新街的第四年,他完全不像从前的模样:六十二岁的面粉商人看起来还不到四十岁,是一个胖大的有钱人,刚干过轻浮的勾当,穿着花哨的服装,连过路人看了也会开心,连笑容也显得年轻。现在却似乎成了个七十岁的痴呆老人,行动踉跄,脸色苍白。灵活的蓝眼睛显出了暗淡的铁灰色,苍白无神,似乎连眼泪的滋润都没有,眼眶却又红得像流血。红眼叫人看了害怕,泪眼却又叫人怜悯。有些学医的年轻大学生看到他嘴唇下垂,颧骨突出,认为他得了痴呆症,使劲推呀摇呀,都得不出什么结果。
有一天晚餐后,沃克大妈冷嘲热讽地对他说:“怎么?她们就不再来看你了,你的那些女儿?”说话的口气好像怀疑他不是她们的父亲。高里奥大爷一听就发抖了,仿佛房东大妈用铁针刺了他一下似的。
“她们有时候会来的。”他回答时声音显得很激动。
“哈哈!你有时还会看到她们?”大学生叫了起来,“你真行,高大爷!”
但是高老头没有听懂他的回答引起的开心话,又沉浸到沉思默想中去了。而那些只看表面现象的人以为他是麻木不仁,智力上有缺陷。如果他们真了解他,也许会对他所面临的物质问题和精神问题感一点兴趣,但那的确太难了。虽然很容易就知道,高里奥是不是当真做过面粉生意,他的财产到底有多少,但是那些知情的老人几乎都住在公寓里,虽不是足不出户,但是很少走出街区。至于其他人呢,五花八门的巴黎生活使他们一离开圣贞妮薇芙新街,就忘记了他们所取笑过的可怜虫。对于那些眼界狭窄的人,就像对这些无忧无虑的年轻大学生一样,高里奥大爷所受的苦难枯燥无味,是他自己的愚蠢所酿成的苦果,和他们所关心的钱财和前途有什么关系呢?至于他说是他女儿的那些女客,每个人都同意沃克大妈逻辑严谨的推论。“假如高老头的女儿像来看他的女客那么有钱,他也不会住到我这个公寓的三楼,每月只付四十五个法郎,连出去都穿得像个穷人了。”
没有什么能够推翻这个结论。因此,到了1819年11月底,也就是本书好戏开场的时候,公寓里的每一个人对可怜的高老头都有一个固定的看法。有一个博物馆的职员在公寓包伙,他说高老头不但没有女儿,甚至没有老婆。他寻欢作乐的生活使他成了一只到处为家的蜗牛,一种可以归入甲革类的人形软体动物。比起高老头,住三楼的布瓦雷都成了雄鹰,成了上等人。因为布瓦雷还会说话,讲道理,回答问题。虽然,说老实话,他并没有说出什么,只是重复别人说的、讲的或回答的,他习惯于用不同的字眼来重复别人说过的话。但他到底还是参加了谈话,到底是个活人,懂得道理,而据这个博物馆的职员说,高老头却经常是雷奥秘发明的寒暑表上的零度。
目录
一沃克公寓/1
二贵族之家/41
三花花世界/69
四亡命之徒/115
五高家二女/157
六老人之死/195
译者后记/215
【免费在线读】
一沃克公寓
这座为普通人提供膳宿的公寓是沃克大妈的产业。公寓在圣贞妮薇芙新街的下段,新街到弓箭街是一个斜坡,坡度很陡,而且高低不平,很少有马车经过。这些杂乱无章的小街斜道,在慈悲谷修道院和先贤祠两座大建筑物之间,反倒显得悠闲安静。这两座大楼庄严肃穆的圆形屋顶洒下了金黄的光彩,也投下了阴沉的暗影,改变了这里的环境和气氛。这里,路面上的铺石都是干巴巴的,没有污泥浊水,墙脚下长满了小草。*无忧无虑的人到了这里,也会像过路人一样感到忧从中来。车子的吱吱嘎嘎声似乎都是一件大事。房屋看起来阴沉沉的,高耸的围墙使人觉得像是监狱。
一个走错了路的巴黎人到了这里,只看到普通人寄宿的公寓和办事处,只看到穷困潦倒、奄奄待毙的老头子,想寻开心却不得不拼命干活儿的年轻人。巴黎没有一个街区比这里更叫人恶心,甚至可以说,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而圣贞妮薇芙新街作为这幅苦难图的框架,真是再合适不过了。为了使读者有个深刻的印象,不管用多么灰暗的色调,多么严酷的字眼,都不会太过分,就像参观古罗马的地下墓穴一样,一步一步走下墓道,越走光线越暗淡,导游的口气越说越枯燥。这个比喻真是再恰当不过了。其实谁能说得出:枯萎的心灵和空虚的脑袋,到底哪一样更可怕呢?
公寓的正面朝着一个小花园,侧面靠着圣贞妮薇芙新街,形成一个直角。在公寓和小花园之间,沿着房子的正面有一条两米宽、连环形的砾石地,前面又有一条铺沙小路,路旁有天竺葵、夹竹桃、石榴花,都种在蓝白两色的陶器盆里。顺着小路就会走到一扇大门前,门上挂了一个招牌,上面写着“沃克之家”,下面还有“供应膳宿,欢迎男女客人光临”的字样。
白天,进门要先按栅栏上装的门铃,铃声不大好听。从栅栏向外看,可以看到铺沙路的尽头,对面墙上画了一个绿色大理石的神龛,看得出来又是当地街区画家的艺术品。在神龛凹进去的地方,有一座爱神的雕像,雕像上五颜六色的油彩,象征派的爱好者一看就知道是巴黎的风流病,而这种病不消走几步就可以找到医治的地方。神像底座上刻的字已经看不清楚,但是总会使人浮想联篇,是不是1777年伏尔泰荣归巴黎时,群众的热情高涨,为他的丰功伟绩立下了这座纪念碑呢?碑上刻的字是:不管你是谁,爱神都是你的老师,现在是,过去是,将来应该还是。
天快黑了。栅栏门换上了门板,栅栏后面的公寓有多长,小花园就有多宽。花园两边都是墙,一边是沿街的墙,另一边是左邻右舍的分界墙。分界墙上爬满了一大片常春藤,仿佛从上到下都包裹了起来,特别吸引过路人,成了如画的景色;沿街的墙种了一排果树,葡萄藤爬满墙,虽然收成和成色不尽人意,但沃克大妈和房客谈起来又兴致勃勃。沿着每一堵墙都有一条狭窄的小道,通往一片菩提树的浓荫。沃克大妈是在宫方家出生的,总把“菩提”说成“不提”,虽然房客多次纠正,也不起什么作用。在这两条平行的小路中间有一大块方地,上面种着长生花,旁边是剪成圆锥形的果树,再靠边种的是莴苣或香芹。在菩提树荫下,有一张漆成绿色的圆桌,周围还有几把椅子。在炎热的夏天,连鸡蛋都会被阳光烤熟,但是有钱人还要坐在树荫下喝咖啡。
房子似乎本来就是为开公寓而盖的,底层*间屋子由靠街的两个窗子照亮,由一个落地玻璃门进出。这间屋子就是客厅,隔壁是间餐厅,隔开餐厅和厨房的是楼梯间。楼梯的踏板每一级都是木板嵌上擦亮的彩色方砖。客厅的陈设叫人看了难受:几张沙发,几把椅子,都是陈旧不堪的,有些沙发罩磨得漏了底,有些却又磨得发亮。客厅中间是一张圣安妮时代的圆桌,桌面是云花石的,上面放了个白瓷茶具柜,柜子上的金色花纹大半已经磨损掉了,这种柜子今天还可以随处看到。房子的地板相当糟,护壁板也只有半个人高,隔墙板上糊了上光的漆纸,纸上画着《特勒马克》即尤里西斯远征洛亚,十年未归,他的儿子特勒马克万里寻父的故事。的故事,英雄人物穿着华丽的彩服。在两扇铁栅窗之间的壁板上,房客们看到的是款待尤里西斯之子(就是特勒马克)的盛宴。四十年来,这张画引起了房客的说笑,他们自以为高人一等,而现实中的地位却低人一头。看到画上丰盛的酒席,而自己却只能维持不饿肚子。奈何!壁炉是石块砌成的,炉床干干净净,说明没有重大的事情是不会生火的。壁炉架上摆了两个花瓶,瓶里插满了纸花,外面盖了个玻璃罩,却掩盖不了纸花放得太久的陈旧颜色。花瓶中间摆了一架灰蓝色云石的座钟,叫人看不上眼。这*间屋子发出一股说不出的怪味,也许可以叫作公寓味,像是封闭多年的老房子,潮湿腐朽,变酸变烂,使人感到寒冷,臭气触鼻,连衣服也挡不住气味的侵蚀;闻起来有残羹剩菜的味道,或下人的房间、低级的办事处、贫民救济所的汗味。如果要描写这种怪味,那得发明一个方法来计算、估计这些老老少少的房客叫人作呕的品质,和污染空气的独特气息,才能说得清楚。其实,这种恶心的味道,如果比起隔壁的餐厅来,也不那么难闻,甚至不比夫人们的小客厅相差太远呢。
餐厅全装上了护壁板,原来的油漆颜色现在已经看不清了,露出了木板的本色,上面留下了一层层油污的痕迹,画出了无以名状的形状。靠墙摆了几个碗框,手一碰就会感到黏糊糊的,里面放了几个发暗光的长颈大肚玻璃瓶,几块带有波纹织锦的圆垫子,几沓杜奈出产的蓝边厚瓷盘。在一个角落里放了一个分格的小柜子,每一格都标了号码,让用膳的房客放他们的餐巾,不是油渍斑斑,就是酒味扑鼻;还有一些老家具稳如大山,安然不动,显然放在哪里都不合适,但是不能处理掉,就像医院里无可救药的病人一样,公寓对这些老古董也下不了狠心。例如带顶棚的晴雨表,每逢下雨,顶棚就会张开伸出去;还有叫人看了倒胃口的木刻版画,偏偏还要配上一个黑漆描金的木框;又如镶嵌了铜鳞的挂钟,一个绿色的火炉,几盏油和灰尘混成一片的油灯,一张铺上漆布的长桌,布上的油渍厚得足够让一个爱开玩笑的食客用手指在上面留名纪念;还有几把缺胳膊断腿的旧椅子,几块放在门口擦鞋泥用的草垫子已经藕断丝连,踩不断却又踏还乱了;还有几个差劲的小脚炉,洞眼有的圆、有的扁,结合的地方也已经松动,连嵌接的小木头都烤焦了。怎么办呢?要说出这些家具多么陈旧、腐朽,怎么裂开、摇晃,如何被虫蛀、残缺不全、阴阳怪气、毫无用处、一动就要散架,那需要太多的文字了,会使读者觉得没有兴趣。性急的人更受不了。只简单补充一句:红色的方砖地被鞋底磨得高低不平,或者上色不匀,显得有厚有薄。总而言之,房子笼罩在穷苦的气氛中,没有一点诗意;而节衣缩食、饱受折磨的贫困却都集中在这里。虽然还不是一塌糊涂,也已经是遍体鳞伤;虽然还没有千疮百孔、衣衫褴褛,但是迟早要腐烂崩溃,变成一摊烂泥的。
这间餐厅的黄金时间是早晨7点钟左右,沃克大妈的猫比女主人还早,抢先跳到食品柜上,闻了闻盖着碟子的几大碗牛奶,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这是它早晨的例行公事。然后女主人出场了,她戴着罗纱网眼便帽,露出了一圈没有梳理好的假发,脚上穿的是一双皱得像鬼脸似的拖鞋。她的脸有点显老,也有点显胖,脸中央突出一个鹰钩鼻;她的双手滚圆,身体丰满得像一个踏实的教徒,胸脯鼓得太显眼,并且摇摇晃晃。餐厅闻起来有股霉味,暗示投机倒把的不法作风;而沃克大妈呼吸着这暖洋洋的臭气,一点也不觉得倒胃,反而感到神清气爽。她的脸孔叫人觉得新鲜,仿佛见到秋天的*次霜冻。她的眼角皱皱褶褶,表情变化很快,刚刚还是想讨人欢喜,满脸笑容的舞女,忽然翻脸不认人,瞪眼竖眉,成了逼人还账的讨债人。总而言之,她这个人就是公寓的化身,公寓也是她放大的形象。监狱不能没有警卫,这二者是缺一不可的。这个苍白肥胖的女人就是公寓生活的产物,正像伤寒病是医院的漏网之鱼一样。她外面穿的羊毛围裙,遮住了用旧裙子改成的内裙,但线缝开裂的内裙露出了棉絮。
你们可以走遍海上,写尽墨水,想要说个清楚明白——但是无论你们走了千里万里,写了千言万语,无论你们这些海洋探险家人数多少,兴趣多大,总会发现这片海洋还有新的处女地,有没人知道的龙潭虎穴、奇花异草、奇珍异宝、奇禽怪兽。总有一些你们文学探海家闻所未闻,或者难免遗漏的东西。“沃克公寓”就是一个这样千奇百怪的地方。
高里奥大爷是个六十九岁的老头儿,1813年不做生意了,住到沃克大妈的公寓里。他先住的是谷杜尔太太那一套,每年付一千二百法郎的膳宿费。那时,多付或者少付五个金币,对他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据说沃克大妈预收了他一笔赔偿费,就把那一套三间房修整一新,其实不过是增加了一些便宜家具、黄布窗帘、绒面木架沙发、几张胶画,还有连乡下小酒店都不用的糊墙纸而已。那时,大家对高大爷还有几分敬意,对他的称呼是高先生。也许他花起钱来不太在乎,大家以为他是个不会管理钱财、老实可欺的房客。他初来的时候衣装一应齐全,是一个从生意场上退下来好好过日子的大商人。沃克大妈很喜欢他那十八件精工细作的半荷兰式的衬衣,装饰颈部的花边用两根别针扣住,别针之间有一根细小的金链子,每根别针上又有一个大钻石,这就特别引人注目了。他平常穿一套浅蓝色的衣服,一件弯弓似的蓝白两色背心,鼓起一个梨形的大肚子,肚子一鼓一缩,垂在肚子上的粗金链子就一起一落。他的鼻烟盒也是金的,里面还装了一圈头发做纪念品,是不是泄露了他走桃花运的秘密?当沃克大妈说起他是好色之徒的时候,他的嘴角上会露出愉快的笑容,仿佛抓到了他心头的痒处。他的柜子里装满了大大小小的银器,大妈好意帮他整理时都看花了眼,什么长柄勺,调羹小勺,杯盘碗盏,油瓶汤罐,各种盘碟,镀金餐具,还有些不太好看,却又舍不得丢掉的东西。这些东西使他回想起家庭生活中的往事。
“这一件,”他拿起一个盘子和一个上面有两只斑鸠互相亲热的小碗盖,对沃克大妈说,“是我妻子在结婚一周年的时候,送给我的*件纪念品。可怜的好人!她把结婚前省下来的钱都用在这上头了。你看见没有,大妈,即使把这些东西埋到土里去,我也要用手指头把它们挖出来,怎么舍得和它们分手呢?谢谢上帝!我这辈子每天早上都可以用这个小碗喝咖啡了。还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呢?我托盘里的面包可以吃好久哩!”
在这*个年头的大部分时间里,高里奥经常是每星期在外面吃一两次晚餐。后来,不晓得怎么搞的,改成一个月只进城吃两次了。高里奥先生在外面用餐的习惯很符合沃克大妈的利益。因此当他越来越按时的在公寓用餐时,不能不引起沃克大妈的不满。这些小人国的人物*令人讨厌的习惯,就是以为别人和他们一样小气。不幸的是,到了第二年年底,高里奥先生证实了关于他的流言蜚语,他居然要求沃克大妈让他搬到二楼去,可以把膳宿费减少到九百法郎。他要节省开支,甚至整个冬天都不生火。沃克大妈要他预付膳宿费,他倒爽快地答应了。从此以后,沃克大妈就叫他高老头。至于他的经济情况为什么会下落到这个地步,那就只好任人猜想了。要想猜破也不容易,简直有点像是探险。正如那个假伯爵夫人说过的,高里奥大爷是个不太说话、假装正派的人。根据那些头脑空洞,无话可说又要随便说话的人自以为是的逻辑,闭口不谈私事的人一定没干好事。这个与众不同的商人居然沉默寡言,一定是个骗子;这个对女人殷勤的老头,一定是一个好色鬼。沃特能就在这个时候住进了公寓。根据他的观察,高里奥大爷有时去证券交易所做公债买卖,蚀本之后,用一个金融界相当流行的字眼来说,他就做起“投机生意”来了,有时他又是个赌徒,每天晚上要去赌场碰碰运气,赢他十来个法郎;有人说他是警察局雇用的暗探,但沃特能认为他做暗探不够机敏;有时还有人说高里奥是个守财奴,放高利贷,出借小额贷款,又有人说他做奖券生意。总之,说法五花八门,一句话,他几乎成了罪恶之源,无耻之尤、无能之辈,简直是神秘莫测了。不过,无论把他的行为说得多么坏,罪恶说得多么大,名誉说得如何扫地,他还没有令人讨厌得到了扫地出门的地步,并且还是照付他的膳宿费。再说,他有人所不及的用处,谁都可以对他发脾气,发泄自己的好脾气或坏脾气,谁都可以和他开玩笑或者说冲撞的话。虽然众说纷纭,但是比较可靠而且大家都能接受的看法,还是沃克大妈说的:“这个老头子保养得那么好,身体这样结实,眼睛看得清楚;和他在一起可以寻开心,其实是个放荡不羁的人,只是趣味与众不同而已。”
下面沃克家的寡妇举了一个事实为例,说明她并不是无中生有,诬蔑诽谤。在那个带来晦气的伯爵夫人不费分文地白吃白住了六个月,却又溜之大吉之后,有一天早上,大妈还没起床,忽然听见楼梯上有绸子长裙窸窸窣窣的响声,还有小巧玲珑的少女轻快敏捷的脚步声,一阵风似的飘进了高里奥未卜先知就半开半关的房门。胖厨娘希尔微马上来告诉老板娘:一个漂亮得不太正经而又打扮得有如天仙的女人,穿了一双没有污泥沾染的斜纹薄呢半筒靴,从街上一溜烟似的走进了厨房,向她打听高里奥先生住的是哪套房间。沃克大妈厨娘赶快去门外偷听,只听到几句温存体贴的言语,他们的谈话就结束了。高里奥先生送客的时候,胖厨娘希尔微立刻拿上菜篮子,假装要上市场去买菜,其实是要跟踪这一对情人。
“大妈,”她回来时对老板娘说,“高里奥先生一定是阔气得不得了,才会走到这一步的。你想想看,在断头街转弯的地方,有一部漂亮的马车在等他们,我还看见女客上车呢。”
吃晚餐的时候,沃克大妈特意去把窗帘拉上,免得阳光刺了高里奥的眼睛。
“高里奥先生,光艳照人的东西都喜欢你,连阳光都追上你了。”她暗示早上的女客人,“哎哟!你的口味真高,她的确很漂亮!”
“那是我的女儿。”他说话时露出了一股得意的神气,房客们都看出了老头子的自负,还加上爱面子。这事过了一个月后,高里奥先生又会了一次客。他的女儿上次来穿的是晨装,这次来是在晚餐后,穿的是去社交场合的衣服。房客们正在客厅里闲谈,看见这个金发女郎身材苗条,风度高雅。她太出色了,怎么可能是高老头的女儿呢?
“来了两个!”胖厨娘说。她没有认出客人就是上次来的那一位。
几天之后,又来了另外一个女儿,身材高大,体态匀称,皮肤深色,头发漆黑,眼睛灵活,她也要见高里奥先生。
“来了三个!”希尔微说。
第二个女儿*次也是上午来看父亲的,过了几天,又在晚上穿了舞装,坐着马车来了。
“来了四个!”沃克大妈和胖厨娘希尔微一起说。一点也没看出,她就是上次来时没有打扮的那个女客。
那时高里奥还付一千二百法郎的膳宿费。沃克大妈觉得一个有钱人养上四五个情妇也不值得大惊小怪,甚至认为他把情妇说成是女儿,说法也很高明。他把她们叫到沃克公寓里来,她也不说他不循规蹈矩。只是这些漂亮的情妇说明了,她的房客从前为什么不把她放在眼里。
第二年年初,她就不客气地说他是一只大公猫(情夫)了。后来,等他的身份降低到只付九百法郎的时候,有一次碰到一个女客下楼,她就毫不客气地质问他是不是把她的公寓当成销魂场所了。高里奥大爷告诉她这个女客是他的大女儿。
“你难道有三十六个女儿吗?”沃克大妈尖酸刻薄地问道。
“我只有两个。”她的房客很客气地回答,就像一个破落户一样只敢逆来顺受。
快到第三年年底时,高里奥大爷还要减少开销,搬到三楼去了,每月只交四十五法郎。他不再吸鼻烟,不再请理发师,头发也不再扑粉了。当高里奥大爷*次没有扑粉就出现时,沃克大妈吃了一惊,甚至叫了起来,因为他的头发灰绿色,肮里肮脏。他的外貌受到内心忧虑的折磨,不知不觉地变得一天比一天难看,不但不能增加用餐人的食欲,反而成了餐桌上倒胃口的阴沉面孔。那时大家不再怀疑:高里奥大爷是个放荡不羁的老风流,他的眼睛受到春药的恶性影响,若不是医生本领好,恐怕早就保不住了。他的头发颜色令人讨厌,也是生活荒唐,毫无节制,还要吃药继续荒唐下去的结果。高老头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使这些翻来覆去的闲言碎语越听越像是真的。他的衣服穿旧了,他就买十四个苏一码的白布做衬衫。他的金刚钻石、金鼻烟壶、粗金链子、金银珠宝,都一件一件不见了。他不再穿浅蓝的衣服、舒适的套装,不管冬天还是夏天,都穿栗色粗呢外衣,粗毛背心,灰色斜纹厚布长裤。他变得越来越消瘦了,腿肚子不再鼓起来。满足于过普通人的好日子而胖起来的脸,起了很多皱纹,额头也画上了皱褶,两腮陷了下去。
在他住到圣贞妮薇芙新街的第四年,他完全不像从前的模样:六十二岁的面粉商人看起来还不到四十岁,是一个胖大的有钱人,刚干过轻浮的勾当,穿着花哨的服装,连过路人看了也会开心,连笑容也显得年轻。现在却似乎成了个七十岁的痴呆老人,行动踉跄,脸色苍白。灵活的蓝眼睛显出了暗淡的铁灰色,苍白无神,似乎连眼泪的滋润都没有,眼眶却又红得像流血。红眼叫人看了害怕,泪眼却又叫人怜悯。有些学医的年轻大学生看到他嘴唇下垂,颧骨突出,认为他得了痴呆症,使劲推呀摇呀,都得不出什么结果。
有一天晚餐后,沃克大妈冷嘲热讽地对他说:“怎么?她们就不再来看你了,你的那些女儿?”说话的口气好像怀疑他不是她们的父亲。高里奥大爷一听就发抖了,仿佛房东大妈用铁针刺了他一下似的。
“她们有时候会来的。”他回答时声音显得很激动。
“哈哈!你有时还会看到她们?”大学生叫了起来,“你真行,高大爷!”
但是高老头没有听懂他的回答引起的开心话,又沉浸到沉思默想中去了。而那些只看表面现象的人以为他是麻木不仁,智力上有缺陷。如果他们真了解他,也许会对他所面临的物质问题和精神问题感一点兴趣,但那的确太难了。虽然很容易就知道,高里奥是不是当真做过面粉生意,他的财产到底有多少,但是那些知情的老人几乎都住在公寓里,虽不是足不出户,但是很少走出街区。至于其他人呢,五花八门的巴黎生活使他们一离开圣贞妮薇芙新街,就忘记了他们所取笑过的可怜虫。对于那些眼界狭窄的人,就像对这些无忧无虑的年轻大学生一样,高里奥大爷所受的苦难枯燥无味,是他自己的愚蠢所酿成的苦果,和他们所关心的钱财和前途有什么关系呢?至于他说是他女儿的那些女客,每个人都同意沃克大妈逻辑严谨的推论。“假如高老头的女儿像来看他的女客那么有钱,他也不会住到我这个公寓的三楼,每月只付四十五个法郎,连出去都穿得像个穷人了。”
没有什么能够推翻这个结论。因此,到了1819年11月底,也就是本书好戏开场的时候,公寓里的每一个人对可怜的高老头都有一个固定的看法。有一个博物馆的职员在公寓包伙,他说高老头不但没有女儿,甚至没有老婆。他寻欢作乐的生活使他成了一只到处为家的蜗牛,一种可以归入甲革类的人形软体动物。比起高老头,住三楼的布瓦雷都成了雄鹰,成了上等人。因为布瓦雷还会说话,讲道理,回答问题。虽然,说老实话,他并没有说出什么,只是重复别人说的、讲的或回答的,他习惯于用不同的字眼来重复别人说过的话。但他到底还是参加了谈话,到底是个活人,懂得道理,而据这个博物馆的职员说,高老头却经常是雷奥秘发明的寒暑表上的零度。
【作者简介】
作者:巴尔扎克(1799-1850),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一生创作90余部长、中、短篇小说和随笔,合称《人间喜剧》。其中代表作为《欧叶妮·葛朗台》《高老头》等。一百多年来,他的作品传遍了全世界,对世界文学的发展和人类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称赞他“是超群的小说家”和“现实主义大师”。
译者:许渊冲,北京大学教授,著名法语翻译家、翻译理论家,是迄今将中国古典诗词翻译成英法韵文的*专家。书销中外百余本,诗译英法*人。主要法文译著有《高老头》《红与黑》《包法利夫人》等。他曾荣获国际翻译界*奖项之一的“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以及中国翻译协会颁发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光盘服务联系方式: 020-38250260 客服QQ:4006604884
云图客服:
用户发送的提问,这种方式就需要有位在线客服来回答用户的问题,这种 就属于对话式的,问题是这种提问是否需要用户登录才能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