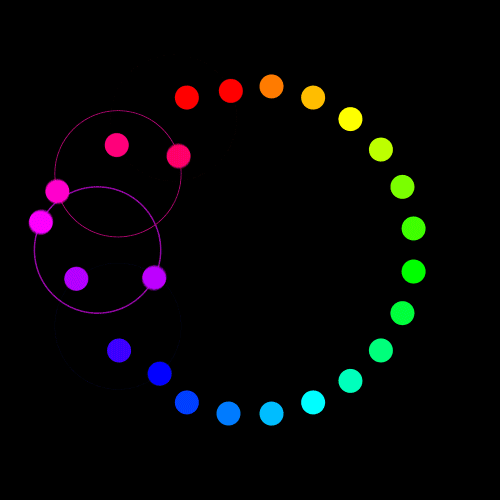简介
《此情须问天》故事的发端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的那场灾难性的大洪水。仿佛有着特殊的天人感应,一代伟人的离世、震惊中外的大地震等交织而至。作者以此为起点,勾勒小说主人公的人生轨迹,循序推进,层层展开,使人犹如身临其境,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时代。
生活是没有布景的舞台。小说主人公、童年时代的陈玉栋和黎珩为躲避那场罕见的水灾,偶然相遇,一场动人心扉、让人心痛、催人泪下的人生活剧由此拉开帷幕。主人公以及和他们相关的人物故事渐次登台。这些故事,或平淡,或跌宕,或伤感,或无奈,无不让人感同身受而引发心灵的共鸣。
目录
第一章
有山的地方神话多,有河的地方故事多。从双狮山发源的双狮河支流众多,中下游的清阳河是众支流之一。清阳河也有些与众不同,它的流向是自东向西的,弯弯曲曲的不知从哪里来也不知流向哪里,它以一种优美的曲线展示着独特的姿态和充满自信的长度。不到汛期的河面只有几十米宽,两岸的沙滩与河面的宽度差不多。南岸的河床高出水面二三十米,河堤上面是绵延不断的农田和村落。北岸没有河堤,沙滩的尽头是一片片树林,树林的尽头散落着一个个村庄。沙滩和树林成了北岸居民的河堤,即使河流汛期水涨,他们大多数时候也都是安全的。河边有个村庄绰号舟河,其实叫陈家湾。
传说这条小河每隔十年发一次洪水,每隔三十年发一次特大洪水。每次特大洪水过后,方圆几十里的村庄和农田都会被荡为平地,只有陈家湾除外。陈家湾像一艘永不下沉的奇妙的船,水涨它也涨,因此得名舟河。
在北岸的村庄中,只有陈家湾与树林几乎平行。远远看去,它就在河边上,没有任何安全感。陈家湾北面是相隔一公里的曾家坝,小河涨水时,如果水势小,曾家坝能够幸免于难,如果水势大,河水会把离自己近的陈家湾高高举起,把距离远的曾家坝吞入腹中。但造物主总是公平的,它给了陈家湾不沉的造化,也给了曾家坝繁华的街道。曾家坝是方圆十里乃至几十里的著名街镇。这里有通往远处的公路,大客车迎来送往,把近处的人送出去,把远处的人接回来;货车把近处的货物运出去,又把外地的货物运进来。每逢农历的双日子,这里都会有集市,远远近近的人们都来这里赶集,陈家湾的人也要来这里赶集,买一些生活用品和农用品。
这一年,汛期来之前,陈家湾的老人们就开始议论水势大小了。有的说,十年一次小水,三十年一次大水,这次涨水小不了。有的说,现在政府管理了,能把大水变成小水。议论这些“天下大事”时,最合适的场合是大柿树下,说话最权威的当然是“老私塾”陈雷生。
陈雷生小时候读过私塾,对周易八卦有些研究,平时喜欢读书看报听广播,是村子里为数不多的老知识分子,外号“老私塾”。当他手里端着旱烟袋朝大柿树走来时,柿树下的人们就会像报幕一样说,老私塾来了。说这话的人是他的平辈或长辈,又因为他在兄弟里排行老三,所以晚辈的“报幕员
”会说,三叔来了或三爷来了。
柿树下有陈雷生的专用座位。柿树的根部突出地面,也不知坐了几朝几代,被磨得油光锃亮,庞大的树冠像遮阳挡雨的伞。背靠着三人合抱粗的柿树,老私塾悠闲地抽着旱烟袋,安静地看着树下的人们,听着他们唠家常、唠农活、唠天下大事。只有当别人说的太过离谱时他才慢慢地磕去烟袋锅子里的灰烬,用毋庸置疑的口气加以纠正。被纠正的人丝毫不觉得难为情,因为老私塾说的话就是真理,接受他的批评、指点和建议,已然成了人们的习惯。他的经验、知识和智慧,是陈家湾的主心骨,人们信任他、尊敬他。每当他走到树下时,那个坐在树根上的人就会站起来,把这个最舒坦的位置让给他,他会客气地和人招呼一声,泰然入座。
午饭后,村里的人忍受不住七月的闷热,陆陆续续来到柿树下乘凉。但他们议论的话题却比天气更沉闷,那就是今年会不会涨水,这是入夏以来最为热点的话题。村里很多人都记得,十年前的那场大水,几乎把陈家湾这艘小船压沉。当时只有100来户人家的陈家湾接待了有着200多户人家的曾家坝人。各家屋里以及房檐下都是曾家坝来的“跑洪”人,这棵大柿树下也密密麻麻地铺着麻袋或草席,住满了人。幸好那次洪水来得急走得也快,只有短短三天时间。三天里,陈家湾倾其所有招待曾家坝的人们,三天后,陈家湾家家米尽粮绝,人们只好以野菜甚至青草充饥,眼巴眼望地等着地里的秋作物赶快成熟。屈指算来,今年的汛期即将到来,而且还是特大洪水的汛期,从六月末开始,人们就开始为曾家坝和自己村庄的命运担心了。
当人们用询问的目光等待老私塾发言时,只见他紧皱眉头抽着嘶嘶作响的旱烟袋,烟袋锅子里的火光时隐时现,人们知道,这时还不是老私塾的发言时间。等到一袋烟抽完,烟袋锅子磕在石块上当当作响时,老私塾才叹了一口气说:“今年的洪水不来便罢,来的话一定不善。”听他说完,空气变得更加沉闷,有人摇头,有人叹气,有人闷闷地抽着烟。这一刻,仿佛时间凝固起来,柿树以及树下的人们都沉默在这凝固的时间里。
这时,忽然传来一个男孩子的哭声,还未变声的小细嗓子加上十足的底气,使得男孩的哭声听起来像高音唢呐,足以响彻半个庄子。当他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从柿树旁走过时,老私塾磕着烟袋说:
“娃子过来,又打架了?” 男孩哭得更响:“我、我没打架,是他们欺负人,他们打我。”
老私塾伸手拉着男孩的胳膊,和蔼地说:“让三爷看看打哪儿了?”
当他碰到男孩的手时,男孩的哭声变得撕心裂肺起来,老私塾仔细一看,原来他的胳膊被人打脱臼了,难怪这孩子哭得这么痛苦。
“这帮土小子太不像话,打人没个轻重。”说着,他趁男孩不注意,一手握着男孩的胳膊,一手捏着胳膊肘的脱臼处,猛的一拉一拽,眨眼工夫男孩的疼痛减轻了,哭声也小了许多。老私塾轻轻揉捏男孩的胳膊说:“他们为什么欺负你?”他知道男孩说的是实话,他肯定是被人欺负了。
男孩一听哭得更伤心了:“我割的草比他们多,他们就说我割了他们的草,他们说草是贫下中农的不是地主的。他们要分我的草,我不让分,他们就喊着打倒地主,就……”
男孩哭得说不下去了,老私塾此时已心如明镜。男孩叫陈玉栋,他爷爷是地主,他也就自然属于地主成分。老私塾亲眼见证了玉栋爷爷当上地主的全过程。那是一个勤谨、老实的庄稼人,1948年H省解放前夕,他倾尽一生积蓄买下了80亩地,收留了一个姓徐的逃荒人做长工,在收了第一茬庄稼后,为长工娶了媳妇,从此和长工互称老表,一块地里干农活,一个锅里涮稀粥,相处十分和睦。
正当长工生养儿子时,解放的春雨落在他头上,为了能够分到陈家的房屋院落,他亲自做了一顶锥形大纸帽戴在玉栋爷爷头上。在批斗会上,他声泪俱下地控诉玉栋爷爷的“罪行”,历数这位老地主剥削他全家人的种种罪恶,凡是他听到的有关地主剥削罪行的故事,都借过来为他所用,他只需把故事里地主的名姓换一下就行了。开始时,村里的人对他的说法很是反感,但因为他有着无比光荣的雇农成分,谁也不敢当面说他什么,人人都在心里骂他不是东西。这个不是东西的东西把自己编造的谎言一遍遍重复后,人们也就充耳不闻,习以为常了。后来,他如愿以偿地把玉栋爷爷一家撵到了生产队的牛棚里,自己成了陈家大院的主人。就这样,玉栋爷爷当了不到一年的地主,却让他的子孙背上了无比沉重的地主成分。
正如人们担心的那样,紧紧慢慢的雨下了七天七夜后,洪水来了,来势非常凶猛。一夜之间,到陈家湾逃难的人像蚂蚁一样遍布全村,能够遮雨的干地上,铺满了草席和麻袋,男女老少躺着的、坐着的,把草席和麻袋挤得满满的,他们随身带的少量食品和行李只能放在被雨水浸透的湿地上。
陈玉栋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是他12岁的时候。大难当前,人们忽略了他家的地主成分,也顾不得和他家划清界限,他家新盖的茅草房里挤满了人,房檐下也是人,院子里有一棵枣树,一棵槐树,都是新栽的,小小树冠下放满了东西,甚至连猪窝也派上了用场,那只刚刚买回来的小猪仔被拉了出来拴在露天的雨地里,略作清理的猪窝里铺上了麦秸,麦秸上铺一张席子,这对困极累极的“跑洪”人来说,也是一张不错的床铺。玉栋爹妈忙不迭地照应着,一会儿屋里一会儿院子里跑来跑去,非常热情。做饭时,每顿饭都要做三锅以上。若是在他爷爷那时,家里大囤小囤都是粮食,招待这么多人还是绰绰有余的。现在不行了,现在他家最值钱的家当是一口米缸、一口面缸和一口水缸。第一天熬的粥还能挂上筷子,第二天就稀了许多,第三天就能照出人影了。三天过后,他家的米缸面缸像用水涮过一样干净。这倒不是因为那些逃难人饭量大,而是因为人太多了。其实,逃难的大人们一般能不吃就不吃了,每家只盛一碗或者两碗稀粥分给小孩吃。
陈玉栋从未见到过他家住这么多人,过去在人们眼中像一堆臭狗屎一样的地主家院忽然吃香了,而且把地主家的米面毫不见外地吃了个精光。这给陈玉栋带来了不小的快乐,这是他童年时代为数不多的快乐之一。
洪水来后的第三天傍晚,陈玉栋背着父母偷偷来到村边。洪水已经退去了很多,被水冲过的玉米、高粱东倒西歪,只有极少数秧苗还孤零零地站立着。那棵碗口粗的高高的楝树像村庄的门卫一样安静地守在那里。陈玉栋熟练地爬上树坐在树杈上远望,想看看那个令他向往的、繁华的曾家坝是否安然无恙。
看着眼前的一切,他惊呆了。雨已经停了下来,西边的云彩泛着暗暗的橘红色,难道太阳在不知不觉中来过?明天该不会下雨了吧?如果远处的水面不是肆虐的洪水,如果近处的黄泥不埋没庄稼,那么眼前的景象可以算得上人间难寻的奇景了。陈家湾真的像一艘船,四周是漫无边际的黄乎乎的水,奇怪的是陈家湾并没有比水平面高出许多,它似乎和水面在一个平行线上。可是一公里外的曾家坝却不见了踪影,只能透过水雾看到一些朦胧的树,往日可以看得一清二楚的房舍罩在了水或水雾中。
“洪水可真厉害啊!难怪人们离开家跑到这里来呢。”陈玉栋一边想着,边从树上下来,可是他的腿软软的,双手也在颤抖,胸中像揣个兔子一样突突乱跳。这时他才意识到,他被看到的一切吓着了,这是他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害怕和恐惧。
大柿树是他回家的必经之路,树下的土湿湿的。天色渐暗,跑洪的人们在树下铺起了床铺,很安静。此时没有人愿意说话,面对洪水带来的灾害,没有人能够阻挡,他们很无奈,很软弱。
陈玉栋绕着柿树转了一圈,没有人认识他,也没有人注意他。他漫无目的地看着这些遭难的人,心中乱乱的,一会儿想想这儿,一会儿又跳到了别处。这里的地面这么湿,他们睡在这里会生病的吧?听说长时间睡在湿地上的人,身上会长痒疙瘩,长痒疙瘩的滋味可不好受;房子被水冲倒,庄稼被水淹,他们回去后住在哪里?吃什么呢?他们会不会像忆苦思甜大会上听到的故事一样,左手拿着破碗,右手拿着打狗棍出去逃荒要饭?想到这里时,他的鼻子酸了一下:“可惜我家太穷了,如果我家富有一些该多好!”他所想象的富有其实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粮食。他这样胡思乱想的时候,突然两个孩子争吵的声音打破了人群的安静。P1-4 ……
有山的地方神话多,有河的地方故事多。从双狮山发源的双狮河支流众多,中下游的清阳河是众支流之一。清阳河也有些与众不同,它的流向是自东向西的,弯弯曲曲的不知从哪里来也不知流向哪里,它以一种优美的曲线展示着独特的姿态和充满自信的长度。不到汛期的河面只有几十米宽,两岸的沙滩与河面的宽度差不多。南岸的河床高出水面二三十米,河堤上面是绵延不断的农田和村落。北岸没有河堤,沙滩的尽头是一片片树林,树林的尽头散落着一个个村庄。沙滩和树林成了北岸居民的河堤,即使河流汛期水涨,他们大多数时候也都是安全的。河边有个村庄绰号舟河,其实叫陈家湾。
传说这条小河每隔十年发一次洪水,每隔三十年发一次特大洪水。每次特大洪水过后,方圆几十里的村庄和农田都会被荡为平地,只有陈家湾除外。陈家湾像一艘永不下沉的奇妙的船,水涨它也涨,因此得名舟河。
在北岸的村庄中,只有陈家湾与树林几乎平行。远远看去,它就在河边上,没有任何安全感。陈家湾北面是相隔一公里的曾家坝,小河涨水时,如果水势小,曾家坝能够幸免于难,如果水势大,河水会把离自己近的陈家湾高高举起,把距离远的曾家坝吞入腹中。但造物主总是公平的,它给了陈家湾不沉的造化,也给了曾家坝繁华的街道。曾家坝是方圆十里乃至几十里的著名街镇。这里有通往远处的公路,大客车迎来送往,把近处的人送出去,把远处的人接回来;货车把近处的货物运出去,又把外地的货物运进来。每逢农历的双日子,这里都会有集市,远远近近的人们都来这里赶集,陈家湾的人也要来这里赶集,买一些生活用品和农用品。
这一年,汛期来之前,陈家湾的老人们就开始议论水势大小了。有的说,十年一次小水,三十年一次大水,这次涨水小不了。有的说,现在政府管理了,能把大水变成小水。议论这些“天下大事”时,最合适的场合是大柿树下,说话最权威的当然是“老私塾”陈雷生。
陈雷生小时候读过私塾,对周易八卦有些研究,平时喜欢读书看报听广播,是村子里为数不多的老知识分子,外号“老私塾”。当他手里端着旱烟袋朝大柿树走来时,柿树下的人们就会像报幕一样说,老私塾来了。说这话的人是他的平辈或长辈,又因为他在兄弟里排行老三,所以晚辈的“报幕员
”会说,三叔来了或三爷来了。
柿树下有陈雷生的专用座位。柿树的根部突出地面,也不知坐了几朝几代,被磨得油光锃亮,庞大的树冠像遮阳挡雨的伞。背靠着三人合抱粗的柿树,老私塾悠闲地抽着旱烟袋,安静地看着树下的人们,听着他们唠家常、唠农活、唠天下大事。只有当别人说的太过离谱时他才慢慢地磕去烟袋锅子里的灰烬,用毋庸置疑的口气加以纠正。被纠正的人丝毫不觉得难为情,因为老私塾说的话就是真理,接受他的批评、指点和建议,已然成了人们的习惯。他的经验、知识和智慧,是陈家湾的主心骨,人们信任他、尊敬他。每当他走到树下时,那个坐在树根上的人就会站起来,把这个最舒坦的位置让给他,他会客气地和人招呼一声,泰然入座。
午饭后,村里的人忍受不住七月的闷热,陆陆续续来到柿树下乘凉。但他们议论的话题却比天气更沉闷,那就是今年会不会涨水,这是入夏以来最为热点的话题。村里很多人都记得,十年前的那场大水,几乎把陈家湾这艘小船压沉。当时只有100来户人家的陈家湾接待了有着200多户人家的曾家坝人。各家屋里以及房檐下都是曾家坝来的“跑洪”人,这棵大柿树下也密密麻麻地铺着麻袋或草席,住满了人。幸好那次洪水来得急走得也快,只有短短三天时间。三天里,陈家湾倾其所有招待曾家坝的人们,三天后,陈家湾家家米尽粮绝,人们只好以野菜甚至青草充饥,眼巴眼望地等着地里的秋作物赶快成熟。屈指算来,今年的汛期即将到来,而且还是特大洪水的汛期,从六月末开始,人们就开始为曾家坝和自己村庄的命运担心了。
当人们用询问的目光等待老私塾发言时,只见他紧皱眉头抽着嘶嘶作响的旱烟袋,烟袋锅子里的火光时隐时现,人们知道,这时还不是老私塾的发言时间。等到一袋烟抽完,烟袋锅子磕在石块上当当作响时,老私塾才叹了一口气说:“今年的洪水不来便罢,来的话一定不善。”听他说完,空气变得更加沉闷,有人摇头,有人叹气,有人闷闷地抽着烟。这一刻,仿佛时间凝固起来,柿树以及树下的人们都沉默在这凝固的时间里。
这时,忽然传来一个男孩子的哭声,还未变声的小细嗓子加上十足的底气,使得男孩的哭声听起来像高音唢呐,足以响彻半个庄子。当他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从柿树旁走过时,老私塾磕着烟袋说:
“娃子过来,又打架了?” 男孩哭得更响:“我、我没打架,是他们欺负人,他们打我。”
老私塾伸手拉着男孩的胳膊,和蔼地说:“让三爷看看打哪儿了?”
当他碰到男孩的手时,男孩的哭声变得撕心裂肺起来,老私塾仔细一看,原来他的胳膊被人打脱臼了,难怪这孩子哭得这么痛苦。
“这帮土小子太不像话,打人没个轻重。”说着,他趁男孩不注意,一手握着男孩的胳膊,一手捏着胳膊肘的脱臼处,猛的一拉一拽,眨眼工夫男孩的疼痛减轻了,哭声也小了许多。老私塾轻轻揉捏男孩的胳膊说:“他们为什么欺负你?”他知道男孩说的是实话,他肯定是被人欺负了。
男孩一听哭得更伤心了:“我割的草比他们多,他们就说我割了他们的草,他们说草是贫下中农的不是地主的。他们要分我的草,我不让分,他们就喊着打倒地主,就……”
男孩哭得说不下去了,老私塾此时已心如明镜。男孩叫陈玉栋,他爷爷是地主,他也就自然属于地主成分。老私塾亲眼见证了玉栋爷爷当上地主的全过程。那是一个勤谨、老实的庄稼人,1948年H省解放前夕,他倾尽一生积蓄买下了80亩地,收留了一个姓徐的逃荒人做长工,在收了第一茬庄稼后,为长工娶了媳妇,从此和长工互称老表,一块地里干农活,一个锅里涮稀粥,相处十分和睦。
正当长工生养儿子时,解放的春雨落在他头上,为了能够分到陈家的房屋院落,他亲自做了一顶锥形大纸帽戴在玉栋爷爷头上。在批斗会上,他声泪俱下地控诉玉栋爷爷的“罪行”,历数这位老地主剥削他全家人的种种罪恶,凡是他听到的有关地主剥削罪行的故事,都借过来为他所用,他只需把故事里地主的名姓换一下就行了。开始时,村里的人对他的说法很是反感,但因为他有着无比光荣的雇农成分,谁也不敢当面说他什么,人人都在心里骂他不是东西。这个不是东西的东西把自己编造的谎言一遍遍重复后,人们也就充耳不闻,习以为常了。后来,他如愿以偿地把玉栋爷爷一家撵到了生产队的牛棚里,自己成了陈家大院的主人。就这样,玉栋爷爷当了不到一年的地主,却让他的子孙背上了无比沉重的地主成分。
正如人们担心的那样,紧紧慢慢的雨下了七天七夜后,洪水来了,来势非常凶猛。一夜之间,到陈家湾逃难的人像蚂蚁一样遍布全村,能够遮雨的干地上,铺满了草席和麻袋,男女老少躺着的、坐着的,把草席和麻袋挤得满满的,他们随身带的少量食品和行李只能放在被雨水浸透的湿地上。
陈玉栋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是他12岁的时候。大难当前,人们忽略了他家的地主成分,也顾不得和他家划清界限,他家新盖的茅草房里挤满了人,房檐下也是人,院子里有一棵枣树,一棵槐树,都是新栽的,小小树冠下放满了东西,甚至连猪窝也派上了用场,那只刚刚买回来的小猪仔被拉了出来拴在露天的雨地里,略作清理的猪窝里铺上了麦秸,麦秸上铺一张席子,这对困极累极的“跑洪”人来说,也是一张不错的床铺。玉栋爹妈忙不迭地照应着,一会儿屋里一会儿院子里跑来跑去,非常热情。做饭时,每顿饭都要做三锅以上。若是在他爷爷那时,家里大囤小囤都是粮食,招待这么多人还是绰绰有余的。现在不行了,现在他家最值钱的家当是一口米缸、一口面缸和一口水缸。第一天熬的粥还能挂上筷子,第二天就稀了许多,第三天就能照出人影了。三天过后,他家的米缸面缸像用水涮过一样干净。这倒不是因为那些逃难人饭量大,而是因为人太多了。其实,逃难的大人们一般能不吃就不吃了,每家只盛一碗或者两碗稀粥分给小孩吃。
陈玉栋从未见到过他家住这么多人,过去在人们眼中像一堆臭狗屎一样的地主家院忽然吃香了,而且把地主家的米面毫不见外地吃了个精光。这给陈玉栋带来了不小的快乐,这是他童年时代为数不多的快乐之一。
洪水来后的第三天傍晚,陈玉栋背着父母偷偷来到村边。洪水已经退去了很多,被水冲过的玉米、高粱东倒西歪,只有极少数秧苗还孤零零地站立着。那棵碗口粗的高高的楝树像村庄的门卫一样安静地守在那里。陈玉栋熟练地爬上树坐在树杈上远望,想看看那个令他向往的、繁华的曾家坝是否安然无恙。
看着眼前的一切,他惊呆了。雨已经停了下来,西边的云彩泛着暗暗的橘红色,难道太阳在不知不觉中来过?明天该不会下雨了吧?如果远处的水面不是肆虐的洪水,如果近处的黄泥不埋没庄稼,那么眼前的景象可以算得上人间难寻的奇景了。陈家湾真的像一艘船,四周是漫无边际的黄乎乎的水,奇怪的是陈家湾并没有比水平面高出许多,它似乎和水面在一个平行线上。可是一公里外的曾家坝却不见了踪影,只能透过水雾看到一些朦胧的树,往日可以看得一清二楚的房舍罩在了水或水雾中。
“洪水可真厉害啊!难怪人们离开家跑到这里来呢。”陈玉栋一边想着,边从树上下来,可是他的腿软软的,双手也在颤抖,胸中像揣个兔子一样突突乱跳。这时他才意识到,他被看到的一切吓着了,这是他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害怕和恐惧。
大柿树是他回家的必经之路,树下的土湿湿的。天色渐暗,跑洪的人们在树下铺起了床铺,很安静。此时没有人愿意说话,面对洪水带来的灾害,没有人能够阻挡,他们很无奈,很软弱。
陈玉栋绕着柿树转了一圈,没有人认识他,也没有人注意他。他漫无目的地看着这些遭难的人,心中乱乱的,一会儿想想这儿,一会儿又跳到了别处。这里的地面这么湿,他们睡在这里会生病的吧?听说长时间睡在湿地上的人,身上会长痒疙瘩,长痒疙瘩的滋味可不好受;房子被水冲倒,庄稼被水淹,他们回去后住在哪里?吃什么呢?他们会不会像忆苦思甜大会上听到的故事一样,左手拿着破碗,右手拿着打狗棍出去逃荒要饭?想到这里时,他的鼻子酸了一下:“可惜我家太穷了,如果我家富有一些该多好!”他所想象的富有其实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粮食。他这样胡思乱想的时候,突然两个孩子争吵的声音打破了人群的安静。P1-4 ……
- 名称
- 类型
- 大小
光盘服务联系方式: 020-38250260 客服QQ:4006604884
云图客服:
用户发送的提问,这种方式就需要有位在线客服来回答用户的问题,这种 就属于对话式的,问题是这种提问是否需要用户登录才能提问
Video Player
×
Audio Player
×
pdf Play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