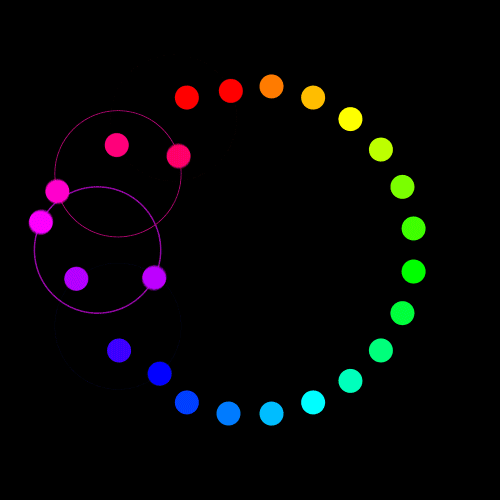微信扫一扫,移动浏览光盘
简介
未来某个时候,世界已经被一些彼此竞争的高科技生物公司所控制,它们开发各种免疫和抗病毒药物,在动物身上进行基因嫁接试验以培育供人类移植用的器官,甚至蓄意研制病毒然后再提供药品以牟取暴利。在网络色情和网络游戏中长大的“秧鸡”是一个危险的天才,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大公司主持一个研制长生不老药物的项目,也许是出于对人类堕落的绝望,“秧鸡”在药物中暗藏了一种致命病毒,同时他在实验室里培育出一种摆脱了所有人类痼疾的草食性新人。当“秧鸡”所设计的病毒大爆发如期而至后,人类在骚乱中走向毁灭,只留下“秧鸡”儿时的朋友“雪人”在世界的废墟上孤独地生活着。作为“秧鸡”设计的新人类的“牧羊人”,“雪人”只能靠在垃圾堆中寻找衣食生存,而且还要小心防备器官猪、狼犬兽之类人造动物的攻击。但最让他不安的还是如何去应对那群天真懵懂的“秧鸡人”,好奇心是否会驱使他们重演人类的历史呢?本书无疑会使人想起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阿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堪称二十一世纪的反面乌托邦。
目录
未来的天空:有没有阳光?
(代 译 序)
江晓原
最近这一年,我大约花了三百小时做一件事。
如今这年头,能在一年中为一件事花三百小时,也算不容易了。
这件事就是看科幻电影。这一年中我看了一百多部科幻电影,主要是美国和欧洲出品的,也有少数日本的。
在这一百多部科幻电影中,我注意到的一个奇怪现象,那就是:这些电影中所幻想的未来世界,清一色都是暗淡而悲惨的。
早期的科幻小说,比如儒勒·凡尔纳在十九世纪后期创作的那些作品,对于未来似乎还抱有信心;不过,在被奉为科幻小说鼻祖的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1818)中,就没有什么光明的未来。而且,儒勒·凡尔纳这种对于未来世界的信心,很快就被另一种挥之不去的忧虑所取代,人类的未来不再是美好的了。比如在英国人h. g. 威尔斯的著名小说《时间机器》(1895)中,主人公乘时间机器到达了公元802701年(!),但是在那时的世界里,文明人早已智力退化,被当作养肥了的畜牲,随时会遭到猎杀。在他的另一部著名小说《星际战争》(1898)中,地球人几乎被入侵的火星人征服。
而在近几十年大量幻想未来世界的西方电影里,未来世界根本没有光明,而是:蛮荒,比如《未来水世界》(water world);黑暗,比如《撕裂的末日》(equilibrium);荒诞,比如《罗根的逃亡》(logan餾 run);虚幻,比如《黑客帝国》(matrix)系列;核灾难,比如《终结者》(terminator)系列;大瘟疫,比如《12猴子》(12 monkeys);等等。
还有一条幻想未来之路,是从《乌托邦》开始的。
自从莫尔的《乌托邦》问世以来,类似的著作颇多,如培根的《新大西岛》、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兰托德的《塞瓦兰人的历史》等等。这些都是对理想社会的设计和描绘,所以这些书里所描绘的社会都是美好的,人民生活幸福,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类似于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我们政治教科书中所说的“空想社会主义”。但是到二十世纪西方文学中,就出现了被称为 “反乌托邦” 的作品。奥威尔的《一九八四》(1948)、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1932)和扎米亚京的《我们》(1924)被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其中前两部名声尤大。
如果说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是从对思想专制的恐惧出发,来营造一个“反乌托邦”,那么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就是从对现代化的担忧出发,来营造另一个“反乌托邦”。
从赫胥黎写《美丽新世界》和奥威尔写《一九八四》,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他们所担忧的“反乌托邦”是否会出现呢?按照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内尔·波斯特曼在他的新作《娱乐至死》中的意见,“奥威尔的预言似乎和我们无关,而赫胥黎的预言正在实现”。他认为有两种方法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不管哪一种,未来都是暗淡的。在这些小说和电影中,未来世界不外三种主题:一、资源耗竭,二、惊天浩劫,三、高度专制。
当年德国中学教师奥斯瓦尔德·施宾格勒写了一部《西方的没落》,一纸风行。在坚信“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的年代,这本书的标题对中国人来说是令人愉快的。但是西方人似乎从来就不讳言他们对未来的忧虑。
再看中国的科幻作品,在这个问题上与西方作品有明显的不同——中国的作品通常幻想一个美妙的未来世界,那里科技高度发达,物质极度丰富。这种差别背后,应该有着深刻的根源。
将科幻视为科普的一部分,应该是原因之一。既然是科普嘛,当然要歌颂科学本身及其一切作用——“科普”这个概念是有一个隐含前提的,就是:科学本身及其一切作用都一定是好的,所以才要普及它。
. 另一个明显的原因,当然就是传统的唯科学主义的强大影响。唯科学主义既相信世间一切问题都可以靠科学技术来解决,这就必然导向一种对人类前途的乐观主义信念。在这个信念支配下,人类社会只能越发展越光明,而且这种发展的向上趋势,通常被假定为线性的,连循环论、周期性之类的模式(比如《时间机器》就是这种模式)也不行。
这种幼稚的乐观主义信念,和早年的空想社会主义颇有关系。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自然科学的辉煌胜利,催生了唯科学主义观念,使许多人相信自然科学法则可以用于对人类社会的研究。比如法国的圣西门、孔德等人,就致力于发现社会发展的“规律”,并相信这种“规律”在精英的直接控制和运用之下,就可以使人类的社会生活尽善尽美。这正是后来哈耶克所担忧的“理性的滥用”。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事实上深刻影响了此后两个世纪的历史进程。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科幻作品中的美好未来世界就很容易理解了——在唯科学主义观念的支配下,未来世界只能是美好的。
前些时候,有人对法国的青少年做了一个问卷调查,这个调查后来也被移植到中国来,中法青少年在有些问题上的答案大相径庭,很值得玩味。比如其中有一题是这样的:“如果你可以在时空隧道中穿行,你愿意选择去哪个时代旅行?”
最大部分的法国青少年愿意选择今天,而不是未来;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只有极少中国青少年愿意选择今天,而最大部分选择的是未来。这和上文所说的情形是一致的:西方人普遍对未来充满忧虑,而中国人普遍对未来抱着幼稚的乐观。
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幻想电影可能起了极大的作用。在上述这个问卷调查中,还有一题问的是“下面这些信息载体中,你最喜欢的是哪一种”,选项有电影、互联网、书籍等,结果最大部分(竟有40%以上)法国青少年选择了“电影”。多数中国青少年则选择了“互联网”——书籍已经被中西方的下一代共同冷落。
和西方许许多多已经问世的科学幻想作品一样,小说《羚羊与秧鸡》所展示的未来世界也是一片愁云惨雾,暗淡无光。
小说叙事的结构是以一个悬念为主线,这个悬念就是:那场浩劫到底是什么?是如何发生的?为此小说有规律地交替变换叙事视角(人称)和时空:
“现在” ——二十世纪下半叶某年,那时人类经历了一场浩劫,所有的人都死光了,只剩下一个叫作“雪人”的人,是一个真实的人类。与他做伴的是一群用生物技术制造出来的、完美无缺的“人”,由于这些“人”是由小说中一个名为“秧鸡”的科学狂人制造出来的,所以就被叫作“秧鸡人”(“秧鸡人”都取了辉煌的历史名人的名字,比如林肯、居里夫人、达·芬奇等等)。此时总是用第三人称,叙述“雪人”和“秧鸡人”的生存活动。此时的生存环境对“雪人”来说已经变得极为险恶。
“过去”——这是动态的,从“雪人”和“秧鸡”的学生时代开始,每一次回到“过去”的场景,这两个男孩就长大一点。从童年、中学时代、大学时代,一直到大学毕业进入公司工作,最终到浩劫发生,与“现在”衔接起来,形成全书的结尾。“雪人”和“秧鸡”是同学,是朋友,是同事,最后“雪人”是“秧鸡”的副手。“过去”总是用“雪人”第一人称回忆的方式叙述,所有“过去”场景所构成的故事,也就是那个悬念逐渐形成又逐渐被揭示的过程。
与许许多多西方的科幻小说和电影一样,《羚羊与秧鸡》中这一系列“过去”的场景,就是一幕人类社会的“末世”场景。
——那时政府似乎已经退隐到无足轻重的地步了(这一点在西方许多科幻小说和电影中是常见的),各个大公司建立了自己的“大院”,里面实验室、宿舍、学校、医院、商店、色情场所等一应俱全,有自己的警察,简直就如同国中之国。原先的都市则成为下层民众生活的地方,小说中称为“杂市”,那里设施破败,治安混乱,人们生活在贫困和无望之中。
——生物工程似乎成为小说中惟一的科学技术。人们让猪身上长满人所需要的器官,所以这些猪被称为“器官猪”,一只“器官猪”身上可以长——比如说吧——六个肾。专门为人类提供鸡肉的“鸡”根本没有脑袋,却能够在一处同时生长十二份鸡胸脯肉,另一处同时生长十二份鸡大腿肉。如此等等。
——所有的疾病都可以被消灭,但是制造药品的大公司为了让人们继续购买药品,不惜研制出病毒并暗中传播。如果有人企图揭发这种阴谋,等待他的就是死亡——“秧鸡”的父亲就是因此被谋杀的。
——文学艺术已经遭到空前的鄙视,只有科学技术(其实只有生物工程)成为天之骄子。吉米和“秧鸡”从同一个中学毕业,但是理科成绩优异的“秧鸡”被沃森—克里克学院——这是以双螺旋模型的发现者命名的学院,一看就知道是搞生物学的——以优厚的奖学金挖走,而喜欢文学艺术的吉米则勉强被玛莎·格雷厄姆学院接受。小说描述了这两个学院之间的天壤之别:沃森—克里克学院设施完善,待遇优厚,玛莎·格雷厄姆学院则一派破落光景。这实际上象征着如今我们已经看得相当清楚的趋势:人文学术日益遭到轻视,而科学技术则盛气凌人。
——色情网站和大麻毒品泛滥无边,中学生们把这些东西看成家常便饭。“雪人”——学生时代他被称为“吉米”,大学毕业后被称为“吉姆”——就是在访问色情网站时认识本书的另一位主人公“羚羊”的。她是一个六七岁时被人从印尼买来从事色情业的女孩,后来成为“雪人”的恋人,同时也成为“秧鸡”的女人。
——当最后病毒在全世界各处同时爆发时,所有的人类都在短短几天内死亡,人类文明突然之间陷于停顿、瘫痪。“雪人”和那群“秧鸡人”靠着“秧鸡”事先预备好的应急装置才得以幸存。策划了这场浩劫的“秧鸡”自己最终死在了“雪人”枪下。人类文明在滥用技术、放纵贪欲的疯狂之下宣告终结。
西方许多被我们归入“科幻”的作品,其实是被当作文学作品来创作的,作为一个文学家,在人类前途这个问题上,当然有可能持某种悲观主义的哲学观点。但是,将西方科幻作品中普遍的悲观主义理解为“西方作家对于人类命运的一种深层忧虑,一种责任感”,这只能提供部分的解释——难道西方作家在这个问题上竟没有人愿意标新立异、独弹异调吗?难道他们普遍对人类文明的未来没有信心了吗?
我们当然不能排除西方科幻作品中有光明未来的可能性,但这样的作品非常之少是可以肯定的——我本人看了一百多部西方科幻电影,没有一部是有着光明未来的。结尾处,当然会伸张正义、惩罚邪恶,但编剧和导演从来不向观众许诺一个光明的未来。这么多的编剧和导演,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却在这个问题上如此高度一致,这对于崇尚多元化的西方文化来说,确实是一个奇怪的现象。
对这种现象如何理解?它意味着什么?
读《羚羊与秧鸡》很容易使人联想起“玩火自焚”这句成语,其实这句成语正是古人关于滥用技术的一个寓言。在文明肇始之初,火,就是那个时代的“高科技”,就是那个时代的先进技术,而那个落得自焚下场的人,是因为他“玩”火。夫玩者,不慎重也,不认真对待也,不考虑后果也,总而言之,即滥用也。在《羚羊与秧鸡》中,聪明能干、少年得志的生物学家“秧鸡”,就是这样一个玩火者——他玩的“火”是病毒,是生物工程。这把火烧毁了整个人类文明。
以前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曾经将科幻当作“科普”的一种形式,因为仍然陷溺在传统“科普”的老套之中,只看见科学知识,却没有人文关怀,所以我们自己创作出来的科幻作品,只是一味歌颂科学技术在未来将如何伟大辉煌。而西方那些科幻作品,则很长时间未能引入(只有儒勒·凡尔纳那些对未来乐观的小说得到了特殊待遇)。但是,如今兴起的科学文化传播,早已超越了传统的“科普”概念——可以这样说,有无人文关怀,是科学文化传播和传统“科普”的分界线。
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这些科幻小说和电影中经常出现的对技术滥用的深切担忧,对未来世界的悲观预测,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正是对科学技术的人文关怀的集中表现。这些小说和电影无疑是科学文化传播中的一种类型,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类型。
西方人如今在大部分领域还处于强势,却对未来缺乏积极的信念;中国人积贫积弱百余年,现在也仍是发展中国家,却对未来充满信心,这一对比从表面上看颇有反讽意义。然而,随着中国的富强,我们科幻作品中的基调,是不是也会逐渐告别盲目的乐观主义,开始表达我们自己的人文关怀呢?事实上,这样的作品已经开始在中国出现了。
2004年11月11日
于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
(代 译 序)
江晓原
最近这一年,我大约花了三百小时做一件事。
如今这年头,能在一年中为一件事花三百小时,也算不容易了。
这件事就是看科幻电影。这一年中我看了一百多部科幻电影,主要是美国和欧洲出品的,也有少数日本的。
在这一百多部科幻电影中,我注意到的一个奇怪现象,那就是:这些电影中所幻想的未来世界,清一色都是暗淡而悲惨的。
早期的科幻小说,比如儒勒·凡尔纳在十九世纪后期创作的那些作品,对于未来似乎还抱有信心;不过,在被奉为科幻小说鼻祖的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1818)中,就没有什么光明的未来。而且,儒勒·凡尔纳这种对于未来世界的信心,很快就被另一种挥之不去的忧虑所取代,人类的未来不再是美好的了。比如在英国人h. g. 威尔斯的著名小说《时间机器》(1895)中,主人公乘时间机器到达了公元802701年(!),但是在那时的世界里,文明人早已智力退化,被当作养肥了的畜牲,随时会遭到猎杀。在他的另一部著名小说《星际战争》(1898)中,地球人几乎被入侵的火星人征服。
而在近几十年大量幻想未来世界的西方电影里,未来世界根本没有光明,而是:蛮荒,比如《未来水世界》(water world);黑暗,比如《撕裂的末日》(equilibrium);荒诞,比如《罗根的逃亡》(logan餾 run);虚幻,比如《黑客帝国》(matrix)系列;核灾难,比如《终结者》(terminator)系列;大瘟疫,比如《12猴子》(12 monkeys);等等。
还有一条幻想未来之路,是从《乌托邦》开始的。
自从莫尔的《乌托邦》问世以来,类似的著作颇多,如培根的《新大西岛》、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兰托德的《塞瓦兰人的历史》等等。这些都是对理想社会的设计和描绘,所以这些书里所描绘的社会都是美好的,人民生活幸福,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类似于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我们政治教科书中所说的“空想社会主义”。但是到二十世纪西方文学中,就出现了被称为 “反乌托邦” 的作品。奥威尔的《一九八四》(1948)、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1932)和扎米亚京的《我们》(1924)被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其中前两部名声尤大。
如果说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是从对思想专制的恐惧出发,来营造一个“反乌托邦”,那么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就是从对现代化的担忧出发,来营造另一个“反乌托邦”。
从赫胥黎写《美丽新世界》和奥威尔写《一九八四》,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他们所担忧的“反乌托邦”是否会出现呢?按照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内尔·波斯特曼在他的新作《娱乐至死》中的意见,“奥威尔的预言似乎和我们无关,而赫胥黎的预言正在实现”。他认为有两种方法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不管哪一种,未来都是暗淡的。在这些小说和电影中,未来世界不外三种主题:一、资源耗竭,二、惊天浩劫,三、高度专制。
当年德国中学教师奥斯瓦尔德·施宾格勒写了一部《西方的没落》,一纸风行。在坚信“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的年代,这本书的标题对中国人来说是令人愉快的。但是西方人似乎从来就不讳言他们对未来的忧虑。
再看中国的科幻作品,在这个问题上与西方作品有明显的不同——中国的作品通常幻想一个美妙的未来世界,那里科技高度发达,物质极度丰富。这种差别背后,应该有着深刻的根源。
将科幻视为科普的一部分,应该是原因之一。既然是科普嘛,当然要歌颂科学本身及其一切作用——“科普”这个概念是有一个隐含前提的,就是:科学本身及其一切作用都一定是好的,所以才要普及它。
. 另一个明显的原因,当然就是传统的唯科学主义的强大影响。唯科学主义既相信世间一切问题都可以靠科学技术来解决,这就必然导向一种对人类前途的乐观主义信念。在这个信念支配下,人类社会只能越发展越光明,而且这种发展的向上趋势,通常被假定为线性的,连循环论、周期性之类的模式(比如《时间机器》就是这种模式)也不行。
这种幼稚的乐观主义信念,和早年的空想社会主义颇有关系。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自然科学的辉煌胜利,催生了唯科学主义观念,使许多人相信自然科学法则可以用于对人类社会的研究。比如法国的圣西门、孔德等人,就致力于发现社会发展的“规律”,并相信这种“规律”在精英的直接控制和运用之下,就可以使人类的社会生活尽善尽美。这正是后来哈耶克所担忧的“理性的滥用”。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事实上深刻影响了此后两个世纪的历史进程。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科幻作品中的美好未来世界就很容易理解了——在唯科学主义观念的支配下,未来世界只能是美好的。
前些时候,有人对法国的青少年做了一个问卷调查,这个调查后来也被移植到中国来,中法青少年在有些问题上的答案大相径庭,很值得玩味。比如其中有一题是这样的:“如果你可以在时空隧道中穿行,你愿意选择去哪个时代旅行?”
最大部分的法国青少年愿意选择今天,而不是未来;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只有极少中国青少年愿意选择今天,而最大部分选择的是未来。这和上文所说的情形是一致的:西方人普遍对未来充满忧虑,而中国人普遍对未来抱着幼稚的乐观。
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幻想电影可能起了极大的作用。在上述这个问卷调查中,还有一题问的是“下面这些信息载体中,你最喜欢的是哪一种”,选项有电影、互联网、书籍等,结果最大部分(竟有40%以上)法国青少年选择了“电影”。多数中国青少年则选择了“互联网”——书籍已经被中西方的下一代共同冷落。
和西方许许多多已经问世的科学幻想作品一样,小说《羚羊与秧鸡》所展示的未来世界也是一片愁云惨雾,暗淡无光。
小说叙事的结构是以一个悬念为主线,这个悬念就是:那场浩劫到底是什么?是如何发生的?为此小说有规律地交替变换叙事视角(人称)和时空:
“现在” ——二十世纪下半叶某年,那时人类经历了一场浩劫,所有的人都死光了,只剩下一个叫作“雪人”的人,是一个真实的人类。与他做伴的是一群用生物技术制造出来的、完美无缺的“人”,由于这些“人”是由小说中一个名为“秧鸡”的科学狂人制造出来的,所以就被叫作“秧鸡人”(“秧鸡人”都取了辉煌的历史名人的名字,比如林肯、居里夫人、达·芬奇等等)。此时总是用第三人称,叙述“雪人”和“秧鸡人”的生存活动。此时的生存环境对“雪人”来说已经变得极为险恶。
“过去”——这是动态的,从“雪人”和“秧鸡”的学生时代开始,每一次回到“过去”的场景,这两个男孩就长大一点。从童年、中学时代、大学时代,一直到大学毕业进入公司工作,最终到浩劫发生,与“现在”衔接起来,形成全书的结尾。“雪人”和“秧鸡”是同学,是朋友,是同事,最后“雪人”是“秧鸡”的副手。“过去”总是用“雪人”第一人称回忆的方式叙述,所有“过去”场景所构成的故事,也就是那个悬念逐渐形成又逐渐被揭示的过程。
与许许多多西方的科幻小说和电影一样,《羚羊与秧鸡》中这一系列“过去”的场景,就是一幕人类社会的“末世”场景。
——那时政府似乎已经退隐到无足轻重的地步了(这一点在西方许多科幻小说和电影中是常见的),各个大公司建立了自己的“大院”,里面实验室、宿舍、学校、医院、商店、色情场所等一应俱全,有自己的警察,简直就如同国中之国。原先的都市则成为下层民众生活的地方,小说中称为“杂市”,那里设施破败,治安混乱,人们生活在贫困和无望之中。
——生物工程似乎成为小说中惟一的科学技术。人们让猪身上长满人所需要的器官,所以这些猪被称为“器官猪”,一只“器官猪”身上可以长——比如说吧——六个肾。专门为人类提供鸡肉的“鸡”根本没有脑袋,却能够在一处同时生长十二份鸡胸脯肉,另一处同时生长十二份鸡大腿肉。如此等等。
——所有的疾病都可以被消灭,但是制造药品的大公司为了让人们继续购买药品,不惜研制出病毒并暗中传播。如果有人企图揭发这种阴谋,等待他的就是死亡——“秧鸡”的父亲就是因此被谋杀的。
——文学艺术已经遭到空前的鄙视,只有科学技术(其实只有生物工程)成为天之骄子。吉米和“秧鸡”从同一个中学毕业,但是理科成绩优异的“秧鸡”被沃森—克里克学院——这是以双螺旋模型的发现者命名的学院,一看就知道是搞生物学的——以优厚的奖学金挖走,而喜欢文学艺术的吉米则勉强被玛莎·格雷厄姆学院接受。小说描述了这两个学院之间的天壤之别:沃森—克里克学院设施完善,待遇优厚,玛莎·格雷厄姆学院则一派破落光景。这实际上象征着如今我们已经看得相当清楚的趋势:人文学术日益遭到轻视,而科学技术则盛气凌人。
——色情网站和大麻毒品泛滥无边,中学生们把这些东西看成家常便饭。“雪人”——学生时代他被称为“吉米”,大学毕业后被称为“吉姆”——就是在访问色情网站时认识本书的另一位主人公“羚羊”的。她是一个六七岁时被人从印尼买来从事色情业的女孩,后来成为“雪人”的恋人,同时也成为“秧鸡”的女人。
——当最后病毒在全世界各处同时爆发时,所有的人类都在短短几天内死亡,人类文明突然之间陷于停顿、瘫痪。“雪人”和那群“秧鸡人”靠着“秧鸡”事先预备好的应急装置才得以幸存。策划了这场浩劫的“秧鸡”自己最终死在了“雪人”枪下。人类文明在滥用技术、放纵贪欲的疯狂之下宣告终结。
西方许多被我们归入“科幻”的作品,其实是被当作文学作品来创作的,作为一个文学家,在人类前途这个问题上,当然有可能持某种悲观主义的哲学观点。但是,将西方科幻作品中普遍的悲观主义理解为“西方作家对于人类命运的一种深层忧虑,一种责任感”,这只能提供部分的解释——难道西方作家在这个问题上竟没有人愿意标新立异、独弹异调吗?难道他们普遍对人类文明的未来没有信心了吗?
我们当然不能排除西方科幻作品中有光明未来的可能性,但这样的作品非常之少是可以肯定的——我本人看了一百多部西方科幻电影,没有一部是有着光明未来的。结尾处,当然会伸张正义、惩罚邪恶,但编剧和导演从来不向观众许诺一个光明的未来。这么多的编剧和导演,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却在这个问题上如此高度一致,这对于崇尚多元化的西方文化来说,确实是一个奇怪的现象。
对这种现象如何理解?它意味着什么?
读《羚羊与秧鸡》很容易使人联想起“玩火自焚”这句成语,其实这句成语正是古人关于滥用技术的一个寓言。在文明肇始之初,火,就是那个时代的“高科技”,就是那个时代的先进技术,而那个落得自焚下场的人,是因为他“玩”火。夫玩者,不慎重也,不认真对待也,不考虑后果也,总而言之,即滥用也。在《羚羊与秧鸡》中,聪明能干、少年得志的生物学家“秧鸡”,就是这样一个玩火者——他玩的“火”是病毒,是生物工程。这把火烧毁了整个人类文明。
以前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曾经将科幻当作“科普”的一种形式,因为仍然陷溺在传统“科普”的老套之中,只看见科学知识,却没有人文关怀,所以我们自己创作出来的科幻作品,只是一味歌颂科学技术在未来将如何伟大辉煌。而西方那些科幻作品,则很长时间未能引入(只有儒勒·凡尔纳那些对未来乐观的小说得到了特殊待遇)。但是,如今兴起的科学文化传播,早已超越了传统的“科普”概念——可以这样说,有无人文关怀,是科学文化传播和传统“科普”的分界线。
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这些科幻小说和电影中经常出现的对技术滥用的深切担忧,对未来世界的悲观预测,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正是对科学技术的人文关怀的集中表现。这些小说和电影无疑是科学文化传播中的一种类型,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类型。
西方人如今在大部分领域还处于强势,却对未来缺乏积极的信念;中国人积贫积弱百余年,现在也仍是发展中国家,却对未来充满信心,这一对比从表面上看颇有反讽意义。然而,随着中国的富强,我们科幻作品中的基调,是不是也会逐渐告别盲目的乐观主义,开始表达我们自己的人文关怀呢?事实上,这样的作品已经开始在中国出现了。
2004年11月11日
于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
Oryx and Crake
- 名称
- 类型
- 大小
光盘服务联系方式: 020-38250260 客服QQ:4006604884
云图客服:
用户发送的提问,这种方式就需要有位在线客服来回答用户的问题,这种 就属于对话式的,问题是这种提问是否需要用户登录才能提问
Video Player
×
Audio Player
×
pdf Play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