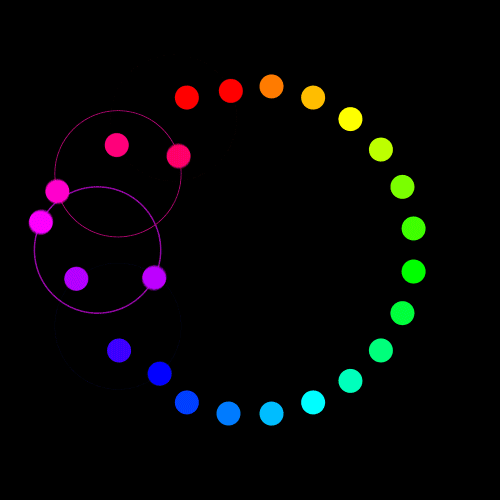001 众多家珍细数来
042 我与建院共成长
047 一代大师杨宽麟
058 长留念记在人间
071 故土中华忆揽洪
086 怀念陈占祥先生
096 忆设计大师胡总
104 敢乘东风学少年
117 行业泰斗王时煦
128 深切铭记是师恩
145 热血青年 建筑名师
159 回忆梅葆琛高工
172 忆恩师和引路人
187 敬贺伟成老九十寿诞
201 马到成功忆宋融
207 回忆程懋堃大师
220 贺观张老八十寿
229 绘景留情读画记
235 宽沟廿年巧运筹
242 画品与人品
252 从《城与园》到《城与年》
266 凤凰台上凤凰游
276 和王兵在一起的日子
288 朴实无华见联想
296 筒子楼 22 年记
307 后 记
【书摘与插画】
怀念陈占祥先生
陈占祥先生走了。和他告别的那天我正好出差,只好托人向陈先生的公子陈衍庆学长转致自己的慰问。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陈先生的名字对有 些人来说可能有点陌生了。陈先生是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在20世纪50年代有名的“八大总”之一(尽管只有短短的三年),并且在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生活了25年。作为后辈,借此机会写些自己的回忆和感受,也是对陈先生的纪念。
在当年的“八大总”中,陈先生和杨宽麟先生一起负责第五设计室,陈先生任室副主任。20世纪60年代我分配来建院时,正好也分在第五设计室,但那时杨、陈二位先生都已不在室里了。杨先生大概已经退休,只是在他偶尔来院参加“运动”时,远远望见过几次;而陈先生经过 1957 年的运动,以“获罪之身”离开了技术领导岗位,经过昌平沙岭的劳动“改造”,为了发挥他的一技之长,在院供应室翻译组做技术情报和建筑理论方面的工作,但五室的老同志还经常谈起杨、陈二位先生在室里时的逸闻趣事。
陈先生给我留下的*深刻的印象就是他那黝黑并富有漫画感的面庞了。将其面色形容为“黑铁色”也不为过,但在眼镜片后面却闪烁着机敏甚至有点狡黠的眼神。另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陈先生的英文。陈先生曾在英国留学八年,略带沙哑的英国标准发音为许多人所称道。据说那时许多援外工程图纸上的英文译文都需要陈先生来*后审定,这样外事部门就很少再来过问,陈先生表现出了作为审定人的权威性。可有一件事我一直也没弄清楚,就是为什么陈先生能说一口标准的英语,可他那江浙口音却让人听着有点费劲。
陈先生是在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撤销之前几个月调任建院副总建筑师的,在室里主管过建国门外使馆区和社会路的沿街建筑的设计施工。当时的使馆区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批使馆,除波兰、捷克使馆是由他们国家自行设计的,可称是新中国成立后较早的中外建筑交流之外,其他使馆都是建院设计的,皆是方整的体形、厚重的砖墙四坡顶。社会路的一组建筑都是多层的,用青砖砌筑。我觉得这些都明显受当时苏联流行的一些样式影响,采用三段式古典手法。但在细部加上一些须弥座上的莲瓣等,看上去比例适当,整体性强。但到 1957年时,一切就都变得急转直下了。
这一切都源于陈先生在“鸣放”时写的一张不到1500字的大字报——《建筑师还是描图机器》。40多年过去了,一切都成了历史,但我想摘录一些当年那张大字报的内容:
建筑设计应当是创造性的脑力劳动,这是我们这一行的基本特征。不承认这一基本特征,工作准出毛病。
这多少年来我们设计了多少万平方米的建筑,速度是超音速。按理说这么多的设计实践早应锻炼出不少大师来,但是在旧社会里,即使是成功的建筑师,其一生的业务很可能勉强抵上我们院里一组一年的任务。瞧瞧我们的作品,屈指算算向科学进军的日益在缩短着的期限,真是令人心寒。这些散布在美好大地上的官方建筑——这是上海某些同行送给我们的帽子,指我们的设计呆板无味,死气重重而言,看来这帽子很合适——群众看不上眼,亦用不惯,我们自己何尝满意。长此以往尽管平方米数足够吓倒任何先进国家,离国际水平依然甚远,至于几年赶上,我看休想!
这么大的功绩应当归功于巨大的组织工作,居然把建筑师变成了描图机器!
当然这一毛病领导上要看出了,所以要求提高质量,这是正确的。在旧有的这个框子下——指的是这一巨大的机器——加上更多这样那样的措施,结果是使人透不过气来。效果呢?让我先占卜一下,我说凶多吉少。
怎么办 ? 让我们大家鸣放吧。
我希望不要给我们什么工时指标而是给我们创造更好些的工作条件。问题很复杂,这里要牵涉到任务统一等等。
我希望院内管得少些,统得少些。这里有许多工作制度问题,我主张设计室和他的设计人员有更多的自决权。
我希望以政策作为创造的指导,让大家多修些人工纪念碑。让我们拿出全盘脑力来设计出适用、经济,可能条件下美观的建筑物贡献给人民。非但有纪念碑而且有奖——我是比较庸俗的,认为钱非谈不可,错了的话,检讨受处分都心服口服。
我希望领导真正了解我们这个行业,看来这是被人误解的一个行业,否则我们怎么会变成描图机器呀!……
针对这些言论,建院、北京市、建筑界对他进行了多次大会小会的批判,同时还要联系家庭出身、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和经历、在都委会的一些主张和言论,当然还有一个“陈华反党联盟”,尽管大家也知道陈占祥和华揽洪二位先生“过去是很不对头,经常闹意见的”。梁思成先生对此也爱莫能助,只能对陈先生说:“你为什么这样糊涂啊?”
我们见到陈先生时,那些疾风暴雨的批判早已过去多年。“文革”时他50多岁,经过长期的锻炼和“改造”,也已经摘去“右派”帽子,但看得出他仍非常谨慎小心,香烟抽得非常凶,帽子压得低低的,常穿的风衣还要把领子竖起来紧裹在身上,一副“破帽遮颜过闹市”的样子。当然,我们对他也存有一些“戒心”。但在翻译组,他却发挥了外文优势做了大量工作。记得那时为了配合院里的重点工程,翻译组都整理出十分详尽细致的专题情报材料。当时英文资料比较缺少,他就千方百计到各个图书馆去查找。据张莉芬同志回忆,当年设计首都体育馆人工冰场,是国内*个室内冰场。当时有关技术资料十分缺少,就是陈先生各处查阅外文资料,为设计工作提供了详尽的技术保证。
其实陈先生擅长的是城市规划,他从22 岁(1938 年)时起赴英留学,攻读城市设计和都市规划,1944年师从英国“大伦敦规划”的主持人、著名规划学家阿尔康培爵士,协助完成英国三座城市的区域规划并获好评。1946年他本想应邀来北平负责都市计划工作,但回国后被留在了南京;1947年还和另外四位留英的建筑师一起成立了“五联建筑与计划研究所”,其中陆谦受先生曾是上海外滩中国银行的设计师,王大闳先生留英后又去美国哈佛大学学习。上海解放后,陈先生给梁思成先生写信,愿意北上从事规划工作。在建院他也向同事们说过:“那时我并不是有多高觉悟,只想到自己学的是城市规划,应在这方面有所发挥。”梁先生在 1949年9月19日给北平市市长聂荣臻的信中还专门做了举荐:“我因朱总司令的关怀,又受曹言行局长的催促,由沪宁一带很费力地找来了二十几位青年建筑师。此外在各部门做领导工作的,也找来了几位,有拟聘的建筑公司总建筑师吴景祥先生,拟聘的建设局企划处处长陈占祥先生,总企划师黄作燊先生以及自由职业的建筑师赵深先生。各位在建筑学上都是有名气的人才。”梁先生还专门提道:“陈占祥先生在英国随名师研究都市计划学,这在中国是极少有的。”梁先生对陈先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样陈先生举家于 1949年10月到达北京,他随即参加了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工作,并在1951年任都委会企划处处长。当时陈先生35岁。
陈先生到达北京以后,即参加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的研究,并于1950年2月正式提出《建议》。由于陈先生“反右”以后的身份,所以长期以来大家都是只知梁而不知陈,只有在梁先生的《梁思成文集》出版以后才知道陈先生也在其中。这份2.6万字的《建议》的主要内容就是希望早日决定首都行政中心区所在地,并请考虑按实际的要求和发展上的有利条件,在城外西郊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地区建政府行政中心区。在《建议》的*后,连用了八个“为着”开头的排比句子来表示
他们的殷切之心:“我们相信,为着解决北京市的问题,使它能平衡地发展来适应全面性的需要;为着使政府机关各单位间得到合理的且能增进工作效率的布置;为着工作人员住处与工作地区的便于来往的短距离;为着避免一时期中大量迁移居民;为着适宜地保存旧城市的
文物;为着减低城内人口过高的密度;为着长期保持街道的正常交通量;为着建立便利而又艺术的新首都,现时西郊这个地区都完全能够适合条件。”现在看来,这些都是北京市发展中所时刻需要面对的问题。当然还有一种意见主张行政中心应设在旧城,认为充分利用旧城的生活服务设施和城市基础设施可以大大节省建设投资,对北京城既充分利用旧的,又建新的能避免旧城的衰落,使旧城更加壮美。持这种意见的有苏联专家和国内另一些专家。
据陈先生回忆,《建议》中梁先生原拟把新市中心设在西郊五棵松一带。那儿是在1938 年抗日战争时为了避免日本人与中国人混居而经营的“居留民地”,陈先生认为当时这种做法距城区太远,是置旧城区的开发于不顾,不如把西郊三里河作为新的行政中心,把钓鱼台、八一湖等组织成新的绿地和公园,同时把南面的莲花池也组织进来。这样形成了梁、陈联名的《建议》。但在*后上报中央的意见中认为行政中心放在旧城区“是在北京市已有的基础上,考虑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情况及现实的需要与可能的条件以达到新首都的合理意见,而郊外另建新的行政中心的方案则偏重于主观愿望,对实际可能条件估计不足,是不能采取的”,这样从总体框架上决定了北京市今后的发展和命运,从而否定了梁、陈的《建议》。陈先生回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梁先生觉得他们的《建议》对旧城区中心改建的可能性考虑不多,于是又和陈先生等研究在以天安门为中心的皇城周围规划,试图以城内“三海”为重点,南面与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的中轴线相连接,融合为一体。但这一补充方案却始终没有公开。陈先生回忆说:“我是确切地知道它的存在的。因为有些图纸是我画的。”他还记得当时对团城下的金鳌玉桥和景山前红墙的改建方案,并且梁先生不顾多病之身亲自着色,和大家干了一个通宵画彩色渲染图,*后完成1∶200比例的通长画卷。
1953年,当时的都委会还责成华揽洪和陈占祥先生分别组织人员编制了北京市总体规划的两种设想(见本书第75页)。陈先生的方案保持了旧城棋盘式道路格局,旧城外的放射路与旧城环路相交,铁路不插入旧城,并把行政办公区集中在平安里、东四十条、菜市口、磁器口所围合的范围之内。此后又专门成立了畅观楼小组对总体规划的两个方案进行综合修改,于12月提出《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由北京市委上报中央。但陈、华二先生都没有参加方案的研究,这个*后草案较系统地借鉴了苏联城市规划的经验,并聘请
苏联专家巴拉金做指导。等到国家计委对规划草案审议并向中央提出意见报告时,陈先生即将离开都委会,调到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了。
陈先生由梁先生举荐来北京,而“反右”时的建筑学会的批判会也是梁先生主持的。但陈先生回忆梁先生从未因他的“右派”身份而有所顾忌,每次批判会后“梁先生对我总是鼓励多于批判”。更让陈先生难忘的是,1971年梁先生病重住院见到来探望的陈先生时,还鼓励陈先生要向前看,千万不能对祖国失去信心。他告诉陈先生不管人生旅途中有多大的坎坷,对祖国一定要忠诚,要为祖国服务,但在学术思想上要有自己的信念。陈先生实际上也是一直这样做的,不管是“文革”时的冲击,还是下放时面对种种生活上的困难,比如在西直门大杂院里的居住条件,一张餐桌除吃饭之外,还要兼作睡觉之用等,他都能坦然处之。据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介绍,陈先生1987年退休后,于1988年赴美国。1989年他拒绝了美国方面的挽留,返回祖国,表现了陈先生热爱祖国的赤诚之心。他也正是按梁先生的“宝贵遗言”去做的。
在关于“反右”的问题改正和落实政策之后,陈先生于1979年调任国家城建总局城市规划研究所(现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任顾问总工程师。此后的20多年中,又可以经常在一些杂志上看到陈先生的文章了。1980年年初,陈先生对北京城市规划中的首都性质和城市规模发表了意见。这时陈先生又能公开并坦率地表明自己的观点了,如首都规划体制的改革问题,对于首都作为外事活动中心(当时还没有国际化城市的提法)的应对措施,首都发展“第三级工业”(即第三产业)的问题以及城市规模必须按照规律来控制等。这些都是关于北京城市发展中的一些很有前瞻性、预见性的看法。
陈先生还重译了《雅典宪章》,新译了《马丘比丘宪章》。这两个对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有极大影响、极大指导作用的重要文献被介绍给我们以后,其中的许多观点和原则都为我们所接受,关于休闲、交通运输、城市增长、城市设计、文物和遗产的保护、环境保护等课题已成为人们研究和关注的热点。陈先生离开建院以后,见到他的机会比较少了,常常只能在一些学术性的会议和需要他出面的场合上见到他,但都没有机会多谈。虽然那时陈先生比在建院时胖了一些,但风采依旧,面色依旧,机敏而幽默的眼神依旧,并且爽朗的笑声更多了。
陈先生的规划思想和学术观点,还需要进一步总结和研究。他重视规划理论研究,强调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主张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协调统一,重视建筑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他的许多主张和看法,经过时间和实践检验,也被人们看得越来越清楚。
*后集成数句作为这篇纪念文章的结束:
负笈英伦报国回,怀志京华演城规。
新区运筹分内外,故都营造求是非。
书生总为直言累,大匠难免长年悲。
且喜厄运皆昨日,伏枥老骥奋蹄追。
2001 年 5 月
(本文原刊于《建筑创作》2001 年第 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