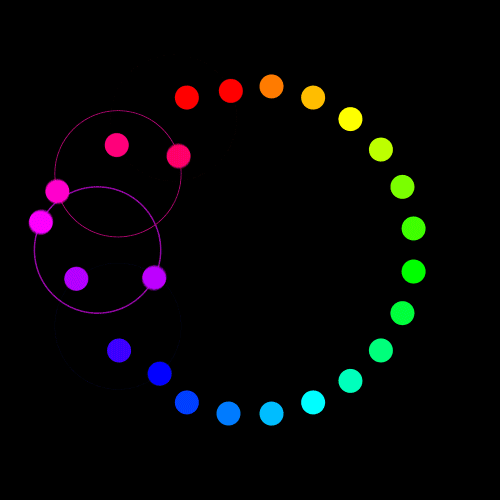简介
莫泊桑是世界著名的短篇小说家,有“世界短篇小说之王”的美称。本书收录了他包括《羊脂球》、《项链》、《我的叔叔于勒》等在内的三十篇著名短篇小说。莫泊桑短篇小说的内容十分丰富。在他笔下,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事件、包罗万象的社会生活,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都得到了精雕细琢式的描写;各种场景,如奢华的上层聚会、精致的中产阶级沙龙、淳朴自然的村落、喧哗热闹的集镇,也都得到了生动的写照。可以说,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是一幅19世纪后半叶法国的社会风俗画,是整个社会的精微缩影。
【免费在线读】
羊脂球
一连好几天,许多溃军残部都在卢昂的市区里穿过。他们简直不能算是军队,只能说是散兵游勇。士兵们脸上的胡子全都又脏又长,身上的军服也都破烂不堪,既没有团队旗帜,也没有团队的番号。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向前走着,全都像是被压折了脊梁的落水狗一样无精打采,既不知道想什么,也不知道干什么,完全是习惯性地朝前走着,仿佛一停下来就会立刻倒地不起。
当然,我们所看到的,绝大多数是因战争动员而应召入伍的人,以及那些素以机警出名而奉命出战的国民卫队。前者都是生来就爱好和平的人,依靠固定收入生活的安分守己的人,他们大都扛着步枪躬着身子;而后者则是胆小怕死又易于冲动的人,他们一方面随时准备冲锋,一方面又随时准备开小差。而且在这两类人中间,还有几个红裤子步兵,他们都是在一场恶战中某个步兵师被歼后仅有的残余;另外还有许多垂头丧气的炮兵,也跟这些番号不同的步兵混杂在一起;偶尔也有几个头戴闪闪发光的铜盔的龙骑兵,拖着笨重的脚步跟在步兵们的步伐后面吃力地走着。
许多义勇军也以种种壮烈的名号成立了,他们的名号是:失败复仇队、墟墓公民队、死亡分享队,也都带着土匪的神气走过。
他们的首领,有些原本是做呢绒或粮食生意的商人,有些则是歇业的牛油贩子或者肥皂贩子。战争爆发以后,他们全都成了应运而生的战士,由于他们有银元或者长胡子,都做了军官。他们高谈阔论地讨论着作战计划,甚至吹嘘说:危亡关头的法国只能依靠他们的肩膀才能支撑下去。不过,有时候他们也很害怕他们的部下——那些常常因为过于凶悍而喜欢抢劫和胡闹的强徒。
普鲁士人快要攻进卢昂市区了,有人说。
两个月来,本市的国民卫队已经很谨慎地在附近各处山林里做过许多侦察工作,偶尔还放枪误伤了自己的哨兵,有时候即便遇着一只在荆棘丛中动弹的小兔子,他们也会预备作战。现在倒好,他们全都解散回家了。至于那些军械和服装,以及从前被他们拿到市郊三法里一带国道边上吓唬老百姓的凶器,现在却一下子都不见了。
法国最后的那些士兵终于渡过了塞纳河,从汕塞韦和布尔阿沙转移到俄德梅桥去了。尽管走在最后的是一位师长,但在这些乱糟糟的残兵败将面前,他也照样束手无策。而且,眼睁睁地看着这样一个曾经善战的民族竞至于因为惨败而崩溃,他能不万念俱灰吗?好在还有两名副官陪着他,徒步后撤。
接下来,整个城市便在一种深沉宁静得令人恐怖的气氛里等候着。很多被商业弄昏了头脑的大肚子富翁都在忧心忡忡地等待战胜者的到来,而且当他们一想起自己厨房里烤肉的铁叉和斩肉的大刀有可能被人当做武器看待时,都不由自主地浑身发起抖来。
生活像是停顿了,店铺全部关了门,街道上也是阒无声息。偶尔有那么一两个因为这沉寂而胆怯的居民出门,也都沿着墙跟,迅速地溜过。
由于等待而烦闷的人们,这个时候反倒有些盼望着敌人快些到来。
在法军完全撤退后的第二天下午,三五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普鲁士骑兵匆匆忙忙地穿过了市区。随后,便有一堆乌压压的人马从汕喀德邻的山坡上开了下来,同时另外两股敌军也出现在了达尔内答勒和祁倭姆丛林里的大路上。这三支部队的前哨恰好在市政府广场上会师。最后,日耳曼人的主力也从附近那些街道开了过来,一个营接着一个营,强硬而富有节奏的步伐踏在石板街上,橐橐作响。
一句句生硬而陌生的口令,沿着那些像是死了一般的空房子在空中弥漫。尽管房子的百叶窗早已全部关闭,可是里面却有无数双眼睛正在窥视着这些胜利者——根据“战争法则”,他们将主宰这座城市全部的生命和财产。居民们在他们晦暗的屋子里吓得要死,就像是遇到了肆虐的大洪水,遇到了天崩地陷的大地震——要知道,在这些天灾面前,任何的聪明和力量都是无济于事的。很显然,每当秩序遭到颠覆,每当安全不复存在,每当法律保护之下的所有事物只得任凭一种无意识的暴力摆布时,这种同样无能为力的感觉就会必然跟着显现出来。无论是造成房屋坍塌、毁家灭族的地震,还是能让农民连同牛羊的尸体与冲散的栋梁一块儿漂流的江河决口,也无论是获胜的军队对自卫者的虐杀,抑或是以刀神的名义实行抢劫并以炮声向神灵致谢的盗匪,同样都是令人恐怖的灾难,同样都在破坏着人们对于永恒公理的信仰,破坏着我们那种通过教育建立起来的对于上帝保佑和人类理性的信心。
终于,在每所房屋的门外,一支支人数不多的小分队开始叩门了。这是入侵以后的占领行为。战败者对战胜者应该承担的义务也从此开始了。
过了不久,开始时的恐怖一旦消失以后,一种新的宁静气氛又建立了起来。在许多人家,普鲁士军官们跟主人一起用餐。其中,偶尔也会有受到过良好教育的军官,出于礼貌,替法国叫屈,表示自己参加这次战争并非出于自愿。于是,有人出于对他的感激,再加上迟早可能需要他的保护,心想,既然可以应付得了他,多供养几个士兵又有何妨呢。况且,对于一个完全可以依靠的人,为什么要去得罪呢?这种做法固然是轻率的意味多过了豪放,不过轻率早已不是卢昂居民的缺点,正如现在跟从前那个因壮烈守城而增光的时代不同了是一个道理。最后,有人指出,法国是个历史悠久的礼仪文明之邦,即使不能在公开场合与外来入侵者表示亲近,在家里讲究礼貌原本也是许可的。所以,双方在门外装作彼此陌生,而在家里却能其乐融融,到了后来,日耳曼人在法国人的家里每晚待得更久了,甚至可以跟主人家同在一座壁炉前烤火了。
慢慢地,市区也恢复了它平时的状态。尽管法国人还不大出门,可普鲁士士兵却在街道上往来不息。此外,许多身着蓝色军服的轻骑兵军官前往咖啡馆时,虽然也很傲慢地在街面的石块上拖着长军刀,但是他们对普通居民的蔑视,并不比一年前在同样的咖啡馆里喝酒的法国步兵军官更为明显。
然而空气中总是弥漫着一点儿东西,一点儿飘忽不定又无从捉摸的东西,一种令人难以容忍的异样气息,就好像是一种极其稀薄的味道,那种外患入侵的味道。它充塞着私人住宅和公共场所,它使饮食变了滋味,它让人觉得身在旅途——前往野蛮而又危险的部落的旅途。
战胜者终于开始伸手索要钱财了。居民们都有钱,自始至终都在如数缴纳。不过,有些诺曼底商人,越是富裕,就越害怕牺牲,越害怕看见自己财产中的哪怕一小部分转到别人手里。
然而,在市区下游两三法里左右的河道里,在靠近十字洲的吉艾卜达勒或者别萨尔一带,时常有船户或者渔民从水底捞起日耳曼人的尸首——这些军服里泡得发胀的尸首都是在生前被人一刀戳死或者一脚踢死的,不是脑袋被石头砸坏了,就是被人从桥上一下推落到水里。河底的污泥隐没了这类暖昧不明的野蛮而合法的报复行为。隐姓埋名的英雄行为,就跟偷袭一样,虽然不能获得荣誉和掌声,却也不像光天化日之下的战斗那般可怕。
对入侵者的憎恶,通常可以让三五个胆大的人变得格外坚强,使他们为了一个信念而不顾性命。
最后,虽然这些入侵者对市区控制得越来越严酷,虽然他们在征服途中所犯下的骇人听闻的罪行也早已造成了轰动,可在眼下的市区里却还没有完成过一件。这种情况下,人们的胆子也都渐渐大了起来,当地商人们做生意的心眼儿又重新活泛了起来。其中,好几个商人都在哈佛尔订有利益重大的契约,而那个城市还在法军防守之下,然后,他们打算先从陆路前往吉艾卜,然后坐船转赴那个海港。
有人利用自己熟识的日耳曼军官们的势力,获得了一张由他们总司令签发的出境证。
所以,一辆驷驾长途马车被预定去执行这趟任务,有十名旅客到车行里预定了座位,并且决定在某个星期二还没有天亮的时候起程,免得招来看热闹的人。
几天过去了,地面都冻硬了。从星期一午后三点钟左右开始,成堆的黑云夹杂着雪花从北方飞了过来,直下到天黑,又下到深夜,仍然没有停止。
次日凌晨四点半光景,旅客们就已经聚到了诺曼底旅馆的天井里,那是他们上车的地方。
当时,他们都还睡意沉沉,在衣服里面颤抖着身子。黑暗里,谁也看不清楚谁,而且冬天的厚衣服把他们的身子裹得像是一些穿着长道袍的胖修士。不过,尽管如此,还是有两名旅客互相认出来了,而第三个也向他们身边走去,他们开始闲聊起来。一个说“我带了我的妻子”,另一个说“我也是一样”,那一个又接着说“我们打算不回卢昂了,而且,要是普鲁士人进攻哈佛尔,我们就准备去英国”也许是因为物以类聚的缘故,他们都有着相同的计划。
……
【前言】
前言莫泊桑(1850~1893年),法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出身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自1880年发表成名作《羊脂球》起,莫泊桑便一鸣惊人,成为法国文坛上最明亮的文学之星。莫泊桑的绝大部分作品也是从这时到1890年的十年间创作出来的。他在这十年短短的文学
【免费在线读】
羊脂球
一连好几天,许多溃军残部都在卢昂的市区里穿过。他们简直不能算是军队,只能说是散兵游勇。士兵们脸上的胡子全都又脏又长,身上的军服也都破烂不堪,既没有团队旗帜,也没有团队的番号。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向前走着,全都像是被压折了脊梁的落水狗一样无精打采,既不知道想什么,也不知道干什么,完全是习惯性地朝前走着,仿佛一停下来就会立刻倒地不起。
当然,我们所看到的,绝大多数是因战争动员而应召入伍的人,以及那些素以机警出名而奉命出战的国民卫队。前者都是生来就爱好和平的人,依靠固定收入生活的安分守己的人,他们大都扛着步枪躬着身子;而后者则是胆小怕死又易于冲动的人,他们一方面随时准备冲锋,一方面又随时准备开小差。而且在这两类人中间,还有几个红裤子步兵,他们都是在一场恶战中某个步兵师被歼后仅有的残余;另外还有许多垂头丧气的炮兵,也跟这些番号不同的步兵混杂在一起;偶尔也有几个头戴闪闪发光的铜盔的龙骑兵,拖着笨重的脚步跟在步兵们的步伐后面吃力地走着。
许多义勇军也以种种壮烈的名号成立了,他们的名号是:失败复仇队、墟墓公民队、死亡分享队,也都带着土匪的神气走过。
他们的首领,有些原本是做呢绒或粮食生意的商人,有些则是歇业的牛油贩子或者肥皂贩子。战争爆发以后,他们全都成了应运而生的战士,由于他们有银元或者长胡子,都做了军官。他们高谈阔论地讨论着作战计划,甚至吹嘘说:危亡关头的法国只能依靠他们的肩膀才能支撑下去。不过,有时候他们也很害怕他们的部下——那些常常因为过于凶悍而喜欢抢劫和胡闹的强徒。
普鲁士人快要攻进卢昂市区了,有人说。
两个月来,本市的国民卫队已经很谨慎地在附近各处山林里做过许多侦察工作,偶尔还放枪误伤了自己的哨兵,有时候即便遇着一只在荆棘丛中动弹的小兔子,他们也会预备作战。现在倒好,他们全都解散回家了。至于那些军械和服装,以及从前被他们拿到市郊三法里一带国道边上吓唬老百姓的凶器,现在却一下子都不见了。
法国最后的那些士兵终于渡过了塞纳河,从汕塞韦和布尔阿沙转移到俄德梅桥去了。尽管走在最后的是一位师长,但在这些乱糟糟的残兵败将面前,他也照样束手无策。而且,眼睁睁地看着这样一个曾经善战的民族竞至于因为惨败而崩溃,他能不万念俱灰吗?好在还有两名副官陪着他,徒步后撤。
接下来,整个城市便在一种深沉宁静得令人恐怖的气氛里等候着。很多被商业弄昏了头脑的大肚子富翁都在忧心忡忡地等待战胜者的到来,而且当他们一想起自己厨房里烤肉的铁叉和斩肉的大刀有可能被人当做武器看待时,都不由自主地浑身发起抖来。
生活像是停顿了,店铺全部关了门,街道上也是阒无声息。偶尔有那么一两个因为这沉寂而胆怯的居民出门,也都沿着墙跟,迅速地溜过。
由于等待而烦闷的人们,这个时候反倒有些盼望着敌人快些到来。
在法军完全撤退后的第二天下午,三五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普鲁士骑兵匆匆忙忙地穿过了市区。随后,便有一堆乌压压的人马从汕喀德邻的山坡上开了下来,同时另外两股敌军也出现在了达尔内答勒和祁倭姆丛林里的大路上。这三支部队的前哨恰好在市政府广场上会师。最后,日耳曼人的主力也从附近那些街道开了过来,一个营接着一个营,强硬而富有节奏的步伐踏在石板街上,橐橐作响。
一句句生硬而陌生的口令,沿着那些像是死了一般的空房子在空中弥漫。尽管房子的百叶窗早已全部关闭,可是里面却有无数双眼睛正在窥视着这些胜利者——根据“战争法则”,他们将主宰这座城市全部的生命和财产。居民们在他们晦暗的屋子里吓得要死,就像是遇到了肆虐的大洪水,遇到了天崩地陷的大地震——要知道,在这些天灾面前,任何的聪明和力量都是无济于事的。很显然,每当秩序遭到颠覆,每当安全不复存在,每当法律保护之下的所有事物只得任凭一种无意识的暴力摆布时,这种同样无能为力的感觉就会必然跟着显现出来。无论是造成房屋坍塌、毁家灭族的地震,还是能让农民连同牛羊的尸体与冲散的栋梁一块儿漂流的江河决口,也无论是获胜的军队对自卫者的虐杀,抑或是以刀神的名义实行抢劫并以炮声向神灵致谢的盗匪,同样都是令人恐怖的灾难,同样都在破坏着人们对于永恒公理的信仰,破坏着我们那种通过教育建立起来的对于上帝保佑和人类理性的信心。
终于,在每所房屋的门外,一支支人数不多的小分队开始叩门了。这是入侵以后的占领行为。战败者对战胜者应该承担的义务也从此开始了。
过了不久,开始时的恐怖一旦消失以后,一种新的宁静气氛又建立了起来。在许多人家,普鲁士军官们跟主人一起用餐。其中,偶尔也会有受到过良好教育的军官,出于礼貌,替法国叫屈,表示自己参加这次战争并非出于自愿。于是,有人出于对他的感激,再加上迟早可能需要他的保护,心想,既然可以应付得了他,多供养几个士兵又有何妨呢。况且,对于一个完全可以依靠的人,为什么要去得罪呢?这种做法固然是轻率的意味多过了豪放,不过轻率早已不是卢昂居民的缺点,正如现在跟从前那个因壮烈守城而增光的时代不同了是一个道理。最后,有人指出,法国是个历史悠久的礼仪文明之邦,即使不能在公开场合与外来入侵者表示亲近,在家里讲究礼貌原本也是许可的。所以,双方在门外装作彼此陌生,而在家里却能其乐融融,到了后来,日耳曼人在法国人的家里每晚待得更久了,甚至可以跟主人家同在一座壁炉前烤火了。
慢慢地,市区也恢复了它平时的状态。尽管法国人还不大出门,可普鲁士士兵却在街道上往来不息。此外,许多身着蓝色军服的轻骑兵军官前往咖啡馆时,虽然也很傲慢地在街面的石块上拖着长军刀,但是他们对普通居民的蔑视,并不比一年前在同样的咖啡馆里喝酒的法国步兵军官更为明显。
然而空气中总是弥漫着一点儿东西,一点儿飘忽不定又无从捉摸的东西,一种令人难以容忍的异样气息,就好像是一种极其稀薄的味道,那种外患入侵的味道。它充塞着私人住宅和公共场所,它使饮食变了滋味,它让人觉得身在旅途——前往野蛮而又危险的部落的旅途。
战胜者终于开始伸手索要钱财了。居民们都有钱,自始至终都在如数缴纳。不过,有些诺曼底商人,越是富裕,就越害怕牺牲,越害怕看见自己财产中的哪怕一小部分转到别人手里。
然而,在市区下游两三法里左右的河道里,在靠近十字洲的吉艾卜达勒或者别萨尔一带,时常有船户或者渔民从水底捞起日耳曼人的尸首——这些军服里泡得发胀的尸首都是在生前被人一刀戳死或者一脚踢死的,不是脑袋被石头砸坏了,就是被人从桥上一下推落到水里。河底的污泥隐没了这类暖昧不明的野蛮而合法的报复行为。隐姓埋名的英雄行为,就跟偷袭一样,虽然不能获得荣誉和掌声,却也不像光天化日之下的战斗那般可怕。
对入侵者的憎恶,通常可以让三五个胆大的人变得格外坚强,使他们为了一个信念而不顾性命。
最后,虽然这些入侵者对市区控制得越来越严酷,虽然他们在征服途中所犯下的骇人听闻的罪行也早已造成了轰动,可在眼下的市区里却还没有完成过一件。这种情况下,人们的胆子也都渐渐大了起来,当地商人们做生意的心眼儿又重新活泛了起来。其中,好几个商人都在哈佛尔订有利益重大的契约,而那个城市还在法军防守之下,然后,他们打算先从陆路前往吉艾卜,然后坐船转赴那个海港。
有人利用自己熟识的日耳曼军官们的势力,获得了一张由他们总司令签发的出境证。
所以,一辆驷驾长途马车被预定去执行这趟任务,有十名旅客到车行里预定了座位,并且决定在某个星期二还没有天亮的时候起程,免得招来看热闹的人。
几天过去了,地面都冻硬了。从星期一午后三点钟左右开始,成堆的黑云夹杂着雪花从北方飞了过来,直下到天黑,又下到深夜,仍然没有停止。
次日凌晨四点半光景,旅客们就已经聚到了诺曼底旅馆的天井里,那是他们上车的地方。
当时,他们都还睡意沉沉,在衣服里面颤抖着身子。黑暗里,谁也看不清楚谁,而且冬天的厚衣服把他们的身子裹得像是一些穿着长道袍的胖修士。不过,尽管如此,还是有两名旅客互相认出来了,而第三个也向他们身边走去,他们开始闲聊起来。一个说“我带了我的妻子”,另一个说“我也是一样”,那一个又接着说“我们打算不回卢昂了,而且,要是普鲁士人进攻哈佛尔,我们就准备去英国”也许是因为物以类聚的缘故,他们都有着相同的计划。
……
【前言】
前言莫泊桑(1850~1893年),法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出身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自1880年发表成名作《羊脂球》起,莫泊桑便一鸣惊人,成为法国文坛上最明亮的文学之星。莫泊桑的绝大部分作品也是从这时到1890年的十年间创作出来的。他在这十年短短的文学
目录
莫泊桑短篇小说精选
- 名称
- 类型
- 大小
光盘服务联系方式: 020-38250260 客服QQ:4006604884
云图客服:
用户发送的提问,这种方式就需要有位在线客服来回答用户的问题,这种 就属于对话式的,问题是这种提问是否需要用户登录才能提问
Video Player
×
Audio Player
×
pdf Play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