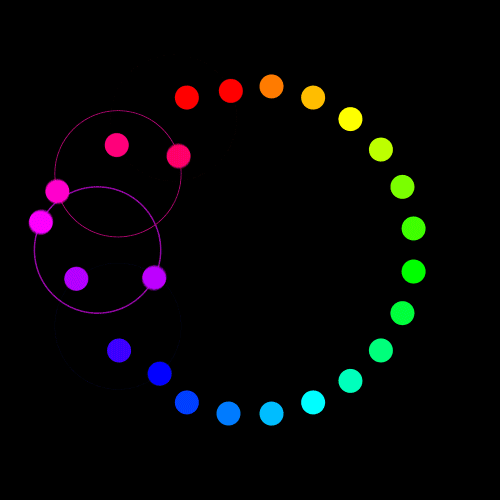简介
王元化先生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研究《文心雕龙》,1979年出版《文心雕龙创作论》,此作初版即为当时大家所推重,郭绍虞、季羡林、徐复观、王力、钱仲联、王瑶等均予以充分肯定。与钱锺书《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等同获首届比较文学荣誉奖。后来多次修订出版,*后定名为,《文心雕龙讲疏》。
本书辨定刘勰出身为庶族,刘勰思想基本以儒家思想为骨干,指出了刘勰思想的前后变化,讲了刘勰文学起源论与文学创作论,且对《文心雕龙》创作论八说作了释义本书是研究《文心雕龙》的经典,对我们创作也很有启发,很值得一读。
【目录】
新版前言
序
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
《灭惑论》与刘勰的前后期思想变化
刘勰的文学起源论与文学创作论
《文心雕龙》创作论八说释义小引
释《物色篇》心物交融说——关于创作活动中的主客关系
附释:一、心物交融说“物”字解
二、王国维的境界说与龚自珍的出入说
三、审美主客关系札记
释《神思篇》杼轴献功说——关于艺术想象
附释:一、“志气”和“辞令”在想象中的作用
二、玄学言意之辨撮要
三、刘勰的虚静说
释《体性篇》才性说——关于风格:作家的创作个性
附释:一、刘勰风格论补述
二、风格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
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关于意象:表象与概念的综合
附释:一、“离方遁圆”补释
二、刘勰的譬喻说与歌德的意蕴说
三、关于“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一点说明
四、再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
释《情采篇》情志说——关于情志:思想与感情的互相渗透
附释:一、《辨骚篇》应归入《文心雕龙》总论
二、文学创作中的思想和感情
释《镕裁篇》三准说——关于创作过程的三个步骤
附释:一、思意言关系兼释《文心雕龙》体例
二、文学创作过程问题
释《附会篇》杂而不越说——关于艺术结构的整体和部分
附释:一、文学创作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二、整体与部分和部分与部分
释《养气篇》率志委和说——关于创作的直接性
附释:一、陆机的应感说
二、创作行为的自觉性与不自觉性
《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序
1983年在日本九州大学的演讲
1984年在上海中日学者《文心雕龙》讨论会上的讲话
1987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演讲
1988年广州《文心雕龙》国际研讨会闭幕词
《敦煌遗书文心雕龙残卷集校》序
《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
《文心雕龙创作论》第二版跋
《文心雕龙讲疏》日译本序
备考
一、郭绍虞
二、曾祖荫
三、钱仲联
四、徐复观
五、季羡林
六、程千帆
七、兴膳宏
八、朱寨
九、牟世金
十、胡厚宣
十一、罗宗强
十二、钱伯城
【免费在线读】
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
刘勰的生平事迹史书很少记载,现在留下的《梁书》和《南史》的《刘勰传》几乎是仅存的文献资料。这两篇传记过于疏略,甚至未详其生卒年月。清刘毓崧《通谊堂集?书文心雕龙后》,根据《时序篇》“暨皇齐驭宝,运集休明,太祖以圣武膺箓,高祖以睿文纂业,文帝以贰离含章,中宗以上哲兴运,并文明自天,缉遐(熙)景祚。今圣历方兴,文思光被”一段文字,考定《文心雕龙》成书不在梁时而在齐末。所据理由有三:一、《时序篇》所述,自唐虞至刘宋,皆但举其代名,而特于齐上加一皇字。二、魏晋之主,称谥号而不称庙号;至齐之四主,唯文帝以身后追尊,止称为帝,余并称祖称宗。三、历朝君臣之文,有褒有贬,独于齐则竭力赞美,绝无规过之词。《书后》又说:“东昏上高宗庙号,系永泰元年八月事,据高宗兴运之语,则成书必在是月之后。梁武帝受和帝之禅位,系中兴二年四月事,据皇齐驭宝之语,则成书必在是月之前。其间首尾相距,将及四载。”这一考证经过近人的研究,已渐成定谳。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根据此说进一步考定刘勰于齐明帝建武三、四年间撰《文心雕龙》,时三十三四岁,正与《序志篇》“齿在逾立”之文相契。从而推出刘勰一生跨宋、齐、梁三代,约当宋泰始初年(465年)生,至梁普通元、二年间(520或521年)卒,得年五十六七岁。至此,刘勰的生平才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轮廓(关于刘勰的卒年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就在这个基础上,参照《宋书》、《南齐书》、《梁书》、《南史》并《梁僧传》中有关资料,加以对勘,写成《梁书刘勰传笺注》。这篇笺注虽不越《梁书》本传范围,但对刘勰的家世及其在梁代齐以后入仕的经历,都有相当丰富的增补。上述研究成果提供了不少线索,但仍留了一些问题尚待解决。这里首先想要提出刘勰的身世问题。
《梁书》本传说到刘勰的家世只有寥寥几句话:“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骑校尉。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灵真、刘尚二人,史书无传,事迹已不可考。但是我们从这里知道灵真为宋司空秀之之弟,而秀之又是辅佐刘裕的谋臣刘穆之的从兄子。根据这条线索,就可以从刘穆之、刘秀之两传来推考刘勰的家世了。杨明照《本传笺注》曾参考有关资料,制出刘勰的世系表①。《本传笺注》分析刘勰的世系表说:“南朝之际,莒人多才,而刘氏尤众,其本支与舍人同者,都二十余人,虽臧氏之盛,亦莫之与京。是舍人家世渊源有自,其于学术,必有启厉者。”这里所说的臧氏,亦为东莞莒人,是一个侨姓大族,其中如臧焘、臧质、臧荣绪、臧严、臧盾、臧厥等,史书并为之立传。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称:“自江左以来,其文学之士,大抵出于世族。”②其中所举能文擅名的士族,舍琅邪王氏、陈郡谢氏、吴郡张氏、南兰陵萧氏、陈郡袁氏、东海王氏、彭城到氏、吴郡陆氏、彭城刘氏、会稽孔氏、庐江何氏、汝南周氏、新野庾氏、东海徐氏、济阳江氏外,就有东莞臧氏在内。《本传笺注》虽然没有明言刘勰出身士族,但以之比配东莞臧氏,似乎认为刘勰也是出身于一个士族家庭。这种看法在王利器《文心雕龙新书序录》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序录》作者直截了当地把刘勰归入士族。近来探讨刘勰出身的文章也多持此说。
刘勰究竟属于士族还是庶族,这是研究刘勰身世的关键问题。自然,在南朝社会结构中,无论士族或庶族,都属于社会上层(当时的下层民众是小农、佃客、奴隶、兵户、门生义故、手工业劳动者等)。但是由于南朝不仅承袭了魏文帝定立的九品中正门选制,而且逐渐形成了一种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因而使士族享有更大的特权。士、庶区别是南朝社会等级编制的一个特点。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南史?王球传》来说明:“徐爰有宠于上,上尝命球及殷景仁与之相知。球辞曰:‘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上改容谢焉。”这里清楚地说明了士、庶区别是国家的典章。当时士族多是占有大块土地和庄园的大地主,有的甚或领有部曲,拥兵自保。晋代魏改屯田制为占田制后,士族可以按照门阀高低,荫其亲属。这也就是说,通过租税和徭役对被荫庇的族人和佃客进行剥削。他们的进身已无须中正的品评,问题全在区分血统,辨别姓望。在这种情况下,官有世胄,谱有世官,于是贾氏、王氏的“谱学”成了专门名家的学问,用以确定士族的世系,以防冒滥。士族拥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实际上成了当时改朝换代的幕后操纵者。至于庶族则多属中小地主阶层,但是在豪族右姓大量进行搜刮、土地急剧集中的时代,他们占有的土地时有被兼并的危险。在进身方面,他们由于门第低卑,更是受到了压抑,绝不能像士族那样平流进取坐至公卿。《晋书》载刘毅陈九品有八损疏,**条就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意思说庶族总是沦于卑位。左思在《咏史诗》中也发出了“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感叹。到了宋、齐两朝,庶族进身的条件受到了更大的限制,《梁书?武帝纪》载齐时有“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的规定③。当时,虽然也有一些庶族被服儒雅,侥幸升迁高位,但都遭到歧视和打击。《晋书》记张华庶族儒雅,声誉日隆,有台辅之望,而荀勖自以大族,恃帝深恩,憎疾之,每伺闲隙,欲出华外镇。《宋书》记蔡兴宗居高位,握重权,而王义恭诋其“起自庶族”。兴宗亦言:“吾素门平进,与主上甚疏,未容有患。”《南齐书》称陈显达自以人微位重,每迁官,常有畏惧之色。尝谓其子曰:“麈尾扇是王谢家物,汝不须捉此自随。”这些事例充分说明士、庶区别甚至并不因位之贵贱而有所改变。所谓“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视寒素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以为之伍”(《文苑英华》引《寒素论》)。所以,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来说,庶族都时常处于升降浮沉、动荡不定的地位。
根据笔者对刘勰家世的考定,并参照他在著作中所表现的思想观点来加以印证,刘勰并不是出身于士族,而是出身于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理由有下面几点:
**,按照士族身份的规定,首先在于魏晋间的祖先名位,其中以积世文儒为贵,武吏出身的不得忝列其数。可是我们在刘勰的世系表中,不能找到一个在魏晋间位列清显的祖先。秀之、灵真的祖父爽,事迹不详,推测可能是刘氏在东晋时的*早人物。《南史》只是说他做过山阴令,而晋时各县令系由卑品充任。至于世系表称东莞刘氏出自汉齐悼惠王肥后,则颇可疑。此说原本之《宋书?刘穆之传》,似乎应有一定根据。但是,南朝时伪造谱牒的现象极为普遍,许多新贵在专重姓望门阀的社会中,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编造一个做过帝王将相的远祖是常见的事。因此,到了后出的《南史》,就把《宋书?刘穆之传》中“汉齐悼惠王肥后”一句话删掉了。这一删节并非随意省略,而是认为《宋书?刘穆之传》的说法是不可信的。这一点,我们可以据《南史》改削《齐书》本纪一事推知。《齐书》本纪曾记齐高帝萧道成世系,自萧何至高帝之父,凡二十三世,皆有官位名讳。《南史?齐本纪》直指其诬说:“据齐、梁纪录,并云出自萧何,又编御史大夫望之,以为先祖之次。案何及望之,于汉俱为勋德,而望之本传,不有此言,齐典所书,便乖实录。近秘书监颜师古,博考经籍,注解《汉书》,已正其非,今随而改削云。”可见《南史》改削前史是以其有乖实录为依据的。据此,我们知道东莞刘氏不仅没有一个在魏晋间致位通显的祖先,而且连出于汉齐悼惠王肥后的说法也是不可靠的。这是刘勰并非出身土族的**个证据。
第二,在刘氏世系中,史书为之立传的有穆之、穆之从兄子秀之、穆子曾孙祥和刘勰四人(其余诸人则附于各传内)。其中穆之、秀之二人要算刘氏世系中*显赫的人物。据《宋书》记载,穆之是刘宋的开国元臣,出身军吏,因军功擢升为前军将军,义熙十三年卒,重赠侍中司徒,宋代晋后,进南康郑公,食邑三千户。秀之父仲道为穆之从兄,曾和穆之一起隶于宋高祖刘裕部下,克京城后补建武参军,事定为余姚令。秀之少孤贫,何承天雅相器重,以女妻之;元嘉十六年,迁建康令,除尚书中兵郎。他在益州刺史任上,以身率下,远近安悦。卒后,追赠侍中司空,并赠封邑千户。穆之、秀之都被追赠,位列三公,食邑千户以上,自然应该归入官僚大地主阶级。可是,从他们的出身方面来看,我们并不能发现属于士族的任何痕迹。穆之是刘氏世系中*早显露头角的重要人物,然而史籍中却有着充分证据说明他是以寒人身份起家的。《宋书》记刘裕进为宋公后追赠穆之表说:“故尚书左仆射前军将臣穆之,爰自布衣,协佐义始,内端谋猷,外勤庶政,密勿军国,心力俱尽。”(此表为傅亮代刘裕所作,亦载于《文选》,题为:《为宋公求加赠刘前军表》)这里明白指出穆之出身于布衣庶族。《南史》也曾经说到穆之的少时情况,可与此互相参照:“穆之少时家贫,诞节,嗜酒食,不修拘检,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见辱,不以为耻。其妻江嗣女,甚明识,每禁不令往。江氏后有庆会,属令勿来,穆之犹往,食毕求槟榔,江氏兄弟戏之曰:‘槟榔消食,君乃常饥,何忽须此?’妻复截发市肴馔,为其兄弟以饷穆之。”(此事亦见于宋孔平仲之《续世说》)这段记载正和上表“爰自布衣”的说法相契。在当时朝代递嬗、政局变化的情势下,往往有一些寒人以军功而被拔擢高位,参与了**统治集团。但是,他们并不因此就得列入士族。这里可举一个突出的事例。《南史》称:“中书舍人纪僧真幸于武帝,稍历军校,容表有士风,谓帝曰:‘臣小人,出自本县武吏,邀逢圣时,阶荣至此,为儿婚得荀昭光女,即时无复所须,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敩谢,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敩,登榻坐定,敩便命左右曰:‘移吾床让客。’僧真丧气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这个例子清楚说明身居高位的庶族乞作士大夫,连皇帝都爱莫能助。我们在《南史?刘祥传》里还可以找到有关穆之身世的一个旁证:“祥少好文学,性韵刚疏,轻言肆行,不避高下。齐建元中,为正员郎。司徒褚彦回入朝,以腰扇障日,祥从侧过曰:‘作如此举止,羞面见人,扇障何益?’彦回曰:‘寒士不逊。’”刘祥是穆之曾孙,时隔四世,仍被士族人物呼为“寒士”,更足以说明刘氏始终未能列入士族。“寒士”亦庶族之通称(《唐书?柳冲传》称“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即以寒士与世胄对举)。总之,细审刘穆之、刘秀之、刘祥三传的史实,刘氏出身布衣庶族,殆无疑义,这是刘勰并非属于士族的第二个证据。
第三,再从刘勰本人的生平事迹来看,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线索。首先,这就是《梁书》本传所记下面一段话:“初,勰撰《文心雕龙》……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据《范注》说,《文心雕龙》约成于齐和帝中兴初。案此时刘勰已居定林寺多年,曾襄佐僧祐校定经藏,且为定林寺僧超辩墓碑制文(据《梁僧传》载,超辩卒于齐永明十三年),不能说是一个完全默默无闻的人物。另一方面,当时沈约与定林寺关系也相当密切,这里只要举出定林寺僧法献于齐建和末卒后由他撰制碑文一事即可说明。法献为僧祐师④,齐永明中被敕为僧主,是一代名僧。刘勰与僧祐关系极为深厚,而僧祐地位又仅次于其师法献。沈约为法献碑制文在建武末,《文心雕龙》成书在中兴初,时间相距极近。在这种情况下,刘勰如果要使自己的作品取定于沈约,似乎并不十分困难。为什么《文心雕龙》书成之后,刘勰不利用自己在定林寺的有利地位以及和僧祐的密切关系去会见沈约,相反却无由自达,非得装成货鬻者干之于车前呢?这个疑问只能用“士庶天隔”的等级界限才能解答。南朝士族名士多以拒庶族寒人交际为美德。庶族人物即使上升为贵戚近臣,倘不自量,往见士族,仍不免会受到侮辱。这类故事史籍记载极丰,不烦赘举。沈约本人就是极重士、庶区别的人物,《文选》载他所写的《奏弹王源》一文可为证。东海王源为王朗七世孙,沈约以为王源及其父祖都位列清选,竟嫁女给富阳满鸾;虽然满鸾任吴郡主簿,鸾父璋之任王国侍郎,可是满氏“姓族士庶莫辨”,因此“王满连姻,实骇物听”,玷辱世族,“莫斯为甚”。刘勰要使自己的作品取定于这样一个人物,只有出于装成货鬻小贩之一途了。其次,《梁书》本传又说,沈约得书取读后,“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沈约重视的原因,前人多有推测,以为在于《声律篇》,因为它和沈约自诩独得胸襟的《四声谱》有相契之处。纪昀《沈氏四声考》曾谓:“勰以宗旨相同,故蒙赏识。”这是不无理由的。距此时不久,刘勰就于梁天监初起家奉朝请,进入仕途了⑤。不过,尽管《文心雕龙》见重于沈约,尽管刘勰入仕后又被昭明太子所爱接,但二人的史传和留下的文集,竟没有一件事涉及刘勰,也没有出现一句对他称道的话,可见他仍旧“未被时流所称”⑥,其原因很可能和他出身微贱有关。此外,刘勰少时入定林寺和不婚娶的原因,也只有用出身于贫寒庶族这件事才能较为圆满地说明。史称南朝赋役繁重,人民多所不堪,只有士族特邀宽典,蠲役免税。庶族自然不会得到优免。根据当时历史记载,一般平民为了避免沉重的课输徭役,往往只有进入寺庙,因为寺庙是享有特权的地方,入寺庙后可以不贯民籍,免于向政府纳税服役。《魏书?释老志》已有“愚民侥幸,假称入道,以避输课”之语。《南史?齐东昏侯纪》称:“诸郡役人,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出家疾病者亦免。”《弘明集》载桓玄《与僚属沙汰僧众教》称:“避役钟于百里,逋逃盈于寺庙,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邑聚游食之群,境积不羁之众。”又僧顺《释三破论》引《三破论》曰:“出家者未见君子,皆是避役。”明明说出当时因避租役而入寺庙是普遍现象。当然,不可否认,刘勰入定林寺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如佛教信仰以及便于读书等(当时的寺庙往往藏书极丰)。不过,我们不能把信仰佛教这一点过于夸大,因为他始终以“白衣”身份寄居定林寺,不仅没有出家,而且一旦得到进身机会,就马上离开寺庙登仕去了,足证他在定林寺时期对佛教的信仰并不十分虔诚。再就刘氏家世来看,亦非世代奉佛,与佛教关系并不密切⑦。他自称感梦撰《文心雕龙》,梦见的是孔子,而不是释迦。《文心雕龙》书中所表现的基本观点是儒家思想,而不是佛学或玄学思想。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他入定林寺依沙门僧祐居处的动机并不全由佛教信仰,其中因避租课徭役很可能占主要成分⑧。至于他不婚娶的原因,也多半由于他是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的缘故。《晋书?范宁传》、《宋书?周朗传》都有当时平民“鳏居每不愿娶,生儿每不敢举”的记载。总之,从刘勰本人的一些事迹来看,只能用出身庶族、家境贫寒的原因才可以说明,否则便很难解释。这是刘勰并非属于士族的第三个证据。
有了上面三个证据,现在回过头来,参照一下《文心雕龙》所表现的思想观点来加以印证,我们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
《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刘勰并没有在这部论著中对当时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直接表示看法。自然,我们从《文心雕龙》的思想体系和基本观点也可以推出刘勰的政治倾向。不过,这里需要找到一些可以用来论证刘勰家世的更直接的材料。就这方面来说,我以为《程器篇》是一篇*值得重视的文字。刘勰在这篇文章中论述了文人的德行和器用,藉以阐明学文本以达政之旨。其中寄慨遥深,不仅颇多激昂愤懑之词,而且也比较直接正面地吐露了自己的人生观和道德理想。纪昀评《程器篇》说:“观此一篇,彦和亦发愤而著书者。观《时序篇》,此书盖成于齐末,彦和入梁乃仕,故郁郁乃尔耶。”纪昀这个说法虽然也看出一些问题,可是没有进一步去发掘其中意蕴,究明刘勰的愤懑针对哪些社会现象,只是笼统地斥之为“有激之谈,不为典要”就一笔带过了。直到*近,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始对《程器篇》作出较充分的分析。兹摘要录下:“细绎其文,可得二义:一者,叹息于无所凭借者之易召讥谤;二者,讥讽位高任重者,怠其职责,而以文采邀誉。于前义可见尔时之人,其文名籍甚者,多出于华宗贵胄,布衣之士,不易见重于世。盖自魏文时创为九品中正之法,日久弊生……宋齐以来,循之未改……至隋文开皇中,始议罢之。是六代甄拔人才,终不出此制。于是士流咸重门第,而寒族无进身之阶,此舍人所以兴叹也。于后义可见尔时显贵,但以辞赋为勋绩,致国事废弛。盖道文既离,浮华无实,乃舍人之所深忧,亦《文心》之所由作也。”这里显然把刘勰的愤激归结到士庶区别问题上面。现在我们就从《程器篇》援引下面几段文字来加以说明。
一、“古之将相,疵咎实多。至如管仲之盗窃,吴起之贪淫,陈平之污点,绛灌之谗嫉,沿兹以下,不可胜数。孔光负衡据鼎,而仄媚董贤,况班马之贱职,潘岳之下位哉!王戎开国上秩,而鬻官嚣俗,况马杜之磐悬,丁路之贫薄哉!”——这里列举的前人仅西晋王戎时间*近,且出身势豪。(《晋书?王戎传》说他:“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其余管仲以下诸人,已经年代绵邈,似乎与士、庶区别问题无关。但是“纪评”指为非为典要的有激之谈正是针对这一段文字而发。细审其旨,我们可以看出刘勰在这里含有借古喻今的深意,表面似在指摘古代将相,实际却是箴砭当时显贵。《奏启篇》以“不畏强御,气流墨中,无纵诡随,声动简外”为楷式,《谐篇》用“心险如山,口壅若川,怨怒之情不一,欢谑之言无方”来解释民间嘲产生的原因,也都是从这种精神出发的。这一点,只要再看一看下面一段引文就更可以明白。
二、“盖人禀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扬,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这一段话*早为鲁迅所重视,他曾经在早期著作《摩罗诗力说》中加以援引,并指出:“东方恶习尽此数言。”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刘勰对于当时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产生的种种恶习所感到的愤懑和不平。正如《校释》所说,他一方面慨叹于布衣寒族无所凭借而易招讥谤,另一方面不满于贵胄士流位高任重而常邀虚誉。《史传篇》:“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常嗤;理欲吹霜煦露,寒暑笔端,此又同时之枉,可为叹息者也!”刘勰推崇“良史直笔”,而指摘某些史臣文士专以门阀高低作为褒贬的标准,亦同申此旨。
三、“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鲁之敬姜,妇人之聪明耳,然推其机综,以方治国,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这里以妇人聪明来说明学文以达政之旨,寓有箴砭时弊之意。当时士族多不问政事,流风所扇,虽所谓英君哲相亦不能免,甚至武人亦沿其流。朝士旷职,多见宽容。《南齐书?褚渊传》称:“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则知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梁书?何敬容传》载姚察之论曰:“宋世王敬弘,身居端右,未尝省牒。风流相尚,其流遂远。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恪勤匪懈,终滞鄙俗。是使朝经废于上,职事隳于下。”《陈书?后主纪论》曰:“自魏正始、晋中朝以来,贵臣虽有识治者,皆以文学相处,罕关庶务,朝章大典,方参议焉。文案簿领,咸委小吏,浸以成俗。迄至于陈,后主因循,未遑改革。”这类情况,史不绝书,几乎随处可见。士流不问政事是由于尚于玄虚,贵为放诞。事实上,玄谈在当时已成了登仕之阶。《世说新语》曾记张凭因清谈得到刘真长赏识而被举为太常博士。任彦昇在《为萧扬州作荐士表》中更直截了当地提出“势门上品犹当格以清谈”。这些都说明了属言玄远方能入仕。刘勰在《明诗篇》中也批评了江左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的不良倾向。《议对篇》则以贵媵还珠之喻斥责了“不达政体”的浮华文风。这种批评和《程器篇》“学文达政”的主张是声气相通、原则同贯的。
四、“文武之术,左右惟宜,郤縠敦书,故举为元帅,岂以好文而不练武哉!孙武兵经,辞如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刘勰为什么以文人习武作为衡量梓材之士的标准呢?此说人多以为异。但是,我们如果参照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也就不难发现刘勰倡立此说的由来。史称齐梁之际,“内难九兴,外寇三作”,刘勰撰《文心雕龙》正在此时。当时中原沦丧已久,北魏迁都洛阳,出兵南侵,萧齐皇朝不仅毫无御侮决心,反而不断演出了自相残杀的丑剧。南渡后,士族偏安江左,过着糜烂腐朽的生活,耽好声色,体羸气弱。这一点,可引《颜氏家训?勉学篇》的一段文字来说明:“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蹑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夫射御书数,古人并习,未有柔靡脆弱如齐梁子弟者。士习至此,国事尚可问哉?”刘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文事武备并重之论的。
五、“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其质,豫章其干,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此说出于儒家。孔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孟子:“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是其所本。这种人生观决定了刘勰的愤懑和不平,不会超越“在邦无怨,在家无怨”的儒家思想界线。纪昀说他由于郁郁不得志而发愤著书,这个论断,大体不差。《诸子篇》“身与时舛,志共道申”的感叹,也同样说明了“穷则独善以垂文”的道理。
根据上面的引文和说明来看,《程器篇》在许多场合都对士庶区别这一社会现象提出了批评,而这种批评是正符合于一个贫寒庶族的身份的。由此同样得出了刘勰并非属于士族的结论,正与上文考定刘勰家世所得证据完全一致。确定了刘勰属于庶族,就不难发现,他的一生经历都和他的出身有关。在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中,贫寒庶族往往处于动荡不定的地位:在经济上遭到排挤,在进身上受到歧视,甚至在日常生活方面也得时时忍辱含垢。这种受压抑、不稳定的地位使他们对当时社会中的某些黑暗现象感到不满。
刘勰的一生,经过了入寺—登仕—出家三个阶段。他在**个时期,由于出身低微,家境贫寒,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进入寺庙,采取了“穷则独善以垂文”的权变之计,发愤著书⑨。他在《文心雕龙》中,吐露了内心的不平和愤懑,反对了代表门阀标榜的浮华尚玄的文风,提出了文质并重的文学主张。从思想体系上来说,他恪守儒家的思想原则和伦理观念。《文心雕龙》基本观点是“宗经”。他处处都在强调仁孝,对儒家称美的先王和孔子推崇备至。从入寺以来,他就一直怀着儒家经世致用发挥事业的理想,当他一旦有了进身机会,认为自己可以实现自己的抱负时,就马上登仕去了。因而,他从**阶段到第二阶段,即由居寺而登仕,完全是合逻辑的发展。这正反映了所谓“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的人生观。他在第二个时期由于有了个人的前途,社会地位骤然提高,从而在思想上也就产生了相应的变化。他自梁天监初起家奉朝请后,就在言行上充分表现出亦步亦趋地趋承萧梁皇朝的意向。《梁书》本传称:“时七庙飨荐,已用蔬果,而二郊农社,犹有牺牲;勰乃表言二郊宜与七庙同改。诏付尚书议,依勰所陈。迁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据《本传笺注》分析:“步兵校尉因陈表而迁。”此说甚是。梁武帝即位不久即长斋素食,曾三次舍身入寺。刘勰陈表正好投合了这种需要⑩。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刘勰在这个时期所写的《灭惑论》找到更有力的证据。这篇论著标志着刘勰由儒家古文学派立场转变到向玄佛合流(此事将在下章中详论)。《灭惑论》中有一段话说:“张角、李弘,毒流汉季;卢悚、孙恩,乱盈晋末;余波所被,实蕃有徒。”刘勰反对奉太平道的张角和五斗米道的孙恩,似乎是佛道之争。卢悚亦奉天师道。李弘事迹不详,但为道教徒似无疑问。《老君音诵戒经》云:“称名李弘,岁岁有之。”晋时李弘有五,但在汉代史籍中,则尚未查出李弘名字。《灭惑论》所谓“余波所被,实蕃有徒”,正是指此而言。事实上,这种思想乃在于维护社会的统治力量。《诸子篇》:“昔东平求诸子、《史记》,而汉朝不与,盖以《史记》多兵谋,而诸子杂诡术也。”照刘勰看来,兵谋诡术都是造成社会动乱的祸源,因此他对于儒家经典以外的《史记》、“诸子”颇多微词。尽管刘勰在仕途中抛弃了以前的愤懑,竭力趋承萧梁皇朝的意向,幻想通过妥协道路去实现自己纬军国、任栋梁的理想;可是,看来他在仕途中并不得志。梁武帝学兼内外,奉佛教而不废儒书,曾经在这两方面发起过许多活动,史籍和《弘明集》都留下不少记载,其中却找不到刘勰参与的任何痕迹,可见他并未得到梁武帝的重视。到了晚年,他仍落入以前郁郁不得志的处境。梁武帝只命他和僧人一起撰经。他的地位又和入寺时相差无几了。终于他选择了出家遁世的途径,作为自己的归宿。据《梁书》本传称:“有敕与慧震沙门于定林寺撰经。证功毕,遂启求出家,先燔鬓发以自誓,敕许之。乃于寺变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刘勰用燔鬓发自誓的坚决态度来启求出家,可能由于在仕途上感到了幻灭,怀有说不出的苦衷。这就是他由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即由仕途而出家的原因。综上所述,刘勰的一生经历正表明了一个贫寒庶族的坎坷命运。他怀着纬军国、任栋梁的入世思想,却不得不以出家作为结局。他不满于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却不得不向**统治集团进行妥协。他恪守儒家古文学派立场反对浮华文风,却不得不与玄佛合流的统治思潮沆瀣一气。这些矛盾现象只有通过他的时代和身世才能得到*终的说明。
目录
新版前言
序
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
《灭惑论》与刘勰的前后期思想变化
刘勰的文学起源论与文学创作论
《文心雕龙》创作论八说释义小引
释《物色篇》心物交融说——关于创作活动中的主客关系
附释:一、心物交融说“物”字解
二、王国维的境界说与龚自珍的出入说
三、审美主客关系札记
释《神思篇》杼轴献功说——关于艺术想象
附释:一、“志气”和“辞令”在想象中的作用
二、玄学言意之辨撮要
三、刘勰的虚静说
释《体性篇》才性说——关于风格:作家的创作个性
附释:一、刘勰风格论补述
二、风格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
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关于意象:表象与概念的综合
附释:一、“离方遁圆”补释
二、刘勰的譬喻说与歌德的意蕴说
三、关于“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一点说明
四、再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
释《情采篇》情志说——关于情志:思想与感情的互相渗透
附释:一、《辨骚篇》应归入《文心雕龙》总论
二、文学创作中的思想和感情
释《镕裁篇》三准说——关于创作过程的三个步骤
附释:一、思意言关系兼释《文心雕龙》体例
二、文学创作过程问题
释《附会篇》杂而不越说——关于艺术结构的整体和部分
附释:一、文学创作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二、整体与部分和部分与部分
释《养气篇》率志委和说——关于创作的直接性
附释:一、陆机的应感说
二、创作行为的自觉性与不自觉性
《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序
1983年在日本九州大学的演讲
1984年在上海中日学者《文心雕龙》讨论会上的讲话
1987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演讲
1988年广州《文心雕龙》国际研讨会闭幕词
《敦煌遗书文心雕龙残卷集校》序
《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
《文心雕龙创作论》第二版跋
《文心雕龙讲疏》日译本序
备考
一、郭绍虞
二、曾祖荫
三、钱仲联
四、徐复观
五、季羡林
六、程千帆
七、兴膳宏
八、朱寨
九、牟世金
十、胡厚宣
十一、罗宗强
十二、钱伯城
【免费在线读】
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
刘勰的生平事迹史书很少记载,现在留下的《梁书》和《南史》的《刘勰传》几乎是仅存的文献资料。这两篇传记过于疏略,甚至未详其生卒年月。清刘毓崧《通谊堂集?书文心雕龙后》,根据《时序篇》“暨皇齐驭宝,运集休明,太祖以圣武膺箓,高祖以睿文纂业,文帝以贰离含章,中宗以上哲兴运,并文明自天,缉遐(熙)景祚。今圣历方兴,文思光被”一段文字,考定《文心雕龙》成书不在梁时而在齐末。所据理由有三:一、《时序篇》所述,自唐虞至刘宋,皆但举其代名,而特于齐上加一皇字。二、魏晋之主,称谥号而不称庙号;至齐之四主,唯文帝以身后追尊,止称为帝,余并称祖称宗。三、历朝君臣之文,有褒有贬,独于齐则竭力赞美,绝无规过之词。《书后》又说:“东昏上高宗庙号,系永泰元年八月事,据高宗兴运之语,则成书必在是月之后。梁武帝受和帝之禅位,系中兴二年四月事,据皇齐驭宝之语,则成书必在是月之前。其间首尾相距,将及四载。”这一考证经过近人的研究,已渐成定谳。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根据此说进一步考定刘勰于齐明帝建武三、四年间撰《文心雕龙》,时三十三四岁,正与《序志篇》“齿在逾立”之文相契。从而推出刘勰一生跨宋、齐、梁三代,约当宋泰始初年(465年)生,至梁普通元、二年间(520或521年)卒,得年五十六七岁。至此,刘勰的生平才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轮廓(关于刘勰的卒年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就在这个基础上,参照《宋书》、《南齐书》、《梁书》、《南史》并《梁僧传》中有关资料,加以对勘,写成《梁书刘勰传笺注》。这篇笺注虽不越《梁书》本传范围,但对刘勰的家世及其在梁代齐以后入仕的经历,都有相当丰富的增补。上述研究成果提供了不少线索,但仍留了一些问题尚待解决。这里首先想要提出刘勰的身世问题。
《梁书》本传说到刘勰的家世只有寥寥几句话:“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骑校尉。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灵真、刘尚二人,史书无传,事迹已不可考。但是我们从这里知道灵真为宋司空秀之之弟,而秀之又是辅佐刘裕的谋臣刘穆之的从兄子。根据这条线索,就可以从刘穆之、刘秀之两传来推考刘勰的家世了。杨明照《本传笺注》曾参考有关资料,制出刘勰的世系表①。《本传笺注》分析刘勰的世系表说:“南朝之际,莒人多才,而刘氏尤众,其本支与舍人同者,都二十余人,虽臧氏之盛,亦莫之与京。是舍人家世渊源有自,其于学术,必有启厉者。”这里所说的臧氏,亦为东莞莒人,是一个侨姓大族,其中如臧焘、臧质、臧荣绪、臧严、臧盾、臧厥等,史书并为之立传。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称:“自江左以来,其文学之士,大抵出于世族。”②其中所举能文擅名的士族,舍琅邪王氏、陈郡谢氏、吴郡张氏、南兰陵萧氏、陈郡袁氏、东海王氏、彭城到氏、吴郡陆氏、彭城刘氏、会稽孔氏、庐江何氏、汝南周氏、新野庾氏、东海徐氏、济阳江氏外,就有东莞臧氏在内。《本传笺注》虽然没有明言刘勰出身士族,但以之比配东莞臧氏,似乎认为刘勰也是出身于一个士族家庭。这种看法在王利器《文心雕龙新书序录》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序录》作者直截了当地把刘勰归入士族。近来探讨刘勰出身的文章也多持此说。
刘勰究竟属于士族还是庶族,这是研究刘勰身世的关键问题。自然,在南朝社会结构中,无论士族或庶族,都属于社会上层(当时的下层民众是小农、佃客、奴隶、兵户、门生义故、手工业劳动者等)。但是由于南朝不仅承袭了魏文帝定立的九品中正门选制,而且逐渐形成了一种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因而使士族享有更大的特权。士、庶区别是南朝社会等级编制的一个特点。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南史?王球传》来说明:“徐爰有宠于上,上尝命球及殷景仁与之相知。球辞曰:‘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上改容谢焉。”这里清楚地说明了士、庶区别是国家的典章。当时士族多是占有大块土地和庄园的大地主,有的甚或领有部曲,拥兵自保。晋代魏改屯田制为占田制后,士族可以按照门阀高低,荫其亲属。这也就是说,通过租税和徭役对被荫庇的族人和佃客进行剥削。他们的进身已无须中正的品评,问题全在区分血统,辨别姓望。在这种情况下,官有世胄,谱有世官,于是贾氏、王氏的“谱学”成了专门名家的学问,用以确定士族的世系,以防冒滥。士族拥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实际上成了当时改朝换代的幕后操纵者。至于庶族则多属中小地主阶层,但是在豪族右姓大量进行搜刮、土地急剧集中的时代,他们占有的土地时有被兼并的危险。在进身方面,他们由于门第低卑,更是受到了压抑,绝不能像士族那样平流进取坐至公卿。《晋书》载刘毅陈九品有八损疏,**条就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意思说庶族总是沦于卑位。左思在《咏史诗》中也发出了“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感叹。到了宋、齐两朝,庶族进身的条件受到了更大的限制,《梁书?武帝纪》载齐时有“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的规定③。当时,虽然也有一些庶族被服儒雅,侥幸升迁高位,但都遭到歧视和打击。《晋书》记张华庶族儒雅,声誉日隆,有台辅之望,而荀勖自以大族,恃帝深恩,憎疾之,每伺闲隙,欲出华外镇。《宋书》记蔡兴宗居高位,握重权,而王义恭诋其“起自庶族”。兴宗亦言:“吾素门平进,与主上甚疏,未容有患。”《南齐书》称陈显达自以人微位重,每迁官,常有畏惧之色。尝谓其子曰:“麈尾扇是王谢家物,汝不须捉此自随。”这些事例充分说明士、庶区别甚至并不因位之贵贱而有所改变。所谓“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视寒素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以为之伍”(《文苑英华》引《寒素论》)。所以,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来说,庶族都时常处于升降浮沉、动荡不定的地位。
根据笔者对刘勰家世的考定,并参照他在著作中所表现的思想观点来加以印证,刘勰并不是出身于士族,而是出身于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理由有下面几点:
**,按照士族身份的规定,首先在于魏晋间的祖先名位,其中以积世文儒为贵,武吏出身的不得忝列其数。可是我们在刘勰的世系表中,不能找到一个在魏晋间位列清显的祖先。秀之、灵真的祖父爽,事迹不详,推测可能是刘氏在东晋时的*早人物。《南史》只是说他做过山阴令,而晋时各县令系由卑品充任。至于世系表称东莞刘氏出自汉齐悼惠王肥后,则颇可疑。此说原本之《宋书?刘穆之传》,似乎应有一定根据。但是,南朝时伪造谱牒的现象极为普遍,许多新贵在专重姓望门阀的社会中,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编造一个做过帝王将相的远祖是常见的事。因此,到了后出的《南史》,就把《宋书?刘穆之传》中“汉齐悼惠王肥后”一句话删掉了。这一删节并非随意省略,而是认为《宋书?刘穆之传》的说法是不可信的。这一点,我们可以据《南史》改削《齐书》本纪一事推知。《齐书》本纪曾记齐高帝萧道成世系,自萧何至高帝之父,凡二十三世,皆有官位名讳。《南史?齐本纪》直指其诬说:“据齐、梁纪录,并云出自萧何,又编御史大夫望之,以为先祖之次。案何及望之,于汉俱为勋德,而望之本传,不有此言,齐典所书,便乖实录。近秘书监颜师古,博考经籍,注解《汉书》,已正其非,今随而改削云。”可见《南史》改削前史是以其有乖实录为依据的。据此,我们知道东莞刘氏不仅没有一个在魏晋间致位通显的祖先,而且连出于汉齐悼惠王肥后的说法也是不可靠的。这是刘勰并非出身土族的**个证据。
第二,在刘氏世系中,史书为之立传的有穆之、穆之从兄子秀之、穆子曾孙祥和刘勰四人(其余诸人则附于各传内)。其中穆之、秀之二人要算刘氏世系中*显赫的人物。据《宋书》记载,穆之是刘宋的开国元臣,出身军吏,因军功擢升为前军将军,义熙十三年卒,重赠侍中司徒,宋代晋后,进南康郑公,食邑三千户。秀之父仲道为穆之从兄,曾和穆之一起隶于宋高祖刘裕部下,克京城后补建武参军,事定为余姚令。秀之少孤贫,何承天雅相器重,以女妻之;元嘉十六年,迁建康令,除尚书中兵郎。他在益州刺史任上,以身率下,远近安悦。卒后,追赠侍中司空,并赠封邑千户。穆之、秀之都被追赠,位列三公,食邑千户以上,自然应该归入官僚大地主阶级。可是,从他们的出身方面来看,我们并不能发现属于士族的任何痕迹。穆之是刘氏世系中*早显露头角的重要人物,然而史籍中却有着充分证据说明他是以寒人身份起家的。《宋书》记刘裕进为宋公后追赠穆之表说:“故尚书左仆射前军将臣穆之,爰自布衣,协佐义始,内端谋猷,外勤庶政,密勿军国,心力俱尽。”(此表为傅亮代刘裕所作,亦载于《文选》,题为:《为宋公求加赠刘前军表》)这里明白指出穆之出身于布衣庶族。《南史》也曾经说到穆之的少时情况,可与此互相参照:“穆之少时家贫,诞节,嗜酒食,不修拘检,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见辱,不以为耻。其妻江嗣女,甚明识,每禁不令往。江氏后有庆会,属令勿来,穆之犹往,食毕求槟榔,江氏兄弟戏之曰:‘槟榔消食,君乃常饥,何忽须此?’妻复截发市肴馔,为其兄弟以饷穆之。”(此事亦见于宋孔平仲之《续世说》)这段记载正和上表“爰自布衣”的说法相契。在当时朝代递嬗、政局变化的情势下,往往有一些寒人以军功而被拔擢高位,参与了**统治集团。但是,他们并不因此就得列入士族。这里可举一个突出的事例。《南史》称:“中书舍人纪僧真幸于武帝,稍历军校,容表有士风,谓帝曰:‘臣小人,出自本县武吏,邀逢圣时,阶荣至此,为儿婚得荀昭光女,即时无复所须,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敩谢,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敩,登榻坐定,敩便命左右曰:‘移吾床让客。’僧真丧气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这个例子清楚说明身居高位的庶族乞作士大夫,连皇帝都爱莫能助。我们在《南史?刘祥传》里还可以找到有关穆之身世的一个旁证:“祥少好文学,性韵刚疏,轻言肆行,不避高下。齐建元中,为正员郎。司徒褚彦回入朝,以腰扇障日,祥从侧过曰:‘作如此举止,羞面见人,扇障何益?’彦回曰:‘寒士不逊。’”刘祥是穆之曾孙,时隔四世,仍被士族人物呼为“寒士”,更足以说明刘氏始终未能列入士族。“寒士”亦庶族之通称(《唐书?柳冲传》称“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即以寒士与世胄对举)。总之,细审刘穆之、刘秀之、刘祥三传的史实,刘氏出身布衣庶族,殆无疑义,这是刘勰并非属于士族的第二个证据。
第三,再从刘勰本人的生平事迹来看,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线索。首先,这就是《梁书》本传所记下面一段话:“初,勰撰《文心雕龙》……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据《范注》说,《文心雕龙》约成于齐和帝中兴初。案此时刘勰已居定林寺多年,曾襄佐僧祐校定经藏,且为定林寺僧超辩墓碑制文(据《梁僧传》载,超辩卒于齐永明十三年),不能说是一个完全默默无闻的人物。另一方面,当时沈约与定林寺关系也相当密切,这里只要举出定林寺僧法献于齐建和末卒后由他撰制碑文一事即可说明。法献为僧祐师④,齐永明中被敕为僧主,是一代名僧。刘勰与僧祐关系极为深厚,而僧祐地位又仅次于其师法献。沈约为法献碑制文在建武末,《文心雕龙》成书在中兴初,时间相距极近。在这种情况下,刘勰如果要使自己的作品取定于沈约,似乎并不十分困难。为什么《文心雕龙》书成之后,刘勰不利用自己在定林寺的有利地位以及和僧祐的密切关系去会见沈约,相反却无由自达,非得装成货鬻者干之于车前呢?这个疑问只能用“士庶天隔”的等级界限才能解答。南朝士族名士多以拒庶族寒人交际为美德。庶族人物即使上升为贵戚近臣,倘不自量,往见士族,仍不免会受到侮辱。这类故事史籍记载极丰,不烦赘举。沈约本人就是极重士、庶区别的人物,《文选》载他所写的《奏弹王源》一文可为证。东海王源为王朗七世孙,沈约以为王源及其父祖都位列清选,竟嫁女给富阳满鸾;虽然满鸾任吴郡主簿,鸾父璋之任王国侍郎,可是满氏“姓族士庶莫辨”,因此“王满连姻,实骇物听”,玷辱世族,“莫斯为甚”。刘勰要使自己的作品取定于这样一个人物,只有出于装成货鬻小贩之一途了。其次,《梁书》本传又说,沈约得书取读后,“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沈约重视的原因,前人多有推测,以为在于《声律篇》,因为它和沈约自诩独得胸襟的《四声谱》有相契之处。纪昀《沈氏四声考》曾谓:“勰以宗旨相同,故蒙赏识。”这是不无理由的。距此时不久,刘勰就于梁天监初起家奉朝请,进入仕途了⑤。不过,尽管《文心雕龙》见重于沈约,尽管刘勰入仕后又被昭明太子所爱接,但二人的史传和留下的文集,竟没有一件事涉及刘勰,也没有出现一句对他称道的话,可见他仍旧“未被时流所称”⑥,其原因很可能和他出身微贱有关。此外,刘勰少时入定林寺和不婚娶的原因,也只有用出身于贫寒庶族这件事才能较为圆满地说明。史称南朝赋役繁重,人民多所不堪,只有士族特邀宽典,蠲役免税。庶族自然不会得到优免。根据当时历史记载,一般平民为了避免沉重的课输徭役,往往只有进入寺庙,因为寺庙是享有特权的地方,入寺庙后可以不贯民籍,免于向政府纳税服役。《魏书?释老志》已有“愚民侥幸,假称入道,以避输课”之语。《南史?齐东昏侯纪》称:“诸郡役人,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出家疾病者亦免。”《弘明集》载桓玄《与僚属沙汰僧众教》称:“避役钟于百里,逋逃盈于寺庙,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邑聚游食之群,境积不羁之众。”又僧顺《释三破论》引《三破论》曰:“出家者未见君子,皆是避役。”明明说出当时因避租役而入寺庙是普遍现象。当然,不可否认,刘勰入定林寺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如佛教信仰以及便于读书等(当时的寺庙往往藏书极丰)。不过,我们不能把信仰佛教这一点过于夸大,因为他始终以“白衣”身份寄居定林寺,不仅没有出家,而且一旦得到进身机会,就马上离开寺庙登仕去了,足证他在定林寺时期对佛教的信仰并不十分虔诚。再就刘氏家世来看,亦非世代奉佛,与佛教关系并不密切⑦。他自称感梦撰《文心雕龙》,梦见的是孔子,而不是释迦。《文心雕龙》书中所表现的基本观点是儒家思想,而不是佛学或玄学思想。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他入定林寺依沙门僧祐居处的动机并不全由佛教信仰,其中因避租课徭役很可能占主要成分⑧。至于他不婚娶的原因,也多半由于他是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的缘故。《晋书?范宁传》、《宋书?周朗传》都有当时平民“鳏居每不愿娶,生儿每不敢举”的记载。总之,从刘勰本人的一些事迹来看,只能用出身庶族、家境贫寒的原因才可以说明,否则便很难解释。这是刘勰并非属于士族的第三个证据。
有了上面三个证据,现在回过头来,参照一下《文心雕龙》所表现的思想观点来加以印证,我们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
《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刘勰并没有在这部论著中对当时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直接表示看法。自然,我们从《文心雕龙》的思想体系和基本观点也可以推出刘勰的政治倾向。不过,这里需要找到一些可以用来论证刘勰家世的更直接的材料。就这方面来说,我以为《程器篇》是一篇*值得重视的文字。刘勰在这篇文章中论述了文人的德行和器用,藉以阐明学文本以达政之旨。其中寄慨遥深,不仅颇多激昂愤懑之词,而且也比较直接正面地吐露了自己的人生观和道德理想。纪昀评《程器篇》说:“观此一篇,彦和亦发愤而著书者。观《时序篇》,此书盖成于齐末,彦和入梁乃仕,故郁郁乃尔耶。”纪昀这个说法虽然也看出一些问题,可是没有进一步去发掘其中意蕴,究明刘勰的愤懑针对哪些社会现象,只是笼统地斥之为“有激之谈,不为典要”就一笔带过了。直到*近,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始对《程器篇》作出较充分的分析。兹摘要录下:“细绎其文,可得二义:一者,叹息于无所凭借者之易召讥谤;二者,讥讽位高任重者,怠其职责,而以文采邀誉。于前义可见尔时之人,其文名籍甚者,多出于华宗贵胄,布衣之士,不易见重于世。盖自魏文时创为九品中正之法,日久弊生……宋齐以来,循之未改……至隋文开皇中,始议罢之。是六代甄拔人才,终不出此制。于是士流咸重门第,而寒族无进身之阶,此舍人所以兴叹也。于后义可见尔时显贵,但以辞赋为勋绩,致国事废弛。盖道文既离,浮华无实,乃舍人之所深忧,亦《文心》之所由作也。”这里显然把刘勰的愤激归结到士庶区别问题上面。现在我们就从《程器篇》援引下面几段文字来加以说明。
一、“古之将相,疵咎实多。至如管仲之盗窃,吴起之贪淫,陈平之污点,绛灌之谗嫉,沿兹以下,不可胜数。孔光负衡据鼎,而仄媚董贤,况班马之贱职,潘岳之下位哉!王戎开国上秩,而鬻官嚣俗,况马杜之磐悬,丁路之贫薄哉!”——这里列举的前人仅西晋王戎时间*近,且出身势豪。(《晋书?王戎传》说他:“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其余管仲以下诸人,已经年代绵邈,似乎与士、庶区别问题无关。但是“纪评”指为非为典要的有激之谈正是针对这一段文字而发。细审其旨,我们可以看出刘勰在这里含有借古喻今的深意,表面似在指摘古代将相,实际却是箴砭当时显贵。《奏启篇》以“不畏强御,气流墨中,无纵诡随,声动简外”为楷式,《谐篇》用“心险如山,口壅若川,怨怒之情不一,欢谑之言无方”来解释民间嘲产生的原因,也都是从这种精神出发的。这一点,只要再看一看下面一段引文就更可以明白。
二、“盖人禀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扬,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这一段话*早为鲁迅所重视,他曾经在早期著作《摩罗诗力说》中加以援引,并指出:“东方恶习尽此数言。”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刘勰对于当时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产生的种种恶习所感到的愤懑和不平。正如《校释》所说,他一方面慨叹于布衣寒族无所凭借而易招讥谤,另一方面不满于贵胄士流位高任重而常邀虚誉。《史传篇》:“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常嗤;理欲吹霜煦露,寒暑笔端,此又同时之枉,可为叹息者也!”刘勰推崇“良史直笔”,而指摘某些史臣文士专以门阀高低作为褒贬的标准,亦同申此旨。
三、“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鲁之敬姜,妇人之聪明耳,然推其机综,以方治国,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这里以妇人聪明来说明学文以达政之旨,寓有箴砭时弊之意。当时士族多不问政事,流风所扇,虽所谓英君哲相亦不能免,甚至武人亦沿其流。朝士旷职,多见宽容。《南齐书?褚渊传》称:“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则知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梁书?何敬容传》载姚察之论曰:“宋世王敬弘,身居端右,未尝省牒。风流相尚,其流遂远。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恪勤匪懈,终滞鄙俗。是使朝经废于上,职事隳于下。”《陈书?后主纪论》曰:“自魏正始、晋中朝以来,贵臣虽有识治者,皆以文学相处,罕关庶务,朝章大典,方参议焉。文案簿领,咸委小吏,浸以成俗。迄至于陈,后主因循,未遑改革。”这类情况,史不绝书,几乎随处可见。士流不问政事是由于尚于玄虚,贵为放诞。事实上,玄谈在当时已成了登仕之阶。《世说新语》曾记张凭因清谈得到刘真长赏识而被举为太常博士。任彦昇在《为萧扬州作荐士表》中更直截了当地提出“势门上品犹当格以清谈”。这些都说明了属言玄远方能入仕。刘勰在《明诗篇》中也批评了江左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的不良倾向。《议对篇》则以贵媵还珠之喻斥责了“不达政体”的浮华文风。这种批评和《程器篇》“学文达政”的主张是声气相通、原则同贯的。
四、“文武之术,左右惟宜,郤縠敦书,故举为元帅,岂以好文而不练武哉!孙武兵经,辞如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刘勰为什么以文人习武作为衡量梓材之士的标准呢?此说人多以为异。但是,我们如果参照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也就不难发现刘勰倡立此说的由来。史称齐梁之际,“内难九兴,外寇三作”,刘勰撰《文心雕龙》正在此时。当时中原沦丧已久,北魏迁都洛阳,出兵南侵,萧齐皇朝不仅毫无御侮决心,反而不断演出了自相残杀的丑剧。南渡后,士族偏安江左,过着糜烂腐朽的生活,耽好声色,体羸气弱。这一点,可引《颜氏家训?勉学篇》的一段文字来说明:“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蹑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夫射御书数,古人并习,未有柔靡脆弱如齐梁子弟者。士习至此,国事尚可问哉?”刘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文事武备并重之论的。
五、“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其质,豫章其干,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此说出于儒家。孔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孟子:“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是其所本。这种人生观决定了刘勰的愤懑和不平,不会超越“在邦无怨,在家无怨”的儒家思想界线。纪昀说他由于郁郁不得志而发愤著书,这个论断,大体不差。《诸子篇》“身与时舛,志共道申”的感叹,也同样说明了“穷则独善以垂文”的道理。
根据上面的引文和说明来看,《程器篇》在许多场合都对士庶区别这一社会现象提出了批评,而这种批评是正符合于一个贫寒庶族的身份的。由此同样得出了刘勰并非属于士族的结论,正与上文考定刘勰家世所得证据完全一致。确定了刘勰属于庶族,就不难发现,他的一生经历都和他的出身有关。在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中,贫寒庶族往往处于动荡不定的地位:在经济上遭到排挤,在进身上受到歧视,甚至在日常生活方面也得时时忍辱含垢。这种受压抑、不稳定的地位使他们对当时社会中的某些黑暗现象感到不满。
刘勰的一生,经过了入寺—登仕—出家三个阶段。他在**个时期,由于出身低微,家境贫寒,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进入寺庙,采取了“穷则独善以垂文”的权变之计,发愤著书⑨。他在《文心雕龙》中,吐露了内心的不平和愤懑,反对了代表门阀标榜的浮华尚玄的文风,提出了文质并重的文学主张。从思想体系上来说,他恪守儒家的思想原则和伦理观念。《文心雕龙》基本观点是“宗经”。他处处都在强调仁孝,对儒家称美的先王和孔子推崇备至。从入寺以来,他就一直怀着儒家经世致用发挥事业的理想,当他一旦有了进身机会,认为自己可以实现自己的抱负时,就马上登仕去了。因而,他从**阶段到第二阶段,即由居寺而登仕,完全是合逻辑的发展。这正反映了所谓“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的人生观。他在第二个时期由于有了个人的前途,社会地位骤然提高,从而在思想上也就产生了相应的变化。他自梁天监初起家奉朝请后,就在言行上充分表现出亦步亦趋地趋承萧梁皇朝的意向。《梁书》本传称:“时七庙飨荐,已用蔬果,而二郊农社,犹有牺牲;勰乃表言二郊宜与七庙同改。诏付尚书议,依勰所陈。迁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据《本传笺注》分析:“步兵校尉因陈表而迁。”此说甚是。梁武帝即位不久即长斋素食,曾三次舍身入寺。刘勰陈表正好投合了这种需要⑩。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刘勰在这个时期所写的《灭惑论》找到更有力的证据。这篇论著标志着刘勰由儒家古文学派立场转变到向玄佛合流(此事将在下章中详论)。《灭惑论》中有一段话说:“张角、李弘,毒流汉季;卢悚、孙恩,乱盈晋末;余波所被,实蕃有徒。”刘勰反对奉太平道的张角和五斗米道的孙恩,似乎是佛道之争。卢悚亦奉天师道。李弘事迹不详,但为道教徒似无疑问。《老君音诵戒经》云:“称名李弘,岁岁有之。”晋时李弘有五,但在汉代史籍中,则尚未查出李弘名字。《灭惑论》所谓“余波所被,实蕃有徒”,正是指此而言。事实上,这种思想乃在于维护社会的统治力量。《诸子篇》:“昔东平求诸子、《史记》,而汉朝不与,盖以《史记》多兵谋,而诸子杂诡术也。”照刘勰看来,兵谋诡术都是造成社会动乱的祸源,因此他对于儒家经典以外的《史记》、“诸子”颇多微词。尽管刘勰在仕途中抛弃了以前的愤懑,竭力趋承萧梁皇朝的意向,幻想通过妥协道路去实现自己纬军国、任栋梁的理想;可是,看来他在仕途中并不得志。梁武帝学兼内外,奉佛教而不废儒书,曾经在这两方面发起过许多活动,史籍和《弘明集》都留下不少记载,其中却找不到刘勰参与的任何痕迹,可见他并未得到梁武帝的重视。到了晚年,他仍落入以前郁郁不得志的处境。梁武帝只命他和僧人一起撰经。他的地位又和入寺时相差无几了。终于他选择了出家遁世的途径,作为自己的归宿。据《梁书》本传称:“有敕与慧震沙门于定林寺撰经。证功毕,遂启求出家,先燔鬓发以自誓,敕许之。乃于寺变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刘勰用燔鬓发自誓的坚决态度来启求出家,可能由于在仕途上感到了幻灭,怀有说不出的苦衷。这就是他由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即由仕途而出家的原因。综上所述,刘勰的一生经历正表明了一个贫寒庶族的坎坷命运。他怀着纬军国、任栋梁的入世思想,却不得不以出家作为结局。他不满于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却不得不向**统治集团进行妥协。他恪守儒家古文学派立场反对浮华文风,却不得不与玄佛合流的统治思潮沆瀣一气。这些矛盾现象只有通过他的时代和身世才能得到*终的说明。
【作者简介】
王元化(1920—2008年),生于湖北武昌,祖籍湖北江陵,是著名的思想家、文艺理论家。解放前从事党的地下文艺工作,1955年在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中受牵连,1981年获得平反。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元化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学术史、中国古代文论、当代文艺理论、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上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与钱锺书并称“北钱南王”,著有《思辨录》(第三版《思辨随笔》1995年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文心雕龙讲疏》(初版《文心雕龙创作论》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评奖荣誉奖)、《清园近思录》等,有很大的学术影响。
文心雕龙讲疏
- 名称
- 类型
- 大小
光盘服务联系方式: 020-38250260 客服QQ:4006604884
云图客服:
用户发送的提问,这种方式就需要有位在线客服来回答用户的问题,这种 就属于对话式的,问题是这种提问是否需要用户登录才能提问
Video Player
×
Audio Player
×
pdf Play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