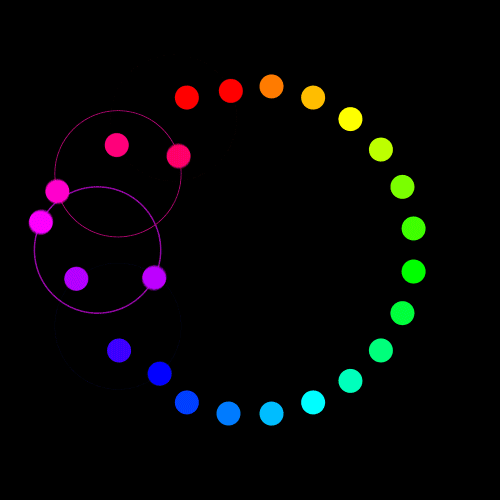简介
本书是继《旧人旧事旧小说》《旧文旧史旧版本》之后,又一部关于天津通俗文学的作品,主要搜罗了民国时期至解放初期天津的报刊与通俗文学领域中鲜为人知而又妙趣横生的小掌故、小内幕,读来颇有趣味。
目录
序——笔底江湖侠者风(王振良)
毛泽东为何要向毛岸英等推荐《峨眉剑侠传》
——兼论毛泽东的“通俗小说情结”
“重写文学史”背景下的通俗小说入史问题
——兼论现代通俗文学研究南北两团队的历史与现状
沦陷时期天津报业沉浮记
——兼谈1937—1945天津报载小说之状况
天津沦陷后,四个报人的联手抗战
——诞生在租界里的《高仲明纪事报》秘密出版纪实
面对日军劝降,两位报馆主人的凛然悲歌
——记以身殉报的《益世报》经理生宝堂与《新天津报》社长刘髯公
《天风报》因连载刘云若与还珠楼主长篇处女作而成“名报”
——“双牛堂”藏民国旧报旧刊典故录之一
以通俗小说连载著称的《新天津画报》
——“双牛堂”藏民国旧报旧刊典故录之二
《庸报》连载《十二金钱镖》让白羽“扬名立蔓”
——“双牛堂”藏民国旧报旧刊典故录之三
专以评书连载取悦读者的《三津报》
——“双牛堂”藏民国旧报旧刊典故录之四
著名导演沈浮曾让《国强报》副刊风生水起
——“双牛堂”藏民国旧报旧刊典故录之五
连载刘云若《歌舞江山》续作的《东亚晨报》
——“双牛堂”藏民国旧报旧刊典故录之六
以副刊取胜的《评报》和以小说连载促销的《平报》
——“双牛堂”藏民国旧报旧刊典故录之七
沦陷时期聚集众多通俗小说“大蔓”的《中南报》
——“双牛堂”藏民国旧报旧刊典故录之八
推出李山野社会小说《红豆相思记》的《天声报》
——“双牛堂”藏民国旧报旧刊典故录之九
记录沦陷时期平津戏曲状况的《游艺画刊》
——“双牛堂”藏民国旧报旧刊典故录之十
吴云心将《益世报》副刊“语林”办成北方“左联”阵地
——以“左翼”作家王余杞及其长篇小说《海河汩汩流》为例
“还珠楼主”笔名寓意及出现时间考辨
——兼谈还珠楼主的“灵肉异趋论”
“纸上江湖”背后的另面白羽
——民国社会武侠小说大师白羽生平新探
可作为武林教材的郑证因技击小说
——兼解郑证因与白羽首次“分手”内幕
刘云若用小说回目写新闻
——《北洋画报》首创“大小事演义”专栏
《北洋画报》上的“愚人”报道
——民国报刊追求“欧化”与“趣味性”例举
被“追认”主题的《雷雨》是怎样写成的
——浅论曹禺剧作中的“主题追认”与“主题先行”
新中国成立前后阿英在天津领导文艺工作始末
——《星报》:诞生在天津的新中国第一张文艺小报
后记(倪斯霆)
【免费在线读】
天津沦陷后,四个报人的联手抗战
——诞生在租界里的《高仲明纪事报》秘密出版纪实
1937年7月7日,随着日军蓄意挑衅,悲壮的枪炮声响彻在宛平城内。卢沟桥上,硝烟弥漫。积蓄经年的中国抗战终于爆发!
华北危机!平津告急!
三周后,因日方背信弃义,幻想中的沟通失败。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十九军军长的宋哲元,与部下第三十八师师长兼天津市市长的张自忠等人,于北平紧急磋商后,迅速向其所部发出“自卫守土”感电。
旋即,驻守天津的第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兼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被师长张自忠委任为天津军事总指挥。面对日军对天津的咄咄紧逼,7月28日,李文田率部于天津多方位对日军展开反击。经过一天浴血奋战,在重创机场与车站的日军后,李文田奉命于29日率部撤出天津。
翌日,除各国租界外,日军全面接管津城。
至此,天津沦陷。
租界内,四个文人在酝酿抵抗
天津法租界,位于老西开的法国天主教堂,其标志性的三个圆形塔楼直插云端,在四周低矮房屋的映衬下,显得巍峨耸立,气度不凡。
其对面便是沦陷前沽上市民夏季泛舟避暑、嬉戏游玩的墙子河。
河北岸靠东面与法国教堂斜对着的第一条街巷,当年是天津法租界贝拉扣路(沦陷后日军易名三十号路,今哈尔滨道)。这是一条并不宽敞且闹中取静的小马路,与西面比邻的福煦将军路(沦陷后日军易名二十六号路,今滨江道)的宽大、热闹、繁华相比,它显得逼仄、隐蔽、幽静,适合人居。1925年由河北省曲阳县同乡王、范、周三姓商人合资兴建,取天赐恩德寓意而命名的天德里,便坐落在这条街巷的南端东侧,与墙子河对岸的法国教堂可谓咫尺之遥。
1937年8月中旬的一天夜晚,在天德里14号(当年门牌)三层小楼二楼的一间小屋内,门窗紧闭,烟雾缭绕。四位已经无报可编刚刚下岗的年轻报人,正在紧张激烈地讨论着一件神秘而又庄重甚至可能掉脑袋的大事。
为首者便是暂租这间屋子的主人,战前天津《大公报》采访部主任并兼本埠新闻编辑的顾建平。其余三人中的两人为顾建平的曾经部下,原《大公报》记者林墨农、孔效儒,另一位则为战前天津《益世报》记者程寒华。
目前随着日军接管天津,他们此前所服务的《大公报》《益世报》已同津城其它大小报刊一样,均被勒令取缔出版,如想继续从事报纸行当,则只有到战前已被日军收买,眼下已沦为日寇“派遣军机关报”的《庸报》去报到。因为随着《庸报》的附逆,原报馆大批有气节的员工已纷纷离职,《庸报》馆正在焦急地笼络编采人员。
但这绝非是顾建平等人所愿。他们不但不会去为日本人编报,反而正在酝酿着如何利用自己的编报所长,去唤醒民众,一同抵抗日军的残暴统治。
此刻,只听操着浙东口音的顾建平(1908—1982)低声而又激奋地说:“日军封锁了津城与外界的联系,天津已成孤岛。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我们应该去和日本人斗一斗。”
孔效儒很抽了一口烟,郁闷地问:“怎么斗?我们都是拿笔的文人,虽然报国心切,但赤手空拳何以施展。”
正在扒着窗帘观察外面动静的林墨农回头急切地说:“老顾,你过去是我们的头儿,如今仍是。你说吧,怎么干?”
林墨农话音未落,程寒华便掐灭烟头,抢着说:“诸位老兄,现在我们是一个团体,国难当头,为了不作亡国奴,和日本人斗,匹夫有责。顾兄,你说怎么干,我们就跟着你干!”
听到三个人的表态,顾建平反倒平静下来,只听他缓缓地说:“我想起了一个故事。那是在一战的时候,德军占领了整个比利时,比国所有报刊都被查封。在布鲁塞尔,有一位比国记者在市外找了一所小屋,自己砌了夹壁墙,在那里安放了电台、简单铅字与小型印刷机。就这样,他与一两个学生秘密地自编自印自己发行了一份鼓吹抗战的小报,名字就叫《比利时自由报》。开始时是单线传递,后来读者渐多,便改为连锁送递。送递时他们就将报纸装在背心裤筒里,凡是得到报纸是人,就可以知道许多被德军封锁的战况及协约国胜利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沦陷区人们的斗志。德军始终在追查这张报纸,但都被这位记者巧妙的躲过了,这张报纸一直出版到德军战败,退出比利时为止……”
“你是说咱们也办一张秘密报纸,秘密发行,唤起市民抗日?”林墨农听明白了。
“可是到哪去找印厂印刷呢?如果日本人发现了肯定玩完。”孔效儒思索着说。
程寒华试着问大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一张油印报纸,这样我们便可以自己编辑自己印刷自己发行了。”
“对!寒华兄说的对。我们就稿一张油印小报,这样有钢笔、蜡纸,有一架油印机,有一台收音机便可以开工了。至于报名嘛……我看就叫《高仲明纪事报》。高仲明者,子虚乌有之人,就是日军发现,也是查无对证。纪事报,就是以记事的形式报道抗战消息,宣传抗日事迹。我们一定要编得文字活泼,通俗易懂。”顾建平受了程寒华的启发,脑子在急速运转。此刻,他两眼发光,望着大家兴奋地说。
这一晚,他们谈得热烈,说的尽兴,各个摩拳擦掌,情绪高昂。在细细地分析了怎样才能做到天时地利人和的诸种因素后,直至翌日黎明,四人方才散去……
恐怖下,一张油印小报在秘密传播
若想编印报纸,一个固定处所是必不可少的。
顾建平提议就将工作地点设在他租住的天德里二楼一间小屋内。理由是贝拉扣路地处法租界,位于华洋杂处的市中心,便于报纸的迅速传递,而且此地虽处都市繁华之首,但闹中取静,相对隐蔽;其次,此地尚属法国地界,洋人集中,人员成分复杂,日本人暂时奈何不得;此外,最最重要的是,此处住房四周邻居成分却相对简单。住在三楼的房东是电报局小职员,为人沉默寡言,他的两个儿子,分别在大学与中学读书。而一楼租户则是来自农村的一个土财主,平时除了关心他们县里是否进了日本兵或土匪外,对其它均无兴趣。
地点选定后,四人便进入了神秘而紧张的筹备中。
首先他们需要一台广播收音机和一架誊写油印机。油印机难不倒干报的人,他们用铁丝和网布制作了一个简易设备,再寻来一个废旧胶滚,简易誊写油印机便大功告成。但收音机却让他们为难,想买没钱,即使有钱,作为战时紧俏品,也是一时难觅。好在林墨农急中生智,他想到了一个即单身又有爱国心的朋友家,有一台名牌收音机。于是他与之联系,朋友深明大义,慨然允诺他可以每晚定点去家里收听抄录新闻。这让四人大喜,虽然增添了每晚跑道之苦,但毕竟苦胜于无,最关键的信息渠道问题终于解决了。
接下来,四个穷文人倾其所有凑了一元八毛钱的开办费。他们买了一元钱的白报纸,裁成16开作为印报用纸,再用两毛钱买了牛皮纸糊信封,其余的六毛钱买了一盒蓝色油墨。又从朋友处寻来几十张旧蜡纸、两支旧铁笔和一块旧钢板,并将钢板用斧子剁成两半,以备两人同时刻写……
1937年9月初,在一个阴雨闷热的夜晚,他们在将屋内两扇窗户用席子遮好再蒙上一块黑布后,这个秘密“报馆”便开工了。
四个人做了简单分工。林墨农负责去友人家收听抄录新闻;顾建平负责总体编辑;程寒华与孔效儒承担具体编辑工作的同时,还负责刻写蜡板;而最后油印报纸、糊信封和分装递送,则四个人同时上阵。
这其中最苦的要数林墨农。从“报馆”到其朋友处,相距两里地,加上绕道,他每晚来回至少要走十里路,而且在宵禁戒严期间,进出日租界和中国地,日本宪兵搜查盘问甚严,他每次都是将抄到的稿件藏在贴身处,和日伪人员巧妙周旋,可谓险象环生。但林墨农对此却毫不畏惧,为节省时间减少麻烦,他费尽心思搞到了一个伪政府职员上下夜班时佩戴的白袖章,这样他便可以大摇大摆地去上“夜班”了。其具体工作时间是,每晚10点从“报馆”出发,11点到朋友处开始收听抄录南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午夜12点抄完,回到“报馆”已是翌日1点钟。随后,四人便开始了紧张的分工合作,直至凌晨五点钟左右,报纸正式印出,紧接着便是兴奋中带着惊险的秘密递送。
这是一张16开12张24版的“日报”,不仅有被日军严密封锁的战争新闻,而且还有特写报道、本埠新闻、社论、短评。创刊的最初三天,每天只印30份。10份送给他们最可靠的朋友,让朋友们在阅后继续传递。其余20份留存起来,以作日后补报之用。
就这样,在沦陷之初风雨如磐的天津,秘密抗战小报《高仲明纪事报》开始神秘地在苦闷中渴盼得到外界声音的市民中间流传了。当时正值淞沪大战的第二个月,许多震撼人心的胜利消息与感神泣鬼的忠勇故事,深深地鼓舞并感染着人们。发行第三天,就有一位大学校长送来了全年的“订报费”,在被婉拒后,他主动要求承担义务递送员,并决定秘密发展进步学生加入递送队伍。
很快,报纸发行量就由创刊时的10份增加到50份。20天后,升到400份。两个月后飙升到800份,其最高量曾达到千余份。读者的迅速增加,让顾建平等人即兴奋又始料不及,原来的四人单线递送已远远不能适应日益庞大的读者群,于是他们发明了“联保”的发行方式——扩充更多的进步人士加入到发行队伍,每个发行人都是单线与他们联系,其下线则是一大批读者,读者再将他们阅后的报纸继续向周边扩散,以此反复。同时,为了安全,他们还采取了“检举”与“调查”两项重大措施:前者请忠实的读者随时检举不忠实的阅报户;后者他们四人随时留意探听阅报户中哪个可疑。无论哪方面发现问题,立即取消对方阅报资格,并且通知其供给者,有时对供给者也予以同样措施,甚至将其所在的整条发行链停掉。
著名学者来新夏教授近年回忆,1937年7月29日天津沦陷后,他们全家几经辗转,最终逃难落脚到法租界绿牌电车道(今滨江道)教堂前一条名叫益德里(与顾建平等人秘密编印《高仲明纪事报》的天德里比邻)的胡同内。“大约快到旧历年底的时候,有一天清晨,我忽然在对着后门的窗台上发现摞着几张报纸。我偷偷打开窗户,又看看无人进出,便把这叠报纸拿进来,只见是几种油印小报,多是16开版,各刊版数不同,有多有少,有一张正反4版的,最多的一份是4张16版。刊名虽已记忆不清,但大都有抗战含义。内容主要是通报战况,像是从收音机中录下来的,有中央社的,有路透社的,也有美联社的。有胜利的喜讯,也有战败的消息,但战败有时用‘转移’字眼,如说国军经过几日与日寇激战后转移到某地,如果按地图追索,则是撤退。油印刊每天都有,但有时刊种不一,基本是免费,有时刊上也写定价,我即放点钱在窗台上,也会被收走的。过了旧历年,这类一直在送。我很好奇,总想看看送报人是谁,我曾起过几天早,但窗台上就已有油印刊了。有一次我有意在天蒙蒙亮时,就在窗帘后头偷窥,只见一个短打扮戴着齐眉破草帽的男子,把小报放在窗台上,一闪身就走出后门,我赶紧绕出后门,但已看不见送报人!这些默默的抗战人,可能在彻夜刻写印刷后,就分头投递,给闭塞窒息的人们,送来一丝亟待知道的或喜或愁的消息。我真诚地感谢这些不知名的真正中国人。祝福他们平安。”[《油印抗日报刊》,来新夏著,《来新夏随笔自选集•问学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3月初版,第276-277页。]
来先生回忆的,便是天津沦陷初期,地下抗战小报在民间秘密流传的往事。而他当时看到并留下深刻记忆的,很可能就是《高仲明纪事报》。
《高仲明纪事报》高额发行份数的背后,则是工作量的数倍增加,最让顾建平等人头疼的,便是需要调查每个阅读者的政治背景、居住环境,尤其是其周围是否有日本商户、洋行及汉奸住宅。此外,尚有每日印不完的报纸、糊不完的信封、买不完的纸张油墨和不能一次送出的邮件……而这一切,都是他们四人承担,因为他们做的是掉脑袋的秘密工作,不能大张旗鼓发动人去干。
《高仲明纪事报》犹如暗夜中的点点荧光,在真实报道抗战消息和迅速唤起人们抵抗情绪的同时,也很快便被日军及汉奸们发现,他们撒出眼线,在四处寻找这张可怕而又神秘的小报……
搜查中,秘密“报馆”几度搬迁
危险接踵而至。
一天夜晚,当林墨农从友人处抄听新闻回程途中,突遇日伪大搜捕,白袖章不管用了,他作为可疑人员被带到了宪兵队,万幸的是,审查他的是一个已附逆的报馆旧同事,他在胡拉乱扯讲了一番老同事们在事变后的各自遭遇后,引发了审查者的感慨,很快便被稀里糊涂地放走了。又一个夜晚,油印中的墨滚裂开了,程寒华连夜去亲戚家开的橡胶门市部去买,归途被一汉奸盯梢,在多走许多路七转八拐后,方才把尾巴甩掉……
面对危险情况,顾建平决定取消林墨农每晚外出抄听任务,他通过关系辗转结识了一位“慷慨”的朋友,此朋友在没问他做什么的情况下,心照不宣地主动送给他一台性能极佳的美国收音机。二十年后,顾建平才知道这位朋友是中共地下党员。
有了自己的收音机,他们又采取“买日本枪打日本”的方法,从日本崛井洋行以学校印讲义的名义,采买来一架日产轮转油印机。
设备添置更新后,外出危险大大降低,工作效率也相应提高,然而新的危险又接着出现。日产轮转油印机性能虽好,但噪音很大。一天凌晨,大家正在工作,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顾建平赶紧掐断电源从门缝挤出身来一看,原来是楼上房东的大儿子,他问顾建平在干什么,怎么屋内总是传出轰轰声。顾建平急中生智,连忙说,声音不是来自我屋,这是远处的炮声。就在房东儿子将信将疑走开之时,顾建平果断决定,此处已不宜久留,要立即搬家。
几经周折,顾建平等人最终看上了英租界益世滨道(今柳州路)与敦桥道(今西安道)相交处的益世里。这是一幢连体的二层小楼,他们选中了其中的11号,一楼由二房东一家自住,二楼他们以两家的名义全部租下。这里离法租界他们原来的“报馆”所在地天德里很近,站在露台上隔着不高的女儿墙便可清晰地看到法国教堂。
随即,在1937年11月初,秘密“报馆”在新址便按时“营业”了。
他们将那架轮转油印机放在铁床的帐幕后面,纸张油墨及各种资料平时均藏在米面袋中。为了掩人耳目,他们故意将收音机的天线、地线大大方方地架设好,每天从中午起,到夜晚11点以前,收音机总是大声地播放着北平电台的大鼓书或东京播送的日本歌,声音大得让全胡同的人都能听得见。而到了夜间11点,他们便把声音拧到最低限度,找到南京或长沙(后来是武汉、重庆)的中央社新闻电台,从《满江红》听起,把所有的新闻全部录下。然后再收听路透社、合众社的电讯,有时甚至能收到延安的广播。在他们的努力下,这些电台所播出的国共两党领导全民抗战的消息,及时地出现在秘密小报上,并在已成“孤岛”的天津沦陷区内传播,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抵抗斗志。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破南京城。随后,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开始了。
三天后,中国战区最高司令长官蒋介石在陪都重庆发表了著名的《告全国国民书》。继此前在庐山喊出“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东西南北,一致起来,长期抵抗”的抗日宣言后,再次疾呼“父勉其子,兄励其弟,长期抵抗,争取世世代代的自由!”
当顾建平等人在小楼里第一时间从重庆中央社新闻电台听到这一声音时,他们的悲壮情怀代替了心中的激动。当天夜里,他们便立即收录,立即刻版,立即印刷……一千八百多字的超长文告,让他们比平日整整延长了四个小时的工时,一直到日出后的九点多钟他们才印完发出。蒋介石在12月16日发出疾呼,17日早上,蒋之全文便刊登在了他们秘密油印的小报上,并已悄然“上市”。他们当时不知道,这与流亡在汉口的《大公报》《中西报》等国内权威大报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刊出了此文。
危险真的出现了!
就在顾建平等人发出这期报纸的当天中午,当他们带着一夜疲劳蒙头大睡时,英租界工部局的十多个侦探持枪破门而入。这本是一次突如其来却没有目标的大搜查,但他们四人的“作案”实证与工具却被起获。万幸的是,搜查人员中没有日本宪兵与高丽浪人,中英两国侦探对这些油印小报抱着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没对小楼进行彻底搜查,故而隐藏巧妙的收音机与油印机奇迹般地躲过了此劫
顾建平等人被英租界工部局逮捕了。面对审讯,顾建平侃侃而谈,力陈宣传抗日是中国人的本份,不违英租界之法,并反复讲述了日军在天津烧杀抢掠给平民百姓带来的灾难。或许是顾建平慷慨激昂的言辞引起了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华人副处长李汉元的同情,让他有了恻隐之心,第二天,顾建平等人在交了一大笔“保证金”后,便被取保释放了。但为了不让他们再给英租界找事,也为了给日本人一个交待,顾建平四人及家眷被驱逐出英租界,而且不许在英租界以外,用任何形式向英租界住民宣传“足以引起不幸事件”的思想。附带还有一项说明:“保证金”是无限期的不再退还。
搬出英租界,顾建平等人几经权衡,他们又秘密潜回发租界贝拉扣路,在原“报馆”所在地天德里附近的效康里31号租下了第三处“馆址”。
新“报馆”仍是一座二层小楼,这次他们全部租下,二层全部作“报馆”,一层他们在一位医生的指导下,挂上“山东曲阜孔氏制药厂”的招牌,成为“中西合璧”专门生产妇科药丸“坤宁珠”的小药厂。为了更安全地编好《纪事报》,他们让家眷分别住到了两层楼的四处,而且每家都安设了很完备的天线、地线,以备必要时可以轮流在各家随时收听中央广播,在各家随时都可以编印报纸。
在此后的日子里,他们白天在一楼药厂生产药丸,夜间在二楼“报馆”秘密编印报纸。黎明时刻,几辆挂着缀有药厂名字三角帆布包的自行车,便踏向了马路的四方。外人不可能知道,三角帆布包里,除了少量的小药丸,更多的是刚刚印出的《纪事报》。
为了安全,他们将后二楼的一个窗户打通,人员可以随时从窗户爬到楼后一个工厂的铁棚内。劫后幸存的收音机与油印机及其它文件资料便藏在铁棚内的一个破旧汽油桶内。夜晚取出,黎明送回,即便捷又安全,而且遇有紧急情况,人员也可从后窗撤离。
就这样,他们在这里坚持战斗了一年零九个月。他们所发出的平型关大捷、太原保卫战、上海保卫战、南京保卫战、台儿庄大战、徐州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华南保卫战的消息及战时评论,极大地鼓舞着身陷沦陷区的天津民众,让人们坚持抵抗,坚决不做亡国奴。这其中,虽然有不少战场失利的消息,但它对读者传递的信息却是:尽管屡战屡败,但我们还是要抗战,而且我们就在不屈不挠地抗战着。此外,每逢“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抗战”纪念日,他们还都编发特刊,号外发行,以示警醒。
最后的时刻到来了!
1939年9月28日,由于秘密小报引起了日本人的极度关注,他们终于闯入法租界,实施大搜查。秘密“报馆”终于被发现,虽然顾建平等人及家眷提前获知消息,已安全撤离,但“报馆”还是被日本宪兵队彻底破坏。至此,在天津沦陷后,坚持每日秘密出版达两年之久的《高仲明纪事报》,在天津消失了。
顾建平、林墨农、孔效儒、程寒华四人撤离天津后,分别去了游击区与大后方,继续从事着他们钟情的抗战与报纸编辑工作。
其实,在天津沦陷之初,国共两党地下人员在天津都曾编发过抗日报刊。如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姚依林便领导编印了《时代周刊》《抗日小报》《风雨同舟》《灯塔》等;而国民党中央社天津分社社长陈纯粹则主持编发了《实录》《长城》《吼声》《电稿》等。这些报刊在事变后的天津,都起到了唤起民众,坚持抵抗的作用。但如若论起坚持时间之久,秘密潜伏之深,每日坚持出报不辍和真实报道时局之迅速,则非顾建平等人所办的《高仲明纪事报》莫属。
【前言】
笔底江湖侠者风
——《旧报旧刊旧连载》序
王振良
在研究天津地方文史的大咖中,斯霆先生是我结识较晚的一位。大约是在2009年2月,筹备“津门论剑——民国北派通俗文学学术讨论会”过程中,才经由张元卿兄引见觌面。
不过若从名字的熟悉度来说,斯霆先生又是我很早就认知的一位。20世纪90年代,我还在南开大学读书的时侯,因为醉心于中国古代小说史,而触角不知不觉地延伸到民国通俗文学,为此保留过很多《天津日报》和《今晚报》的剪报,其中就有不少斯霆先生的文字。这些剪报散页,至今仍有部分“压箱底”幸存下来。
与斯霆先生的初次见面,颠覆了我对自己第六感官的自信:一是这家伙还很年轻,年纪尚未“半百”,而且说话嗓门大,措辞无遮拦,喝酒特爽快,很有些“大哥大”的做派,颇有些江湖侠者的范儿。让我尤其快意的,是他酒量特好,这就牢固了我们后来交往的基础。二是这家伙人高马大,块头够个儿,看不出来有哪点斯文儒雅,可只要沾上通俗文学话题,就晓得他装了一肚皮掌故,而且平时缺乏倾泻的对象。而我呢,一般来说少言少语,能够当极好的听众,最多充当个捧哏角色,故此两个人想生出矛盾都难。而在正式见面之前,我脑海中构筑的“倪斯霆先生”形象,与上面这两点都毫不搭边儿。
与斯霆先生的初次见面,回想起来又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通过参加“津门论剑”会议,激活了他对天津通俗文学热爱的细胞,重新回归到研究者的阵营;二是有意无意之间助推了《品报》的创办,进而使得天津的通俗文学研究队伍整齐起来,成果也逐渐显露。如果没有斯霆先生这个“民间大腕”存在,元卿、顾臻、林鸥和我,很难说就敢毅然扯起一面“品报”小旗子,因为当初我们就都很明白,这事不能纯粹依靠学院派,民间力量才是根本依托。当然话还得说回来,前述所谓两个后果可都是十分积极的,这也可以算是斯霆先生对通俗文学研究的特别贡献。
回顾新时期天津通俗文学研究的历史,斯霆先生是要拥有一席之地的,谁都甭想绕开。如果一定要梳理出这个发展脉络,可以说是滥觞于吴云心先生(主要成果见《吴云心文集》),奠基于张赣生先生(主要成果为《民国北派通俗小说论稿》),倪斯霆先生续脉操管呐喊于前,《品报》及其作者群继起遥相呼应于后。而在这一递嬗过程中,除了起到重要穿针引线作用的宫以仁先生,倪斯霆先生无疑是承前启后的最突出实践者。斯霆先生的父亲倪钟之前辈,是全国著名的曲艺史家,笔耕不辍,著作累身。应该是受这种家学影响,斯霆先生很早就对“俗玩意儿”有着特殊的亲近,十几岁时就从游于吴、张两位夫子之门,耳濡目染之下,他对天津通俗文学尤其是通俗小说钟情有加,这让他以后的笔底江湖显得多姿多彩。1997年至1998年间,斯霆先生在《通俗文学评论》分三期连载了《民国时期天津通俗小说创作与出版史话》长文,一举奠定了其以后的研究基础。而在此前后,他大量地给报纸撰写有关文章,对天津通俗文学的研究不断进行开拓和深化。稍微有些遗憾的是,新的世纪来临之后,斯霆先生成为《书报文摘》的总编辑,繁忙编务加上世俗诱饵,迫使他突然放弃所爱淡出江湖,有将近十年时间不再摆弄这类文字——一位经常披露文坛报海掌故的作者突然疏离报纸,这种突变后来竟至造成研究者的误会,斯霆先生本人也为此付出性命之代价,就是换来一顶“已故民国老报人”的帽子。这一不幸事件,发生在天津市国学研究会某次年会上,其时我恰好恬为相关文章的点评人,因此及时对这顶送错的帽子进行纠偏,可惜那位学者后来正式出版著作时,仍旧坚持了“已故”的说法,对此斯霆先生自然只能付诸一笑,我们若干帮闲者也就顺坡下驴,将此权当作新掌故来看待了。也幸好是印成了白纸黑字,给我亲历的这个段子留下佐证,确凿表明这故事(也可说是事故)并非出于我的杜撰或者演绎。
斯霆先生息影江湖的十来年,给自己换得“已故”标签的同时,也可以说是蓄势待发的十来年。虽然他不再挥洒有关文字,但资料搜集却一直坚持不懈,也就是说他从未放弃对通俗文学的爱恋。斯霆先生的家中,与其他很多藏者一样,自然也是满壁皆书,满地皆书,满床皆书……当然,书里还要搀杂着与通俗小说关系密切的报纸和刊物等。为了查找所存资料,斯霆先生还特意添置了“三宗宝”——木梯子、老花镜、望远镜。木梯子最好理解,书房里摆上此物利于攀爬登高不稀奇;老花镜也说得通,斯霆先生年未半百就有些花了眼;而望远镜呢,据云是用来寻觅书架上层藏品的,可惜了,书架顶天立地,他个头那么大,眼界那么高,可愣是不够用……至于老花镜和望远镜是否曾叠加使用,这一点我倒没问起过。
斯霆先生的资料累积,除了早年狠泡图书馆以及与前辈交游,主要是靠逛书摊搜罗。进步道、八里台、三宫、古文化街,还有狮子林桥下的海河右岸,这些不断变换的天津淘书人乐园,一直晃动着他高高大大的身影。每逢周末旧书集市,斯霆先生是雷打不动必定要现身的,有枣没枣都要插上一竿子,以此他与另两位常逛书摊的文史学者由国庆、侯福志,被朋友们调侃为海河书摊的“油泥猴”。
在相忘于江湖的十来年时间里,我们可以想见,斯霆先生是极为孤寂的。至于淡出江湖的缘由,除了忙于编报等公务,我觉得还有另外一重因素。虽然从来没有听到斯霆先生的自述,但是吴云心、张赣生两位夫子的离去,我想对于他是有着刻骨铭心影响的——随着前贤“拉力”的失去,斯霆先生的写作热情也渐渐消歇;而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新一批天津通俗文学研究爱好者的日益显露和《品报》民间学术群体的形成,他在后来者的“推力”之下才又重新激发动能,终于以2009年“津门论剑”会议的召开为契机,执笔挥剑重出江湖并迅速大放光华:2010年,《旧人旧事旧小说》出版;2012年,《旧文旧史旧版本》出版;2014年,《还珠楼主前传》出版;2016年,自然就是现在这本《旧报旧刊旧连载》了……
斯霆先生的学术思路略偏重于宏观,在史料钩沉考据的基础上,他特别乐于对作家作品作整体评判,用其密友也是文史学者罗文华先生的戏谑说法就是“爱搭大架子”,而正规些的学术表述则可称为具有“史家眼光”。作为旁观者的平心之论,斯霆先生的一些“大架子”,固然囿于基础资料有些似可商榷,但整体来说其“眼光”还是多富洞见并经得住检验的,这恐怕也是得益于家学——父亲就是曲艺史家啊。反观斯霆先生的微观考据,其实也是功夫了得的,比如关于还珠楼主来津时间的考察,关于白羽第一部武侠小说的订正,关于刘云若天津风俗描写的体悟,等等,这绝对是“三脚猫”式门外汉所无法胜任的。
斯霆先生与夫人都属牛,因此其书斋号称“双牛堂”。不过与其父钟之前辈的勤奋多产相比,斯霆先生只能说是一头懒牛。他的这几部书,除了出版社编辑的不断“督促”,周围的一帮小兄弟也是出了力气的——不是帮他查找资料录入文稿,而是每次见面均要“催逼”进度。幸好斯霆先生资料多、思路清,加上身体好、有蛮力,每每被督促催逼得急了,就会屏弃一切世俗杂务,集中个把月时间日夜赶写,一部书稿随之就能杀青了……
斯霆先生已出诸书的写作过程,是我根据片段信息推理而来的,但是我相信这推理的成立。如今,随着《旧人旧事旧小说》《旧文旧史旧版本》《旧报旧刊旧连载》这“九旧”写作目标的最终完成,《天津通俗小说史》也当是呼之欲出了!当然,斯霆先生的疏懒恐怕还是难改,这也就仍需要我们这些小兄弟拿起鞭子,大家肯定不好意思真的抽打他,那这懒牛就需要自策了!
2016年12月5日写定于沽上四平轩
【编辑推荐】
本书作者是天津通俗文学研究的专家,在史料钩沉考据的基础上,对民国时期的天津报刊、作家和作品作评判。书中对民国时期的天津报刊《天风报》《新天津画报》《庸报》《中南报》等从创立到停刊的经过,以及天津通俗文学作家还珠楼主、白羽、郑证因、刘云若等的一些具体事迹,作了较为严谨的考证,并用生动活泼的语言为读者还原出一个“活色生香”的民国时期天津通俗文学文坛。
- 名称
- 类型
- 大小
光盘服务联系方式: 020-38250260 客服QQ:4006604884
云图客服:
用户发送的提问,这种方式就需要有位在线客服来回答用户的问题,这种 就属于对话式的,问题是这种提问是否需要用户登录才能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