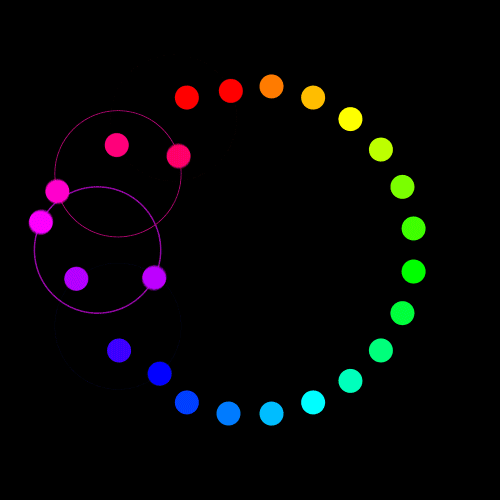简介
柏拉图的作品,除了对话录之外,还有十三封书简。这些书简是柏拉图实际写就,还是虚拟性的、类似于小说的文学创作,迄今仍是不解之谜。不管怎样,这些书简展现了柏拉图一生的行迹,犹如一面镜子,映射出柏拉图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以及柏拉图对哲学的理解。对理解柏拉图其人及其哲学而言,研读这些书简与研读对话录一样重要。
【目录】
引 言 / 1
上篇 柏拉图书简综论 / 5
一、柏拉图书简的真伪 / 7
二、版本源流与研究现状 / 19
三、柏拉图书简的戏剧结构 / 28
四、柏拉图书简的问候语 / 39
中篇 《书简七》研究 / 47
一、《书简七》的文学形式 / 49
二、柏拉图的自述(323d9–330b7) / 65
三、柏拉图的建议(330b8–337e2) / 113
四、柏拉图的哲学审查(337e3–345c3) / 149
五、狄奥尼修斯、狄翁与柏拉图(345c4–352a7) / 183
结 语 / 195
下篇 其他书简研究 / 199
参考文献 / 250
附录:柏拉图书简研究文献通览 / 253
【免费在线读】
柏拉图书简的戏剧结构
公元一世纪时,忒拉绪洛斯将三部对话(《米诺斯》、《法义》、《厄庇诺米斯》)加十三封书简排成一部四联剧(《名哲言行录》卷三,61)。这位古代编者并没把十三封书简从柏拉图的作品织体中排除出去,而是将十三封书简看成一部作品,且看成一部戏剧作品,与对话等量齐观。这一编排原则昭示我们两点:柏拉图书简与柏拉图对话具有某种相似性,因而可以编排在一起;柏拉图书简虽有十三封,但体现着某种统一性,因而可以视作一部作品。从这两点出发,似可把握柏拉图书简的性质。
**点与柏拉图的写作问题相关。众所周知,柏拉图从未写过纯思辨性的论说文,其写作几等于戏剧性的对话作品。但是,柏拉图为什么非写对话不可?
在讨论修辞术的《斐德若》中,苏格拉底指出写作有三大缺陷。其一,成文的言辞如一幅成型的画,看上去栩栩如生,其实已经僵死,“如果你问它们说的某种东西,想把意思搞懂,它们却总是翻来覆去讲同一套话”,换言之,它无法真正教诲学习者;其二,成文的言辞四处流传,没法区分读者,不知道该对谁说、不该对谁说;其三,一旦遭到误解和非难,它更没法辩解和维护自己(275d-e)。依苏格拉底看,任何撰述都难免有这些缺陷:不论是谁写,不论是曾经还是将要写下的,不论是关于法律、政治的还是关于私人的或是“关于任何东西”的,不论散文还是诗行,都无法完美地传授真相,都必然不够牢靠和透彻(277d-e)。
但苏格拉底还提到另一种写作。假如一个人拥有关于正义、美和善的知识,他就能够将一种言辞连带这些知识一道写在习者的灵魂中——而非定格在莎草纸上。这种言辞永远鲜活,能够卫护自己,而且懂得对谁该说、对谁该缄默(276a,c)。何谓写在灵魂中?苏格拉底拿农夫耕种打比方说,灵魂好比一块园子或土壤,写作者好比农夫,靠着“辩证术”拽住一颗合宜的灵魂,用这种含有知识的言辞把种子播散在灵魂里面,于是灵魂里也生出别的言辞,从而使种子永久不死(276e5-277a4)。因此,写作的技艺首先要求认识自己要说或所写的每样东西,其次要求认识灵魂的天性,再次要求找出适宜于每种灵魂的言辞。如此一来,写作就成了以合宜的方式与合宜的灵魂的交谈,它不再是僵死的,而是鲜活生动的“对话”(277b5-c6),因为写下的东西既出自作者的灵魂,又能在其他灵魂中自然地生长(278a-b)。显然,柏拉图对话就是这种写作的典范。柏拉图作为哲人,拥有“辩证术”和引导灵魂的技艺,在他笔下,对话总在特定的人物之间展开,以展现对不同灵魂类型的教育或劝说。可以说,柏拉图通过写作对话克服了写作的缺陷。假如我们把书简同样视作柏拉图的作品,是否也能把书简视作柏拉图的“写作”呢?
苏格拉底所说的“关于任何东西”的任何写作显然包括一般而言的书简:不论是谁写的,不论是政治性的还是私人性的书简。可以推想,一般的书简定然难脱苏格拉底所说的缺陷,对此不妨参考一个例证。与柏拉图同时代的修辞家伊索克拉底有九封书简传世,其中**封写给叙拉古僭主狄奥尼修斯一世,望其能担当未来希腊的运途,书简开头便说,“如果我还年轻些,我就不应给你写什么信,我应当乘船到你那里,亲自跟你交谈”。伊索克拉底宁愿面谈而不愿写信,但年迈的他无力承受舟车之苦,只得选择次好的方式。他在信中说明了写信不如面谈的原因:若给人出谋划策,当面说肯定胜过写信,这不仅因为面对面容易商讨,还因为“所有人都更加相信亲口说出的话,而不是写下的话,因为他们把前者看作实践性的建议,而把后者看作精心的编造”,更重要的是,如果所说的内容没有得到理解或相信,那就可以当场进行补救,而写下的书简一旦引起误解,就没人加以纠正或辩护了。这与苏格拉底所言何其相像!据此,我们不得不设想,柏拉图必定比伊索克拉底更明了书简的这些尴尬,他也必定会运用其写作技艺来克服这些尴尬,他的书简应当与对话一样,既能辨分不同的灵魂,又能为自己辩护。基于这一设想,我们就应当从柏拉图对话来理解柏拉图书简,既然对话和书简都属于柏拉图的写作,只有首先正确地阅读对话,领会柏拉图呈现教诲的方式,才能正确地阅读书简,并由此理解书简中的教诲。鉴于柏拉图对话的戏剧性,我们不由得猜想,柏拉图书简是否同样具有戏剧性?若是,我们就要遵照阅读柏拉图对话的原则来阅读柏拉图书简,不仅要注意书简的“内容”(柏拉图以及其他人物的言辞),也要注意书简的“形式”(比如书简的排序、收信人的身份、时间、场景、情节等),且要根据“形式”来理解“内容”。
可惜的是,十八世纪以来的柏拉图书简研究却循着一条历史考证的路子:抛开柏拉图的写作技艺,跑到后世的作家那里搜罗一切貌似与柏拉图和西西里相关的材料,然后细致地考证人名、地名、年代、时间,以期从柏拉图书简中构建起“真相”——当然,更重要的是借以断定柏拉图书简的真伪。“实证主义者们”固执地相信,柏拉图写下的一定是一份信实的记述,如果不信实的话,那肯定不是柏拉图写的。换言之,宁可相信普鲁塔克、奈波斯、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索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的说法,也不愿相信可能是“柏拉图的”说法。对此,我们可以提出:普鲁塔克、奈波斯等人的记述就一定是今天意义上的“历史”么?它们能够作为反驳“柏拉图”的充足理由吗?倘若“柏拉图”看似不可信的记述与后世作家的说法矛盾,难道我们不更应该从柏拉图的意图来考虑柏拉图为什么这么写而不那样写吗?假如这些书简是柏拉图所写,柏拉图为什么不可以像他写对话那样来写这些书简呢?尽管十三封书简表面上散漫芜杂、缺乏关联,但它们有可能像一篇对话一样有着精妙绝伦的织体,并且传达了某种严肃的教诲。要得到这样的发现,需要我们缓慢而深入地阅读,找寻柏拉图悉心留下的提示,因为柏拉图说,他总是会为少数读者留下蛛丝马迹让他们自己来发现(《书简七》341e2-3)。
其实,关于如何阅读书简,柏拉图留下了关键性的提示,但由于他的提示含糊莫测,而且塞在一封被视为“伪作”的书简里,所以极易被大多数人忽略掉:
至于那个符记——它可以表明哪些书简是我严肃写下的,哪些不是——我设想你还记得,可你还得加以理解,并且要凝神专注于它。因为,有许多人命令我写,要公然拒绝他们可并不容易。那严肃的书简以“神”开头,不那么严肃的书简则以“神们”开头。(《书简十三》363b1-6)
令人费解的是,柏拉图的十三封书简均不是以“神”或“神们”开头。我们是由此推断《书简十三》是伪篇,还是这样设想:某人说自己有A和B,可*后他从兜里掏出的既非A亦非B而是C,对于言行的不一致,我们应该相信他说的还是他做的呢?虽然柏拉图说他的书简以“神”或“神们”开头,可事实上没有哪篇书简如此开头,这便意味着柏拉图用事实—行动反驳了自己的言辞,换言之,“神”、“神们”的说法不过是一句玩笑话,实在没有必要当真,更没必要论证柏拉图所说的“神”是不是基督教的上帝。柏拉图的这一笔法并不稀奇,因为苏格拉底就认为“行动比言辞更可靠”,而且常常不是借由言辞而是借由行动表明他的看法(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卷四,4.10)。
不过,柏拉图却为我们指出,他的有些书简是严肃写下的,有些则不是严肃写下的,至少《书简十三》并不那么严肃。“神”与“神们”莫须有的区分又提示我们,这些书简既不是严肃写下的,也不是不严肃写下的,也就是说,它们混合着“严肃”和“游戏”。“严肃”就是认真、正经、热诚,“游戏”则是闹着玩、开玩笑,柏拉图的书信可能是半认真半玩笑的,既包含了严肃的教诲,又包含了游戏的成分。在另一封书简中,柏拉图又神秘兮兮地说:
你们还必须以这封信作为一条约定和一道至高的法——这是理所应当的——同时以一种不无品味的严肃和作为严肃之姊妹的戏谑起誓……(《书简六》323d1-2)
收信人要把柏拉图的书简看作神圣的约定和至高的法,这足够严肃了,何况还要向这封书简起誓!但柏拉图还要求他们,起誓时要混合着严肃和戏谑——这是柏拉图书简中严肃和戏谑的**一次对举。尽管这一对举在柏拉图对话中并不少见,但只有在这里,柏拉图才说游戏与严肃是一对姊妹。我们要以严肃和游戏相混合的态度看待柏拉图书简,这反过来提示我们,柏拉图是以严肃和游戏相混合的态度写下了他的书简。“游戏”是什么意思?这又要绕回《斐德若》。苏格拉底说,写下的言辞必然带有许多游戏(《斐德若》277e),因为写下的言辞是对口头言辞的“模仿”——口头言辞才是本真的,写下的言辞只是其影像(《斐德若》276a)——而“模仿”是**的“游戏”(《智术师》234b)。而“严肃”是什么意思?《书简七》对此说得*为详细:
每个严肃的人远远不会就那些严肃的主题写作,以免把它们抛入人群中,激起众人的妒意和疑惑。所以,蔽之一言,应当由此认识到,每当某人看到写成的著述——立法者法律方面的著述也好,任何其他方面的著述也好——这些著述之于作者并非*严肃的,若作者本人严肃的话,[之于作者*严肃的东西]藏于他那*美之域的某处。如果他把自己真正严肃从事的东西付诸文字,“那么一定是”凡人们而非诸神“亲手毁灭了你的心”。(《书简七》344c1-2)
柏拉图所严肃从事的不正是爱智慧吗?但真正严肃的东西不可说也不能说,因而不能付诸文字;但是,如何引导有天分的少数人也来追求严肃的东西呢?通过模仿,即通过影像来显现严肃之物,这一模仿的过程本身就是游戏。离开游戏,严肃之物也无从显示出来;离开严肃,游戏就无甚意义。大部分人停留于影像,少数人则通过影像上升到对严肃之物的领会,如此既能避免“激起众人的妒意和疑惑”,又能引导少数人走向哲学。故而,一位严肃之人的写作不可能非常严肃,必然带有很多游戏(《书简七》344c,《斐德若》276d-e,277e)。柏拉图对话不过是借以展现严肃之物的游戏。有不少人认为《书简七》的这段话是**严肃的,代表了柏拉图真正的写作观。但是,《书简七》同样是柏拉图写下的文字,而柏拉图并不会把自己严肃从事的东西付诸文字,所以,《书简七》中定然也包含着游戏,柏拉图书简同样是严肃与游戏的混合体。
下面我们试着看看柏拉图书简的游戏性或戏剧性何在。柏拉图在书简中悄声告诉给我们,他写过许多书简(见《书简三》315b,《书简十一》358e),**不止十三封。但是,我们所知的仅是十三封——这十三封中恰恰有一些本不应该流传下来:比如第二封,柏拉图曾嘱咐狄奥尼修斯把这封书简烧掉(《书简二》314c)。为什么只有十三封,为什么只是这十三封?
…………
目录
引 言 / 1
上篇 柏拉图书简综论 / 5
一、柏拉图书简的真伪 / 7
二、版本源流与研究现状 / 19
三、柏拉图书简的戏剧结构 / 28
四、柏拉图书简的问候语 / 39
中篇 《书简七》研究 / 47
一、《书简七》的文学形式 / 49
二、柏拉图的自述(323d9–330b7) / 65
三、柏拉图的建议(330b8–337e2) / 113
四、柏拉图的哲学审查(337e3–345c3) / 149
五、狄奥尼修斯、狄翁与柏拉图(345c4–352a7) / 183
结 语 / 195
下篇 其他书简研究 / 199
参考文献 / 250
附录:柏拉图书简研究文献通览 / 253
【免费在线读】
柏拉图书简的戏剧结构
公元一世纪时,忒拉绪洛斯将三部对话(《米诺斯》、《法义》、《厄庇诺米斯》)加十三封书简排成一部四联剧(《名哲言行录》卷三,61)。这位古代编者并没把十三封书简从柏拉图的作品织体中排除出去,而是将十三封书简看成一部作品,且看成一部戏剧作品,与对话等量齐观。这一编排原则昭示我们两点:柏拉图书简与柏拉图对话具有某种相似性,因而可以编排在一起;柏拉图书简虽有十三封,但体现着某种统一性,因而可以视作一部作品。从这两点出发,似可把握柏拉图书简的性质。
**点与柏拉图的写作问题相关。众所周知,柏拉图从未写过纯思辨性的论说文,其写作几等于戏剧性的对话作品。但是,柏拉图为什么非写对话不可?
在讨论修辞术的《斐德若》中,苏格拉底指出写作有三大缺陷。其一,成文的言辞如一幅成型的画,看上去栩栩如生,其实已经僵死,“如果你问它们说的某种东西,想把意思搞懂,它们却总是翻来覆去讲同一套话”,换言之,它无法真正教诲学习者;其二,成文的言辞四处流传,没法区分读者,不知道该对谁说、不该对谁说;其三,一旦遭到误解和非难,它更没法辩解和维护自己(275d-e)。依苏格拉底看,任何撰述都难免有这些缺陷:不论是谁写,不论是曾经还是将要写下的,不论是关于法律、政治的还是关于私人的或是“关于任何东西”的,不论散文还是诗行,都无法完美地传授真相,都必然不够牢靠和透彻(277d-e)。
但苏格拉底还提到另一种写作。假如一个人拥有关于正义、美和善的知识,他就能够将一种言辞连带这些知识一道写在习者的灵魂中——而非定格在莎草纸上。这种言辞永远鲜活,能够卫护自己,而且懂得对谁该说、对谁该缄默(276a,c)。何谓写在灵魂中?苏格拉底拿农夫耕种打比方说,灵魂好比一块园子或土壤,写作者好比农夫,靠着“辩证术”拽住一颗合宜的灵魂,用这种含有知识的言辞把种子播散在灵魂里面,于是灵魂里也生出别的言辞,从而使种子永久不死(276e5-277a4)。因此,写作的技艺首先要求认识自己要说或所写的每样东西,其次要求认识灵魂的天性,再次要求找出适宜于每种灵魂的言辞。如此一来,写作就成了以合宜的方式与合宜的灵魂的交谈,它不再是僵死的,而是鲜活生动的“对话”(277b5-c6),因为写下的东西既出自作者的灵魂,又能在其他灵魂中自然地生长(278a-b)。显然,柏拉图对话就是这种写作的典范。柏拉图作为哲人,拥有“辩证术”和引导灵魂的技艺,在他笔下,对话总在特定的人物之间展开,以展现对不同灵魂类型的教育或劝说。可以说,柏拉图通过写作对话克服了写作的缺陷。假如我们把书简同样视作柏拉图的作品,是否也能把书简视作柏拉图的“写作”呢?
苏格拉底所说的“关于任何东西”的任何写作显然包括一般而言的书简:不论是谁写的,不论是政治性的还是私人性的书简。可以推想,一般的书简定然难脱苏格拉底所说的缺陷,对此不妨参考一个例证。与柏拉图同时代的修辞家伊索克拉底有九封书简传世,其中**封写给叙拉古僭主狄奥尼修斯一世,望其能担当未来希腊的运途,书简开头便说,“如果我还年轻些,我就不应给你写什么信,我应当乘船到你那里,亲自跟你交谈”。伊索克拉底宁愿面谈而不愿写信,但年迈的他无力承受舟车之苦,只得选择次好的方式。他在信中说明了写信不如面谈的原因:若给人出谋划策,当面说肯定胜过写信,这不仅因为面对面容易商讨,还因为“所有人都更加相信亲口说出的话,而不是写下的话,因为他们把前者看作实践性的建议,而把后者看作精心的编造”,更重要的是,如果所说的内容没有得到理解或相信,那就可以当场进行补救,而写下的书简一旦引起误解,就没人加以纠正或辩护了。这与苏格拉底所言何其相像!据此,我们不得不设想,柏拉图必定比伊索克拉底更明了书简的这些尴尬,他也必定会运用其写作技艺来克服这些尴尬,他的书简应当与对话一样,既能辨分不同的灵魂,又能为自己辩护。基于这一设想,我们就应当从柏拉图对话来理解柏拉图书简,既然对话和书简都属于柏拉图的写作,只有首先正确地阅读对话,领会柏拉图呈现教诲的方式,才能正确地阅读书简,并由此理解书简中的教诲。鉴于柏拉图对话的戏剧性,我们不由得猜想,柏拉图书简是否同样具有戏剧性?若是,我们就要遵照阅读柏拉图对话的原则来阅读柏拉图书简,不仅要注意书简的“内容”(柏拉图以及其他人物的言辞),也要注意书简的“形式”(比如书简的排序、收信人的身份、时间、场景、情节等),且要根据“形式”来理解“内容”。
可惜的是,十八世纪以来的柏拉图书简研究却循着一条历史考证的路子:抛开柏拉图的写作技艺,跑到后世的作家那里搜罗一切貌似与柏拉图和西西里相关的材料,然后细致地考证人名、地名、年代、时间,以期从柏拉图书简中构建起“真相”——当然,更重要的是借以断定柏拉图书简的真伪。“实证主义者们”固执地相信,柏拉图写下的一定是一份信实的记述,如果不信实的话,那肯定不是柏拉图写的。换言之,宁可相信普鲁塔克、奈波斯、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索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的说法,也不愿相信可能是“柏拉图的”说法。对此,我们可以提出:普鲁塔克、奈波斯等人的记述就一定是今天意义上的“历史”么?它们能够作为反驳“柏拉图”的充足理由吗?倘若“柏拉图”看似不可信的记述与后世作家的说法矛盾,难道我们不更应该从柏拉图的意图来考虑柏拉图为什么这么写而不那样写吗?假如这些书简是柏拉图所写,柏拉图为什么不可以像他写对话那样来写这些书简呢?尽管十三封书简表面上散漫芜杂、缺乏关联,但它们有可能像一篇对话一样有着精妙绝伦的织体,并且传达了某种严肃的教诲。要得到这样的发现,需要我们缓慢而深入地阅读,找寻柏拉图悉心留下的提示,因为柏拉图说,他总是会为少数读者留下蛛丝马迹让他们自己来发现(《书简七》341e2-3)。
其实,关于如何阅读书简,柏拉图留下了关键性的提示,但由于他的提示含糊莫测,而且塞在一封被视为“伪作”的书简里,所以极易被大多数人忽略掉:
至于那个符记——它可以表明哪些书简是我严肃写下的,哪些不是——我设想你还记得,可你还得加以理解,并且要凝神专注于它。因为,有许多人命令我写,要公然拒绝他们可并不容易。那严肃的书简以“神”开头,不那么严肃的书简则以“神们”开头。(《书简十三》363b1-6)
令人费解的是,柏拉图的十三封书简均不是以“神”或“神们”开头。我们是由此推断《书简十三》是伪篇,还是这样设想:某人说自己有A和B,可*后他从兜里掏出的既非A亦非B而是C,对于言行的不一致,我们应该相信他说的还是他做的呢?虽然柏拉图说他的书简以“神”或“神们”开头,可事实上没有哪篇书简如此开头,这便意味着柏拉图用事实—行动反驳了自己的言辞,换言之,“神”、“神们”的说法不过是一句玩笑话,实在没有必要当真,更没必要论证柏拉图所说的“神”是不是基督教的上帝。柏拉图的这一笔法并不稀奇,因为苏格拉底就认为“行动比言辞更可靠”,而且常常不是借由言辞而是借由行动表明他的看法(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卷四,4.10)。
不过,柏拉图却为我们指出,他的有些书简是严肃写下的,有些则不是严肃写下的,至少《书简十三》并不那么严肃。“神”与“神们”莫须有的区分又提示我们,这些书简既不是严肃写下的,也不是不严肃写下的,也就是说,它们混合着“严肃”和“游戏”。“严肃”就是认真、正经、热诚,“游戏”则是闹着玩、开玩笑,柏拉图的书信可能是半认真半玩笑的,既包含了严肃的教诲,又包含了游戏的成分。在另一封书简中,柏拉图又神秘兮兮地说:
你们还必须以这封信作为一条约定和一道至高的法——这是理所应当的——同时以一种不无品味的严肃和作为严肃之姊妹的戏谑起誓……(《书简六》323d1-2)
收信人要把柏拉图的书简看作神圣的约定和至高的法,这足够严肃了,何况还要向这封书简起誓!但柏拉图还要求他们,起誓时要混合着严肃和戏谑——这是柏拉图书简中严肃和戏谑的**一次对举。尽管这一对举在柏拉图对话中并不少见,但只有在这里,柏拉图才说游戏与严肃是一对姊妹。我们要以严肃和游戏相混合的态度看待柏拉图书简,这反过来提示我们,柏拉图是以严肃和游戏相混合的态度写下了他的书简。“游戏”是什么意思?这又要绕回《斐德若》。苏格拉底说,写下的言辞必然带有许多游戏(《斐德若》277e),因为写下的言辞是对口头言辞的“模仿”——口头言辞才是本真的,写下的言辞只是其影像(《斐德若》276a)——而“模仿”是**的“游戏”(《智术师》234b)。而“严肃”是什么意思?《书简七》对此说得*为详细:
每个严肃的人远远不会就那些严肃的主题写作,以免把它们抛入人群中,激起众人的妒意和疑惑。所以,蔽之一言,应当由此认识到,每当某人看到写成的著述——立法者法律方面的著述也好,任何其他方面的著述也好——这些著述之于作者并非*严肃的,若作者本人严肃的话,[之于作者*严肃的东西]藏于他那*美之域的某处。如果他把自己真正严肃从事的东西付诸文字,“那么一定是”凡人们而非诸神“亲手毁灭了你的心”。(《书简七》344c1-2)
柏拉图所严肃从事的不正是爱智慧吗?但真正严肃的东西不可说也不能说,因而不能付诸文字;但是,如何引导有天分的少数人也来追求严肃的东西呢?通过模仿,即通过影像来显现严肃之物,这一模仿的过程本身就是游戏。离开游戏,严肃之物也无从显示出来;离开严肃,游戏就无甚意义。大部分人停留于影像,少数人则通过影像上升到对严肃之物的领会,如此既能避免“激起众人的妒意和疑惑”,又能引导少数人走向哲学。故而,一位严肃之人的写作不可能非常严肃,必然带有很多游戏(《书简七》344c,《斐德若》276d-e,277e)。柏拉图对话不过是借以展现严肃之物的游戏。有不少人认为《书简七》的这段话是**严肃的,代表了柏拉图真正的写作观。但是,《书简七》同样是柏拉图写下的文字,而柏拉图并不会把自己严肃从事的东西付诸文字,所以,《书简七》中定然也包含着游戏,柏拉图书简同样是严肃与游戏的混合体。
下面我们试着看看柏拉图书简的游戏性或戏剧性何在。柏拉图在书简中悄声告诉给我们,他写过许多书简(见《书简三》315b,《书简十一》358e),**不止十三封。但是,我们所知的仅是十三封——这十三封中恰恰有一些本不应该流传下来:比如第二封,柏拉图曾嘱咐狄奥尼修斯把这封书简烧掉(《书简二》314c)。为什么只有十三封,为什么只是这十三封?
…………
【作者简介】
彭磊,男,山东兖州人,哲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古典政治哲学、古典诗学。著有《苏格拉底的明智:〈卡尔米德〉绎读》(华夏出版社,2015年),译有《尼采与现时代》(合译)、《哲学是如何变成苏格拉底式的》(合译),编著《叙拉古的雅典异乡人:柏拉图〈书简七〉探幽》(华夏出版社,2010年)、《莎士比亚戏剧与政治哲学》(华夏出版社,2011年),主持并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柏拉图书信的翻译和研究”(2011)。
哲人与僭主:柏拉图书简研究
- 名称
- 类型
- 大小
光盘服务联系方式: 020-38250260 客服QQ:4006604884
云图客服:
用户发送的提问,这种方式就需要有位在线客服来回答用户的问题,这种 就属于对话式的,问题是这种提问是否需要用户登录才能提问
Video Player
×
Audio Player
×
pdf Play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