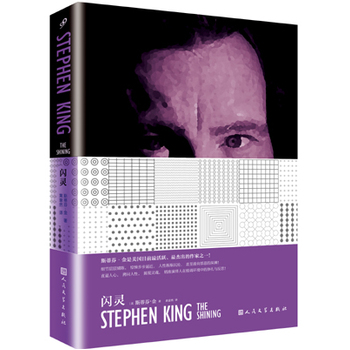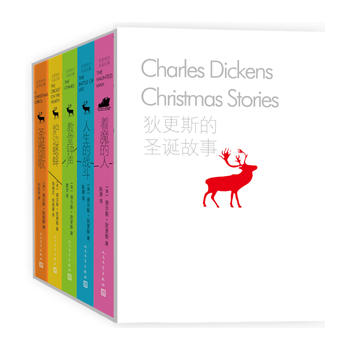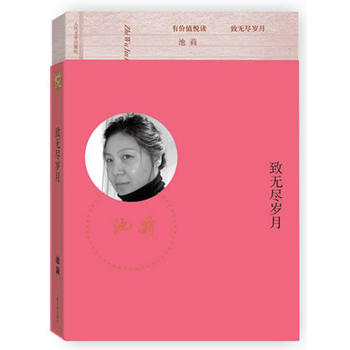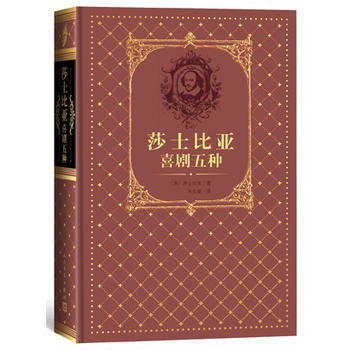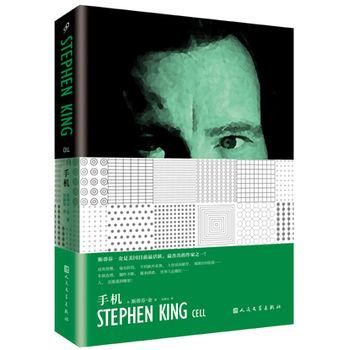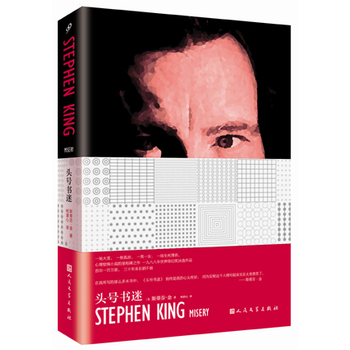共找到 22 项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1月” 相关结果
- 全部分类
- 全部
- 文学
- 历史
- 哲学/宗教
- 法律
- 政治/社会
- 医学
- 教育/心理学
- 艺术/传媒
- 研究生考试
- 资格认证考试
- 公开课
- 语言
- 经济金融
- 管理学
- IT/计算机
- 自然科学
- 工学/工程
- 体育
- 行业资料
- 音乐
- 汽车机械制造
- 文档模板
- 创业
- 农学
- 生活
- 数据库教程
- 民族
作者: 詹仁雄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1月
简介:马尔代夫的性感饭店旅游地点成立的原因很多,大部分的人要去何处,几乎都有明确的动机。去代官山是因为有一堆东西可以血拼,顺便弄清楚台湾的偶像歌手和主播宁愿冒着被偷拍的危险也要走访的原因。去巴黎是因为《欲望都市》的凯莉孤单走在塞纳-马恩省河畔的身影,让你想去体会多情女子在花都的情伤,也想去瞧瞧《达·芬奇密码》中藏着几个世纪秘密的卢浮宫,还因为Louis Vuitton在那边是在台湾的7.5折,这对某些人是最重要的一点,谁管凯莉嫁给谁、耶稣有没有谈过恋爱。去巴厘岛是因为连管理员伯伯都被女儿带去做过热石Spa了,自己只泡过阳明山温泉和做通化街脚底按摩的经验真是太端不上台面了。这些源于心灵底层被电视、电影、杂志或明星们影响后的声音,总会在需要休息或度假的时候,变成你旅游的领航员。而我,去马尔代夫的Hilton饭店,却纯粹是只是因为一封E-mail,一封一天收到三次的E-mail,没有任何的人生记忆参考依据。年终的一天,打开计算机后,分别收到来自不同的三个人,但标题都是“美到不行的梦幻饭店”的信件,在打开内容之前,我先说明一下我会互通电子邮件的网友们的类别:因为本人双子座的好奇心与喜新厌旧的特质,我绝少会收到什么劝人向善的心灵小语,而那些养生餐厅地图跟家具收纳的50招,我几乎没打开就转寄了。久了,我常收到的信件大概只剩两种:一种是美女们展现生命力的艺术照片,虽然艺术照这几个字我说得心虚,但在这种公开发行物上,我还是要优雅一点啦!另一种就是五花八门的怪东西了。这心态很有趣,有时大家像是互相较劲似的,如果信件不稀奇就像说了个冷笑话似的,所以我伟大的网络朋友们,寄来的大多会以严肃的筛选、搞笑方向的标准来满足我的好奇心态。也就是因为如此,连续收到三个人转寄来的同一个邮件,你就不难理解我对这封主旨为“美到不行的梦幻饭店”的信有着怎样一种期待了!打开信件后,我看见了一张张在碧海蓝天的饭店照片,载着饱和阳光的海上小屋,神奇地漂浮在如同画出来的海水上。 其实,马尔代夫的海很容易辨识。那种像苹果口味碳酸饮料颜色的乳青色海水,非常独特。会画画的人知道那是要用蓝色、绿色、白色等比例的颜料混在一起才会有的粉色系。人在这样的海洋,配上湛蓝无云的天空,会有处在明信片里的错觉。饭店大块大块原木建筑的海上屋,放在海天一色的背景里,视觉十分舒服,而最让人感到兴奋的是,它用玻璃做出的地板,透明又豪气的大玻璃就踩在脚下,这是个聪明的设计,因为马尔代夫岛屿旁的海水都不深,从客厅的地板就可以直接观赏魟鱼、魔鬼鱼、小丑鱼在你脚下的珊瑚礁穿梭。这跟你到夏威夷、普吉岛穿着黏黏的救生衣,跟一堆陌生人挤在玻璃船上15分钟,花
作者: 严平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1月 简介:最后的启航 一 再聚首 周扬和他的战友们再度聚首是七十年代末的事情了。1977年10月,头上还戴着三顶反动帽子在重庆图书馆抄写卡片的荒煤,明显地感觉到时代变革的来临,他辗转给周扬写了一封信,表示希望文艺界组织起来:尽管在‘四人帮’倒台后,才有少数同志和我通讯,过渝时看看我,但都对文艺界现状表示忧虑。领导没有个核心,没有组织,真叫人着急。 我真心盼望你和夏衍同志出来工作才好。(徐庆全《文坛拨乱反正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虽然历史上两次被周扬批判,“文革”入狱更与周扬分不开,在狱中,荒煤也从未想到有生之年还要和周扬并肩战斗。但当解冻的春风吹来时,他还是立刻就意识到文艺界需要一个核心,而这个核心仍非周扬莫属。 写这封信的时候,周扬从监狱出来赋闲在家已有两年。从四川到京看病的沙汀,怀着关切和期待的心情屡次前往周扬住处看望;张光年则利用自己复出的地位为周扬早日在文艺界露面创造条件;而文艺界更多的人士纷纷以写信、探望的形式表达自己对周扬的关注和期望。尽管有“两个凡是”的影响和“文艺黑线专政”论的阴影,但周扬在文艺界的地位似乎仍然故我。1977年12月30日,《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以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为主题的“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夏衍、冯乃超、曹靖华等一百多位老文艺工作者应邀出席。周扬首次露面,时任《人民文学》评论组组长的刘锡诚称,这是此次会议中最令人瞩目的事情。他清楚地记得,周扬到达会场时,已经过了预定的时间,大家都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待这位已经有十一个年头未曾露面的老领导的出现,当面容苍老了许多的周扬步入会场时,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周扬的心情显得异常激动,眼睛里闪着兴奋的光芒,刘锡诚说:大概因为这是周扬在多年失去自由后第一次在作家朋友们面前讲话的关系,显得很拘谨,用词很谨慎。他在讲话开始说,他被邀请参加《人民文学》召开的这个座谈会,觉得很幸福,感慨万端,他很虔诚地检讨了自己所犯的错误。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眼泪从他的脸上汹涌地流下来,他无法控制他自己的感情。他这次会上所做的检讨和自责,以及他的讲话的全部内容,得到了到会的许多文艺界人士的赞赏和谅解。 (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事后看,周扬当时的讲话虽然开放幅度并不很大,但他的出现不仅让在场的人感到了久别重逢的激动和喜悦,也给各地文艺界的人士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只停泊了十几年的大船虽然百孔千疮却没有被彻底摧毁,它将缓缓地收拾起碎片,调整好风帆,在大风来临的时候启航。 远在重庆的荒煤立刻就注意到了这个新的动向。在夏衍的鼎力相助下,他开始向中央申诉。很快,由邓小平批转中组部。1978年2月25日,平反结论终于下达。一个月后,荒煤在女儿的陪同下踏上了回京的列车。 那是一个早春的时节,在轰隆隆驶向北方的车厢里他怎么都无法入睡。1975年,作为周扬一案的重要成员,他被宣布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罪状仍有三条:一是叛徒;二是写过鼓吹国防文学的文章,对抗鲁迅;三是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一贯推行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定叛徒纯属捏造。后来他才知道,专案组一直为他的叛徒问题大伤脑筋,但江青一口咬定他是叛徒。她在接见专案组人员时说:“陈荒煤不能够没有任何材料,没有证据!”专案组工作人员插话说:“没有。”她仍然坚持道:“怎么没有呢?他叛变了!” 三年前,他就是戴着这三顶帽子,被两个从重庆来的人押着上了火车。临上车前专案组交给他一只箱子,那正是1966年夏天他接到通知匆忙赴京时拎着的一只小箱子。在列车洗漱间的镜子里他看见了自己,这是入狱七年来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模样,镜子里的人脸色浮肿而灰暗,目光呆痴,头发几乎全都掉光了,隆起的肚子却像是得了血吸虫病……他几乎不能相信自己变成了这个样子——那一年他六十二岁。 现在他回来了,三顶帽子虽然甩掉了“叛徒”一顶,还有两顶却仍旧戴在头上,这使他在激动不已的同时也感到了很深的压抑。不过他牢记夏衍的嘱咐,只要不是叛徒其他一切回京再说。重要的是速速回京!从报纸上发表的消息看,文艺界的一些老朋友已经纷纷露面,他是归来较晚的人。想到还有许多老友再也无法回来了,他们永远地消失在漫漫的黑夜中,眼泪就禁不住悄然涌上他的眼眶。 火车在七点多钟停靠站台。走出站口,灯光并不明亮的广场上,张光年、冯牧、李季、刘剑青等人急急地迎上前来,几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问候声、笑声响成一团,让荒煤在春寒料峭的夜晚感觉到一阵阵扑面而来的暖意。 从张光年的日记看,那天,这已是他们第二次前往车站迎候了。按照列车抵达的时间,一行人六点二十曾准时赶到车站,火车晚点一小时,于是他们回到离车站较近的光年家匆匆用过晚饭再次前往,终于接到了荒煤。很多年后,荒煤都能清楚地想起那个清冷的夜晚,人群熙攘的北京站广场上,那几张久违了的面孔。多年不见,他们虽然都已明显见老,但久经风霜的脸上,却充满着惊喜和掩饰不住的热情。 面容清癯精神矍铄的张光年先于他人而复出,此时已是《人民文学》主编,并担负着筹备恢复作协、《文艺报》的工作。这位诗人对自己在“文革”中的悲惨经历较少提及:“‘文革’初期那几年,我们这些由老干部、老教师、老文化人(科学家、文学家、文艺家等等),组成的‘黑帮’们,日日夜夜过的是什么日子?身受者不堪回忆。年轻人略有所闻。我此刻不愿提起。但愿给少不更事的‘红卫兵’留点脸面,给‘革命群众’留点脸面,也给我们自己留点脸面吧。”(张光年《向阳日记》引言,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5月)他最不能忍受的是,那个被江青操纵的中央专案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对他在十五岁时由地下共青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这段“历史问题”的长期纠缠。他最痛心的是,他的妹妹——一个与周扬从未见过面远在乌鲁木齐的中学教师,却因周扬“黑线”牵连而不堪凌辱自杀身亡;他的衰老怕事的老父亲因两次抄家受惊,脑血栓发作而去世……他自己在经历了残酷的斗争后又经历了七年干校时光,风餐露宿、面朝黄土背朝天,学会了在黑夜里喘息,也在黑夜里思考…… 1978年那晚的北京站广场,出现在荒煤面前的冯牧面色消瘦,声音却一如既往的干脆洪亮。青年时代起冯牧就饱受肺病折磨,父亲曾担心他活不到三十岁,他却带病逃离沦陷的北平,不仅经受了枪林弹雨的战争考验,还闯过了病魔把守的一道道险关。“文革”时,他和侯金镜等人因暗地诅咒林彪江青被关押,凶狠的造反派竟挥拳专门击打他失去了功能的左肺……他挺过来了。从干校回城看病的日子里,他曾经用篆刻排遣漫长的时光,倾心之作便是一方寄托了许多寓意的“久病延年”,“病”字既代表肉体上的创痛,也暗指那场席卷祖国大地的政治风暴带给人们心灵上无以复加的深切痛苦。当得知周扬从监狱中放出来的消息时,他和郭小川等人立刻赶去看望。为了不被人发现,用的是假名。那天,周扬看见他们激动的心情难以平复,说起在狱中,为了使鲁艺的同志不受牵连,为了防止络绎不绝的“外调者”发起突然袭击,他曾经一个个地努力回忆鲁艺的每一个人,竟然想起了二百多个人的名字……听到这里,冯牧和同去的人都禁不住流下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