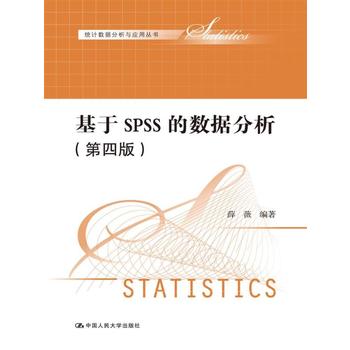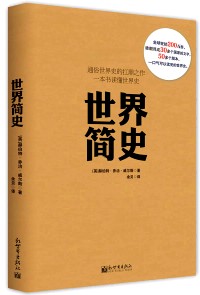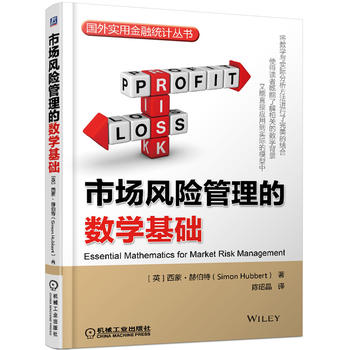共找到 751 项 “赫伯特” 相关结果
- 全部分类
- 全部
- 文学
- 历史
- 哲学/宗教
- 法律
- 政治/社会
- 医学
- 教育/心理学
- 艺术/传媒
- 研究生考试
- 资格认证考试
- 公开课
- 语言
- 经济金融
- 管理学
- IT/计算机
- 自然科学
- 工学/工程
- 体育
- 行业资料
- 音乐
- 汽车机械制造
- 文档模板
- 创业
- 农学
- 生活
- 数据库教程
- 民族
作者: (美)[S.加拉格尔]Simon Gallagher,(美)[S.赫伯特]Simon Herbert著;康博创作室译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纽约]:西蒙与舒斯特国际出版公司,1998
简介: PowerBuilder是具有图形界面的分布式数据前端工发工具,用以快速简捷地开发出面向对象的数据库应用程序。本书深入讲解了PowerBuilder对象和控件的各个方面,包括对DataWindow结象和控件的深入理解,如何创建和使用用户对象,有关DDE和)OLE2.0的概念,PowerBuilder和Internet, PowerBuilder的高级控件及Powersoft基类,分布式计算环境对于PowerBuilder的作用,以及PowerBuilser资源等所有方面。 本书不仅是一本概括了PowerBuider 6.0的所有功能和特征的大全,而且全书内容深入浅出,紧密结合编程实例讲解,使得本书不但适用于从事PowerBuilder6.0使用和开发的初级用户作为入门读物,而且更适用于PowerBuilder的中高级程序人员及有经验的高级用户使用。
Art Criticism in the 20th Century
作者: 沈语冰著
出版社: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
简介: 理论界流行着这样的见解:20世纪乃“批评的世纪”。单从一波接一波风起云涌的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ies]而言,这种说法似乎并不夸张。从上世纪初的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精神分析学派,到上世纪中叶的结构主义、新结构主义、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再到世纪末的新历史主义与后殖民文化批评,批评理论在20世纪的人文学科中确乎风光无限。即就视觉艺术批评来说,与上个世纪潮流迭起的艺术运动一样,艺术批评同样充满了精彩纷呈的景观:阿波利奈尔[Apollinaire]、罗杰·弗莱[Roger Fry]、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赫伯特·里德[Herbe rt Read]、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lGreenberg]、阿尔法雷德·巴尔[Alfred Barr]、哈罗德·罗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约翰·伯格[John Berger]、波普艺术批评家群体、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奥利瓦EOliwa]、阿瑟·邓托[Arthur Danto]、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罗莎琳·克劳斯[Rosalind Krauss]、彼得·贝格尔[Peter Burger]、加布利克[Suzi Gablik]、胡伊森[Huyssen]、T.J.克拉克[T.J.Clark]、麦克尔·弗莱德[Michael Fried]、西尔盖·吉博[Serge Guibaut]、唐纳德·库斯比特[Danald Kusbit]、希尔顿·克莱默[Hilton Kramer]、斯蒂芬·莫拉夫斯基[Stefan Morawski]以及,或许是上世纪最伟大的批评家泰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 然而,这些批评家及其理论在中国的命运却大不相同。当国内支学批评界对上世纪的各种文学批评理论如数家珍的时候,上述艺术批评家当中的许多人在国内艺术批评界甚至闻所未闻。艺术史向来被认为是本国史学中最弱的学科之一,而艺术批评理论的匮乏无疑加剧了它的不堪。上世纪最著名的艺术批评史家文丘利[Venturi]曾经断言:一切艺术史都是批评史,因为艺术史中对作品的描述、解释与评价无不涉及艺术批评,或者不妨说就是批评的任务。20世纪下半叶对西方艺术史的不满程度,可以从欧美各国质疑艺术史的方法论基础的出版物的持续升温这一事实中见出。可以这样说,批评理论的迅速发展已经改变了艺才史的方向。相应地,它的缺失也就成了国内艺术史学科的重灾区。 批评家作为现代艺术潮流的孵化者、报导者、仲裁者甚至制造者,早已被公认为当代艺术动力机制中的关键。试想一下这些批评家在催化与帮助人们理解那些艺术运动中的角色:弗莱之于后印象派、阿波利奈尔之于立体派、格林伯格之于抽象表现主义。也许,我们可以援引美国艺术批评家库斯比特的观点作为我们对艺术批评的一般性质的初步认知。他认为,艺术批评家的角色经常是悖谬的。因为当艺术品还很新鲜和怪异时,他就率先,常常是最鲜活地做出反应,并且初步向我们解释它的意义。然而,他的反应又常常不很全面,因为这样的艺术品还没有被广泛地体验过:作品尚未有一个历史,一个据此可以解释“文本”的语境。当批评家将艺术品当作一个当下产品来遭遇时,它还缺乏历史“负载”。事实上,批评家的部分工作就是要在历史的法庭上赢得胜诉。这就是为什么,正如波德莱尔所说,批评家经常是一个对艺术品“充满激情和党派性的观察家”,而不是对其价值做出无翻害的判断的裁判员的原因。正因为它的当代性,他扮演着鼓动家的角色,只能从作品本身的角度来处理整个案子。对敏感的批评家来说,作品始终让他感到惊异,而他则始终对它保持热度。他会让未来的历史家们去处理诸如解剖艺术品——到那时,它通常已被假定有一个公认的意义一一之类的事情。 然而,批评家当下的观点常常成为有关该作品的本质特征的基本评价。批评家的反应,如果说不是所有未来解释的范型,至少是所有未来解释的条件。他的关注是作品进入历史的门票。现代批评家权力的标志,就是他对新艺术的命名。比如,路易斯·沃塞尔[LouisVauxcelles]的标签“野兽派”和“立体派”就曾大大地影响了人们对这些风格的理解。通过命名,这些艺术品对未来的人们来说就被赋予了某种本质特征。而且,只不过以“符号圈地运动”[Semioticenclave]——借用乌贝托·埃科[Unberto Eco]的术语一一作为开端的理解,成了话语构型的一整套语言,并且开创了各种观点的全部氛围。说白了,其责任是重大的。格林伯格有一回曾写道,批判性地趋近艺术品的最佳时机是当它的新颖性已经逝去而它自身却尚未成为历史之时。然而,正是在这一时刻,艺术品的阐释最是未曾得到解决,最是易受攻击的时候;也是在这样的时刻,批评家以即席命名的形式所作的当机立断,能够一劳永逸地封存它的命运。因此,正如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在《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Critics as Artists]当中所说的那样,批评对艺术至关重要;批评把握、保存、培育、提升艺术。 由于对批评的效验估计不足,也由于对欧美上百年的现代艺术批评缺乏起码的参照,国内艺术批评多少尚处于黑暗中摸索阶段。最近10年来,虽有不少西方当代艺术材料被介绍进来,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甚至介绍者本人对这些材料也不甚了了(国内乱轰轰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研究即是明证),或者以一种绕口令般的伶牙利齿在美术界捣浆糊,使本来严肃的学术工作往往成为一场混仗。于是,甚至出现了——据说流行于美术学院——“西方艺术没有什么,他们要等到塞尚以后才有文人画”之类的荒谬绝伦的观点。如果说本书有什么主题的话,那么其中之一肯定是对这种观点的批评。正当我们奋力抵抗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时候,曾几何时,中国中心主义早已偷偷地从后门溜回来了。事实上,它又何曾从我们泱泱大国五千年文明的“中国”血液中离开过?将艺术界(包括艺术教育界)观念的混淆单纯地归结为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艺术批评(因为批评的原义之一就是“辨析”,亦即使观念尽可能清晰地得到表达),可能失之简单。但是,对西方艺术批评的漠视与无知,已经让我们的学生吃足了苦头。 后果之一便是今日中国艺术走向了两个——至少在我看来——毫无希望的极端。在一极,艺术成了一种单纯的笔墨游戏与自娱自乐,一群与当下感性毫不相关的文人雅玩或匠人的玩意见。这类所谓的画家像龟缩在洞穴中的爬行类动物,固执而有耐心地蛰伏在他们的弹丸之地,他们坚固的硬壳足以抵挡任何来自外界的风雨的骚扰,社会的转型、生活的演化、感受性的变迁、审美观念的变化,在他们看来都是毫无意义的东西,或者干脆是不存在的。其理论依据据说来自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文化矛盾学说,一种认为在经济一技术、政治一社会与审美一文化之间有着不同步的结构的观点。问题在于,在贝尔那里只是一种“事实”[fact]的描述(还是相互“矛盾”的事实),到了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那里却成了一种可以遵照无误的“规范”[norm]。另一种理论据说是波普尔[Karl Popper]的“问题情境”,学说与贡布里希[E.Gombrich]的“图式理论”,一利认为艺术史的风格是艺术家在一定的情境中解决艺术问题的结果的思想。在这儿,波普尔的多样性的“问题情境”被许多人还原为单纯的“形式问题”,而在贡布里希那里是如此丰富而多层次的“趣味逻辑”则被简化为纯粹的“程式与匹配”的“形式课题”(好像贡布里希从来没有关心过趣味的变化似的)。 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另一个理由据说来自“对20世纪中国艺术史逻辑的观照”。在他们的观照中,20世纪的所谓“三大艺术思潮”,即主张水墨画西化的徐悲鸿与主张中西融合的林风眠都或多或少地失败了,唯独主张“拉开中西绘画距离、各自迈向各自高峰”的潘天寿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并与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一道,成为20世纪中国艺术史上最伟岸的大师。本书作者无意否定上述诸人的成就,对诸大师之间(包括徐、林在内)的排队问题也丝毫不感兴趣。我想指出的只是这样一个从未或很少处在人们反思范围中的事实:即20世纪30至40年代的中国现代艺术(特别是在上海)是如何在上世纪中叶的政治运动与保守主义分子的群起而攻之之下渐渐消亡的。所谓“三大思潮”,不管是西化派、融合派还是距离派,在我看来,只是文化保守主义阵营内部的争吵。而20世纪中国艺术史真正的三大思潮中,只有文化保守主义获得了空前成功,来自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过去在国内就没有得到过心悦诚服的承认,如今则早已成为新左派批评家反刍的草料,而现代主义的罂粟却像昙花一样烟消云散。但是,它顽固的毒素在被压抑了整整30年以后,终于在80年代中期悄悄绽放。 第二个极端——在我看来是一个更阴险也是更恶毒的极端——就是在90年代以后以发烧似的热度迅速传播的流行性病毒:后现代主义。正如在欧美,后现代主义是无法挑战现存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左派激进冲动的一种替代性选择(特别参见法国少壮派理论家费里与雷诺[LucFerry and Alain Renaut]对后现代老大师们的反击之作《60年代的法国哲学》[French Philosophy of the Sixties],以及伊格尔顿[Eagleton]的《后现代主义的幻象》[The 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中国式后现代主义的盛行也是80年代末中国激进知识分子新启蒙运动受挫的结果,从此,后现代主义立刻成为文化保守主义与新左派的最佳救命稻草,并加速了文化保守主义与新左派在反对现代主义这一点上的同盟,再次完成了对8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的扼杀(情形与40年代末有着惊人的相似)。 后现代主义是兴起于西方60年代,在70年代达到猖獗的哲学、社会文化与艺术思潮。80年代初,主要由于哈贝马斯[Habermas]的分水岭之作《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方案》[Modernity:An UnfinishedProject]的宣读,西方思想界开始了对后现代主义的强大的批判运动。80与90年代西方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一个主题,可以被归结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争。这在思想界表现在伽达默尔/德里达[Gadamer/Derrida]之争、哈贝马斯/福柯[Habermas/Foucault]之争这样的大师级理论交锋中,表现在法国新生代思想家费里与雷诺等对前此20年中拉康[Lacon]、福柯、德里达、布尔迪厄[Bourdieu]、博德利亚尔[Baudrillard]、德勒兹[Deleuxe]与利奥塔[Lyotard]的压倒性后现代思潮的直接对抗上,体现在德国中生代思想家魏尔默[A.Wellmer]、霍内特[A.Honneth]与法兰克[M.Frank]对法国思想的全面挑战中。在批评界体现在希尔顿·克莱默对后现代主义“庸人的报复”(参同名批评文集The Revenge of the Philistines)所作的反击上,体现在哈贝马斯与魏尔默对詹克斯的“后现代主义建筑理论”所作的驳正上,也体现在艺术批评界持久的“沃霍尔[wlarh01]还是博伊斯[Beuys]”的争论中。在艺术运动中,它不仅体现在德国“新表现主义”对美国波普艺术的宣战中,体现在98-99年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所举办的波洛克EPollock]大型回顾展中(并比较80年代批评波洛克及其高度现代主义的著名论文集《波洛克之后》[Pollocck andAfte门,以及99年出版的“批判之批判”论文集《波洛克:新的取向》[Pollock:New Approaches]),还体现在人们对晚期德朗[Derain]、巴尔蒂斯[Balthus]与莫兰迪[Morandi]的具象绘画的那种持久高涨的热情中。 90年代以来,几个特殊的案例事实上已经宣判了作为一种持续的哲学、思想文化与艺术思潮的后现代主义的死亡,尽管它的某些假设还将产生持久的影响。这也是拙著《透支的想象:现代性哲学引论》(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的结论之一。在这些案例中,“海德格尔[Heidegger]事件”、“保罗·德·曼[Paul de Man]事件”与“索卡尔[Sokal]事件”具备足够的典型性。据说海德格尔是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只有维特根斯坦EWittgenstein]一人堪与媲美。但是,海氏将希腊的存在本体论、中世纪的神学本体论与现代的逻辑本体论,一视同仁地概念化为“存在一神一逻辑学”[Onto-Theo-Logik]是一种典型的削平论。相应地,他将苏格拉底以后的整个西方历史一律视为“远离神的黑暗”,并于20世纪来到“黑夜之夜将达夜半”的最黑暗时期,也是对西方历史的过分简化的图解(显然是尼采的反启蒙思想“人类历史不是一部进步史,而是一部退化史”的翻版)。由于海德格尔戴上了这样一副哲学墨镜,他就不可能对20世纪现实中的色彩与层次做出区分,从而将国家社会主义、极权主义与自由民主制一律视为“现代性的产物”。在他看来,德国纳粹主义、苏联共产主义与美国自由主义,统统都是“同一回事”。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他在德国纳粹运动中以及在其后的“非纳粹化”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海德格尔事件”的复杂之处固然不容许人们在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与他的在世行动中做简单的彼此类推,亦即,说海德格尔的思想直接导致了他的纳粹行为,或者说海德格尔一度的行为证明了他的思想是纳粹主义的,这都是不明智的。但是,如果说海德格尔的思想,再宽泛一点讲,德国20-30年代右翼知识分子(海德格尔、容格尔[Ernst Junger]、舍勒尔[Max Scheler]、卡尔·施米特[Karl SChmitt],“汉语学界”右翼知识分子最为心仪的“四尔”)叫嚣着大地、鲜血、战争、种族的非理性主义思潮,与纳粹意识形态之间没有一点关联,那也委实太天真了! 上世纪60年代,基本上由尼采与海德格尔培育出来的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潮,漂洋过海去到美国后,在美国获得了更为露骨的后现代主义动机。正当美国陷于越战的泥潭而遭致自由民主价值的最大的合法性危机之时,由德里达打头,所谓的“耶鲁四人帮”为后盾的美国后现代主义思潮迅速地在全球漫延开来。其中最著名者,叫保罗·德·曼。此人极其聪明,文笔流畅,思路清晰。其基本观点是,一切文本都是作者袒露与隐瞒的运作,记忆与遗忘的策略。一切阅读都是误读。而写作与阅读则构成作者与读者之间一种揭露与掩盖、设访与投射的游戏。80年代末,从他年轻时期的某些档案材料中,人们发现了他原来是纳粹时期一个积极的反犹主义者。于是,美国大学特别是英文系里那些天真的解构主义信奉者们,突然惊讶地意识到了某个事实:解构主义与罪恶意识的压抑(遗忘)之间的不经意流露的关联。 90年代初,美国的“索卡尔事件”使后现代主义的最后一点美丽幻象也破灭了。索卡尔是一位美国物理学家,他花费了差不多整整两年的时间,处心积虑地炮制了一篇题为《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Toward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的诈文,其中充满了常识性科学错误同时却充斥了后现代主义者最喜爱的奇思妙想与时髦术语,并把它投给了美国最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刊物之一《社会文本》[SocialContext](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座上宾詹明信[F.Jameson]是该刊的主编之一),结果是,此文被登了出来。尽管这一事件的深远意义远未为人们充分意识到,但是,人们普遍认为,此举表明了后现代主义者的学术水准已经下降到了何种荒唐的地步。 可以并不夸张地说,上述三个事件事实上已经宣告了哲学、文学艺术与社会文化三个层次上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破产。“事件”之所以为“事件”,乃是因为人们在其中倾注了大量热情,因而卷入了无数文献。围绕着这些事件,人们能够组织起纷纭的思绪,从而给予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以实体表现的形式。而这个时代精神状况则是:人们对于后现代主义应当被理解为20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的一种病理症状对一点已经获得了清楚的自我意识。后现代主义以其智性上的反理性主义、道德上的犬儒主义与感性上的快乐主义,即便在最为流行的时候,也没有逃脱西方有识之士的尖锐批判。本书多次提及的哈贝马斯就是这样一位思想家。而另外一些学者,则将后现代主义看成西方高度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的一个反题。现在,走向终点的反题已经失去了昔日的锋芒,一种新的综合开始到来。那就是“后现代之后”:魏尔默与霍内特之坚持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辩证观,当作如是解。然而,本书作者宁愿坚持一种拓展了内涵的现代主义立场,并认为哈贝马斯的“未完成的现代性”,或贝格尔的“后前卫艺术”的提法更为可取。因为,如果说现代主义是西方现代艺术的正题,那么,贝格尔所说的旨在摧毁现代主义自主原则的“历史前卫艺术”[historicalavant-garde,指达达主义、早期超现实主义与苏俄前卫艺术]才是现代主义的反题。而后现代主义,某种意义上只是欧洲历史前卫艺术(以杜桑[Duchamp]为代表)的延续,某种意义上则是欧洲历史前卫艺术的一个搞笑的美国版(以沃霍尔为代表,参本书所述胡伊森精彩的分析)。因此,导源于对现代性的敏感意识的现代主义,其潜力远未穷尽,而它在遭遇历史前卫艺术与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后,反而显出了更顽强的生命力。这就是本书结论中所说的“无边的现代主义”的基本意思。 然而,正当后现代主义在它的原发地已经走向终结的时候,它在中国却获得了始料未及的繁衍契机。与某些论者不同,本书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将中国式后现代主义归结为学术界与艺术界鹦鹉学舌的结果(所谓“话语的平移”)。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着深层次的历史原因,也有着更为具体可感的现实动机。后现代主义的反基础主义、反总体性、反主体性、强调动态过程胜于静态结构,与中国前现代性思维是如此合拍,以至于人们稍加思索就不难从后现代主义当中辨别出中国保守主义者的弦外之音。而它所宣扬的后现代主义视觉美学:非线性几何、不对称、反崇高、散点透视乃至中国园林式“后现代空间”……也与中国前现代性美学如出一辙。不是偶然的是,西方鼓吹后现代主义建筑最起劲的查尔斯·詹克斯先生的太太就是一位研究中国园林的专家。而欧美某些后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到中国来兜了一圈后欣快地大叫“后现代建筑在中国”,也就不难理解。于是,贫困时代的灾难性混乱、粗野的地方性崇拜与不加克制的复活主义立刻被宣布为后现代性的前卫性。而近年所谓“经济起飞年代”的那些拙劣的伪现代建筑与陈词滥调的现代主义当然不加区分地被宣布为“现代主义的垃圾”。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落脚的时候,正是80年代尚未分化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新启蒙”遭到重创的时候。这赋予了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干载难逢的大好机会。由90年代初的北京大学出版的《走向后现代主义》开路,北大与中国社科院一路高歌走向“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出版事业大游行:《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后殖民文化批评》,直到蔚为大观的“知识分子图书馆”(似乎只有后现代主义分子才配称得上“知识分子”的称号)。显然,除了迎合文化保守主义的心态,后现代主义太切合新左派的胃口了。在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与新左派眼里,难道还有比批判形而上学的恐怖主义、理性社会的大监狱、西方中心主义的险恶用心、自由民主的乌托邦、全球化的谎言,宣扬身份与差异、文化与价值相对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更好的东西吗? 与保守主义者忽然从后现代主义中找到了中国前现代性的新的合法性一样,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则从西方后现代主义“没有底盘的游戏”(德里达)、“一切皆可”(邓托)、“快乐的虚无主义”(奥利瓦)以及“正经不起来”(苏姗·桑塔格[Susan Sontag])那里,发明了“政治波普”、“泼皮现实主义”、“新文人画”、“玩得就是心跳”、“一点正经没有”,以及各式各样假冒的观念艺术。但是,与保守主义的危险不同,中国式后现代主义的危险并不在于它成了与当下感性全然无关的形式玩物与装饰,而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不顾一切形式法则与视觉质量的纯粹的观念。西方“历史前卫艺术”的合理因素在于:他们的反形式[anti-form]与反艺术[anti-art]是建立在西方现代艺术史特别是经典现代主义的高度形式主义的正题之上的。这样,前卫艺术的反题才拥有了一定的合法性。而中国式后现代主义在没有任何语境的前提下,一下子走到了反形式的前卫艺术,因此它除了孤零零的个别事件之外,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效应。不仅如此,它的真正危险在于,它以貌似激进的观念掩盖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国现代性的先天不健全;并以这种思想的短路形式扼杀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现代性诉求。 在本书即将完成之际,我读到了英国著名批评理论家伊格尔顿的如下一段话:“今天在北京大学设有一个后现代研究的机构,中国在进口减肥可乐的同时一起进口德里达。一种需要深入探讨的时间扭曲。殖民主义的进程有助于在好坏两方面剥夺第三世界社会的发达的现代性,现在这个进程让位于新殖民主义的进程,由于这个新的进程,那些部分地是前现代性的结构被吸入了西方后现代性的旋涡。这样,没有继承一种成熟的现代性的岳现代性日益戒为它们的命运,好像落伍造成了一种形式的早熟。一个进一步的矛盾是,在古老与先锋的痛苦张力中,在文化的领域里,再造了一种现代主义艺术的某些经典条件。”(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第139页)中国是否已经具备了现代主义艺术的经典条件,本书暂且不论。这里能说的是,从意识到我们的参照系的情形——西方现代主义事业的未竟使命及其后现代主义的幻觉——的那一刻起,这种条件就已经在形成之中了。因为,意识的照亮之处,正是救赎的开始之时。本书作者并不自命为这一救赎的努力当中的一部分。我只能满足于在四处弥漫着的文化保守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大雾中保持清醒的尝试,并且坚信,正如文化保守主义一后现代主义同盟曾经欢呼雀跃地宣布中国可以并且应当绕过现代性直接跃入岳现代性是一场白日梦一样,那种认为后现代主义乃是中国艺术的命运的说法也只不过是一纸谎言。曾几何时,人们是那么醉心于中国可以避开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化的现代性命题直奔信息化、乡土化与社群化的“后工业社会”的美梦,然而,一个越来越被认可的事实却是:中国一向试图绕过去的工业化进程、市场法则、理性化管理、程序合理性、法治原则,乃至于统治的正当性基础,却原来是绕不过去的现代性的硬核!而我们在走向社会的现代化与文化的现代性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挫折,无不可以追溯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没有从思想意识到行为习惯上真正确立主体性——黑格尔认为的现代性的本质——的基础地位。回顾中国式后现代主义狂热对“主体性”的嘲笑与“解构”,难道还不让人感到啼笑皆非吗!事实上,文化的中断与意义的失落(我们在处理传统与现代性问题上的曲折与反复)、社会的未分化和并非建立在真正的个体主体性基础之上的社会的虚假团结,以及个性的匮乏,解释了以下社会现实:由于我们在处理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上的笨拙,以至于“创新”需要被当作一种政治口号由政府来加以提倡;由于我们并没有真正确立起一种自我选择、自我负责的现代性的自律道德的基础,以至于“诚信”居然成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文化的文明礼仪之邦”在遭遇现代市场法则与新型人际关系时的最大问题;由于强大的儒家传统与20世纪极左派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对个体主义的压抑,以至于“个性”的不健全始终成为中国各种社会现象最有解释力的终极原因:由于缺乏个性,整个社会才循环地陷于各种“群众运动”之中;由于没有个性,整个社会才经常承受着未分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没有多元的价值体系及其相应的多元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以至于,人们可以说,一个庞大的无边无际的来分化社会的海洋(特鄹是农村),为顽固的文亿保守主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社会资源;雨一个尚来形成自我意识中心、自我价值定位与自我道德承担的“无中心的”[non-centered]个人。恰恰成了“去中心的”[de-centered]、啕醉迷狂的、“一切皆可的”和不负责任的后现代主义的最佳温床。 本书出版之际,我感到更加有必要感谢徐岱、高力克、毛丹、孙周兴、刘翔诸位先生,他们把我从结束学生生涯不久后的那种心智懈怠与无所事事中挽救了出来。回顾近十年的学术道路,我所取得的每一次转机都与他们在浙大玉泉校区所营造的智性氛围有关。对老浙大的怀念已成为一种珍贵的人生体验。没有一种氛围,一个人什么也干不来。因为你不可能在毫无氛围的情况下凝聚起纷乱的思绪。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还有幸前往剑桥大学从事为期一年的访学研究。在此要特别感谢剑桥大学艺术史系主任Dr.Binsky,他的热情好客使我得以自由地使用他们丰富完备的系图书馆和幻灯资料室。而Dr.Alice Mahon的现代艺术史专家与三一学院Fellow的双重身份,不仅给予了我直接的专业指导,而且还让我领略了最古老学院的日常生活气氛。我在剑桥的东道主哲学系则使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剑桥名士”们的风采。Dr.Raymond Geuss令人惊叹的慷慨博达与逸情雅致,常常令人如沐春风、豁然开朗。他的个人背景(出身于美国、长期就学与就勃于德国)及其德国思想史的学术背景,让我在一个视哲学基本为数理逻辑的剑桥环境中找到了“知音”。本书的最后体例就是在与他的无数次讨论之后才确定下来的。 其后去欧陆的游历虽然短暂,但至少部分地实现了我从少年时代就开始编织的梦想。艺术在这里 见证了天地人神四方际会、供奉与馈增的游戏(巴台农神庙),见证了古典时代的英雄精神(万神殿),见证了中古时期神明与圣明的在场(“欧洲大教堂”),也见证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性与神性的卓越平衡。置身于欧洲就是徜徉于艺术。置身于欧洲意味着要回答如下问题:艺术之为美的形式如何与艺术之为真理的在场以及艺术之为道德的进盼相互关联?[How an art as the beau tiful form is related to an art as the present of truth and the stageto morality?]置身于欧洲还意味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一种伟大的文明如何屹立于地表,以及在这种伟大的文明中,艺术能够扮演何种伟大的角色?欧洲是真理的声音战胜虚无主义的历史本身,是道德的力量战胜犬儒主义的历史本身,是艺术的激情战胜猥琐无聊的历史本身。而这一历史本身又是如此直观地凝固在欧洲的城市建筑、广场、雕塑以及各大博物馆中!我在欧洲的经历使我懂得,一种伟大的艺术如何可能,以及一种伟大的文明最终怎样结晶于伟大的艺术之中!这一信念已经深深地沉淀于本书的血脉中了。 在我感到有必要感谢的人当中,范景中先生的位置绝对位于前列。我深受其思想影响的人当中至少有两人(波普尔与贡布里希)与他的出色工作有关。因此,当范先生询问我可否将此书交给中国美院出版社出版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对写书的人来说,没有比遇到一位好编辑更幸运的事了。周书田女士热情而又高度负责的态度使本书得以最快的速度与读者见面。她不厌其烦地编选与调整大量插图,也使本书严肃的理论面孔变得可忍受了。 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我要感谢一直陪伴我左右的两位女士。她们对我的爱怜与纵容是我生活中的永恒慰藉。刚到欧洲时的单身生活使我更加刻骨铭心地感受到了她们在我生命中的位置。她俩的到来使我的生活得以恢复,并着手此书的写作,因此,把它献给她们,理所当然。
作者: 石涛编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2014
简介:《如何阅读一本书》编辑推荐:聆听大师的真知灼见,享受阅读的饕餮盛宴。林语堂、鲁迅、朱自清、梁实秋、福楼拜、苏珊?桑塔格、弥尔顿、瓦尔特?本雅明、翁贝托?艾柯、蒙田、罗伯?卡普兰、安娜?昆丁兰、威廉?塔哥、赫伯特?韦斯特、艾丝黛拉?艾利斯和卡罗琳?西博、阿尔弗雷德?塞弗曼、A?罗森巴赫、爱德华?纽顿、哈罗德?拉宾诺维奇、约翰?米歇、罗伯逊?戴维斯、托马斯?西晋生、索利?加诺尔、罗杰?罗森布莱特、斯图亚特?布朗特,与大师一起分享读书的艺术和乐趣!
作者: 薛薇 编著
简介: 数据分析的核心方法是统计。统计实践的有效工具是SPSS。快速掌握SPSS的正确途径是选择一本从SPSS数据分析“零起点”到“大玩家”的好书。它使读者不再感到数据分析高不可攀,实践过程无章可循,统计理论晦涩难懂,结果解读似是而非,而是让读者成为对SPSS应用高屋建瓴、对方法运用游刃有余、对软件操作融会贯通、对结果解读豁然开朗的数据分析高手。《基于SPSS的数据分析(第三版)》一直不懈地坚持着这个目标并努力成为先行者。 正如英国著名作家赫伯特·乔治·韦尔斯所预言的,“统计思维总有一天会像读与写一样成为一个有效率公民的必备能力。”这个时代正在到来,请从本书开始,勇敢迈出数据分析实践的第一步!
作者: (美)赫伯特·布曼(Herbert D.Bowman)著;丁相顺,金云峰译
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
简介: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作了颇有意义的修改。一些修改指出了中国刑事审判的改革方向。这些修改表明,要在庭审中更多地运用证人出庭作证的方式。这要求中国的法律职业者,无论是检察官还是辩护律师,在法庭审判过程中要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总之,这些修改代表了向确立更加具有抗辩性法庭审判的方式的方向。 做出这些修改以后,新的规定和其实施之间还存在着差距。这种差距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因为某些修改的条款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解释和界定;同时,也由于中国的法官和律师欠缺参与抗辩式庭审的经验。 这本教材旨在帮助中国法官、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学会如何缩小新法规定与实施之间的差距,主要解决如何使中国刑事庭审更富抗辩性。本教材集中关注那些有助于营造出更富抗辩式审判环境的问题,营造这种环境将有利于提升中国刑事庭审查明事实的能力以及提高被告人的权利保护水平。 为了能达到这种效果,这本教材提供了国际公正审判标准方面的相关知识,对抗辩式审判程序本源和构成要素进行了讨论。这样,将在国际标准和中国新刑事诉讼的框架内,给中国的实务家提供不同的视角和相关背景知识,同时也可以启发思路,发现调整中国刑事司法实践的方法。然而,这本教材主要目的是向中国法律职业者——无论是检察官还是辩护律师——提供信息,帮助他们提高辩护技巧,并将其运用到新刑事诉讼法所鼓励的更加积极和抗辩的法庭审判环境中去。编写这本教材是为了提高控辩双方庭审前的准备能力,提高他们在法庭上询问证人和开示证据的能力,以及更加有效地在法庭上陈述观点的能力。
作者: (加)赫伯特·马歇尔·麦克卢汉(Herert Marshall Mcluhan)著
简介:本书是一部媒介文化研究的经典著作。作者认为,电话、电报、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的广泛使用,塑造了一个新的文化形态和传播方式。通过对不同媒介的比较,以及与种种文化现象的关联,作者勾画了一种电子媒介文化社会的图景,并对其发展趋向作出了某些预言。 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人与动物的根本差异,就在于人的未特定化,因而人有超越自然的文化。哲学家深信,人不但生活在物理的世界中,同时也生活在符号的世界中。所以,亚里士多德“人是逻各斯的动物”这一经典定义,可作如下新解:人是符号和文化的动物。 人创造文化,又被
作者: 赫伯特·金迪斯
简介:本书是一部以问题为中心介绍经典博弈论和演化博弈论的教材。博弈论在逻辑上的要求很高,但是在实际应用层面上,它需要的数学技巧非 常少。代数、微积分再加上基本的概率论就足够了。相对而言,读者需要有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博弈论通常会需要大量的符号来清晰地表达思想。读者应该牢记每个术语的精确定义,以及大部分定理的准确表述。本书的一大特点是,对于其中的大部分主题,作者在解决问题时会充分讨论相关的定义、概念、定理并举例说明。相信本书的出版,对应博弈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将会起到非常好的促进作用。
作者: 薛薇
简介:
数据分析的核心方法是统计。统计实践的有效工具是SPSS。快速掌握SPSS的正确途径是选择一本从SPSS数据分析“零起点”到“大玩家”的好书。它使读者不再感到数据分析高不可攀、实践过程无章可循、统计理论晦涩难懂、结果解读似是而非,而是让读者成为对SPSS应用高屋建瓴、对方法运用游刃有余、对软件操作融会贯通、对结果解读令人豁然开朗的数据分析高手。《基于SPSS的数据分析(第四版)》一直不懈地坚持着这个目标并努力成为先行者。
正像英国著名作家赫伯特?乔治?韦尔斯所预言的,“统计思维总有一天会像读与写一样成为一个有效率公民的必备能力!”。这个时代已经到来,请从本书开始,勇敢迈出数据分析实践的*步!
作者: 丹·西蒙斯(Dan Simmons)著;潘振华,官善明,李懿译
出版社:万卷出版公司,2007
简介: ★深受斯蒂芬·金敬仰的作品! ★《轨迹》杂志票选1990年前史上十大科幻小说 ★“最推荐100部科幻奇幻作品榜”上榜作品 [内容简介] 本书书名出自约翰·济慈的同名长诗《Hyperion》。这是一部著名的太空歌剧经典、一部最浩瀚壮美的星际史诗,充满着真实可信、面临艰难道德抉择的故事人物(BY《纽约时报》):末日将临,宇宙中烽烟四起,七位一同前往海伯利安(Hyperion)星上的光阴冢(Time tombs)的朝圣者,在路上分享彼此过去的故事。全书由六篇不同的故事组成,分别叙述了他们背后与伯劳鸟(Shrike)的联系,透露了地球七个世纪以来所发生的历史,并展露了伯劳鸟与人类未来的关系。作品用神似英国古典文学大师乔叟的坎特柏里故事集的铺陈手法,传颂亿万年的宇宙绝唱。 末日前夜,整个银河硝烟弥漫,七名朝圣者,踏上朝圣征途,他们要前往光阴冢,寻找他们生命中未解谜团的答案。他们的发现,也许会是人类得以解救的关键。 牧师——雷纳?霍伊特神父在年级尚幼时,笃信天主教,尽管教会随着历史和变革,业已日薄西山。然而现在,当他看到曾经受他敬仰的人在海伯利安上所受的苦难之后,心中的信仰摇摇欲坠。 士兵——费德曼?卡萨德上校,霸主军队中最有前途、最能干、最坚强的年轻军官。直到他意外来到海伯利安,霎时天翻地覆。 诗人——马丁?塞利纳斯提到伯劳鸟之时,眼睛中闪现出某些东西。饥渴。或者更多…… 学者——索尔?温特伯过着平静的生活,直到他的女儿来到海伯利安进行考古探险……伯劳鸟碰触到她,接着,她开始逆时间而行。 船长——恬静,随和,带着令人捉摸不透的自信,海特?马斯蒂恩深藏不露。 侦探——布劳恩?拉米亚来到海伯利安,为的是查出真凶——谁杀了受她保护的客户。 领事——他看上去平静缄默……一名完美的官员。或者,在他内心深处,是否深藏着什么不愿示人的痛楚?是否有什么无法道来的目的? [相关奖项] 雨果奖、星云奖双奖作品 第一部荣获雨果奖、轨迹奖、日本星云奖、日本雨果奖、法国宇宙奖,入围阿瑟克拉克奖、英伦科幻奖、科幻纪事奖,轨迹杂志票选1990年前史上十大科幻小说 第二部荣获轨迹奖、英伦科幻奖、科幻纪事奖,入围雨果奖、星云奖、阿瑟克拉克奖 1997年和2006年两次“最推荐100部科幻奇幻作品榜”均位列其中 《轨迹》杂志票选1990年前史上十大科幻小说,已售出电影版权 [相关热评] 我景仰丹?西蒙斯 ——恐怖小说大师斯蒂芬?金 “构思宏大,文笔雄健……不落窠臼,堪比伊萨克?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弗兰克?赫伯特的《沙丘》和吉恩?沃尔夫的《新日之书》等经典之作。” ——《纽约时报?书评》 “丹?西蒙斯用一支生花妙笔,描绘了700年之后的未来。小说见解独到,故事错综复杂,可以与伊萨克?阿西莫夫和詹姆斯?布利什的作品相匹敌,甚至是凌驾于它们之上。” ——《华盛顿邮报?图书世界》 “所有科幻小说中,此是必读之物。” ——《书单》 “过去几年出版的最出色的科幻小说之一。” ——《科幻之眼》 “主题和风格的华丽结合。” ——《丹佛邮报》 “科幻小说能做什么,这两本书给出了一个很好的文学范例;此作者的这些书,毋庸置疑的将会影响一个文学类型,而此类型经常将自己狭限在粗劣文学的范畴内。” ——《圣彼得堡时报》 “《海伯利安》(包括《海伯利安的陨落》)是代表最尖端水平的科幻小说……我觉得这部作品将会成为准绳,未来作品都会拿这部作品作比较,就好比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和勒古因的《黑暗的左手》在彼时以同样方式树立了新标准一样。一言以蔽之,这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 ——《伊萨克?阿西莫夫科幻小说杂志》 “西蒙斯以精湛之技挖掘了科幻的潜能。” ——《轨迹》 “这部小说,作为文笔最优美的科幻小说之一,模仿了《坎特伯雷故事集》,构画了一个遥远未来的宇宙,一个名为海伯利安的星球,那正是以约翰?济慈的诗命名的。” ——《落基山新闻报》
One dimensional man: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作者: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著;刘继译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简介:本书内容包括:单向度的社会、单向度的思想、进行替代性选择的机会等三部分。 本书除导言外包括“单向度社会”、“单向度的思想”和“进行替代性选择的机会”三部分。作者通过对政治、生活、思想、文化、语言等领域的分析、批判,指出发达工业社会是如何成功地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使这个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而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这种人丧失了自由和创造力,不再想像或追求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本书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了较为深刻的揭露和探索,但暴露出其社会批判理论的乌托邦性质。本书对研究兰克福学派和马尔库塞理论的发展,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2012
简介:本书共有六十七章,讲述了生物的起源以及人类成长史上所经历的磨难与成功,论述了从地球的形成、生物和人类的起源直到现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横跨五大洲的世界历史。从空间中的世界到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重建,无不渗露出宇宙之旷达,生命之奇特,以及人类无穷无尽的欲望。本书关注的是人类文化的遗产,所传达出的是对人类命运的关怀,透露出作者对欧洲和世界命运的思索。
The postmodern turn:essays in postmodern theory and culture
出版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公司,1993
简介: 在「後現代(主義)」一詞已充斥於文化論述,乃至於日常語言的今天,威斯康辛大學密爾瓦基校區的伊哈布.哈山教授收錄於本書的十篇論文,彷彿一次次精采的批判性演出,構成了理解文學後現代主義的最佳參考依據。作為後現代主義最早的年代紀學者之一,哈山對這個術語的得以逐漸被接受,貢獻可能超過任何其他批評家。本書鋪陳作者本人對後現代主義的思維發展歷程,探索這個概念所經受的各種磨難與考驗,並檢討有關的論辯,足以讓讀者領受一個文化進行自我了解時深沈、豐沛的一面。 《後現代的轉向》 導讀 在晚近有關後現代的理論探討中,哈山所佔的位置並不十分重要。主要的原因是即使到了八0年代,哈山還是堅守某種文學本位的「沈默批評」的立場,與主要辯論中各種學科知識與政治立場相互激盪的鬧熱氣氛顯得格格不入。這並不是說,哈山的討論毫無價值;相反的,透過哈山的呈現,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值得檢討的問題,而這些問題與某些後現代理論的基本觀念仍然是息息相關的。 我必須先就「沈默批評」的意義,稍作說明。沈默批評是哈山所謂沈默文學的延伸。在哈山的心目中,西方文學的主流是「從形式走向反形式」,而形式的作用是透過作品語言與藝術規格的操演來保證意義的傳達,所以走向反形式也就是走向沈默,切斷語言和現實之間的關係,把文學變成一種高度自律的,內顯(imminant)於文字當中的半神祕經驗。同樣的,哈山心目中的理想批評也保有高度自律的傳統承遞(從文藝復興到浪漫主義到現代主義到後現代主義),它的發展動力來自某種內在的規律。所以晚期的哈山特別強調批評或文化理論必須抗拒來自非文學部門的解釋規範,避免沾染特定的政治立場,不向任何意識形態靠攏。這個立場代表了人文主義傳統的一種典型。可以想見,在一般文學研究者當中,哈出的說法還是具有相當代表性的。 如果我對哈山立場的解釋可以成立,這裡面至少牽涉到兩個問題。其一,文學研究的發展有其內在的規律,這種觀念代表的是學科分立的韋伯式現代理性,豈不是大大違背了哈山自己強調的反目的,反連續,反主體的後現代精神?其二,哈山並不否認後現代是產生於「西方社會和它的文學」中的現象,甚至有文學思潮是後現代社會「一個獨特的、精英的方面」的說法。那麼語言文字顯然並不僅是以沈默、憤怒、抗議來面對(規格化的)外在環境,而是在一定的層面上準確的反映,或者說模擬了其他社會、文化部門的現實。 這兩個問題其實可以歸結為文學的兩種發展方向的衝突:文學應該秉持抗議精神,嚴守內在的規律,走向社會狀況的對立面,還是接受下層結構的決定,撤除界限,回歸現實的同質面?或者說,文學應該成為社會的監察院,還是社會的存查院?第一種方向本於求真實、求自主等原則,當然具有強烈的現代精神,第二種方向則似乎具有後現代平淺化、反等級、反創造的意味。這裡並不是說,哈山的講法有矛盾:後現代是現代的延伸或修正,或者後現代與現代可以並存,或者兩者皆是,本來就是哈山一再強調的基本立場。我也不想引用辯證關係、相對自律之類的說法,來為兩種傾向強作連繫。另外,這也不是語言或翻譯意思不準確所造成的問題,雖然我們必須記得,postmodernism具有從後現代主義、後現代現象到後現代症等等的多重涵義。這裡想指出的重點是:哈山以一種很特殊的方式「抹除」了這兩種方向的衝突。不是化解,也不是調和,甚至不必動用互補、延伸等觀念;在不知不覺中,我們忽然發現,監察院其實就是存查院。 或許我們可以對哈山的思考路線作一個外繫式的說明(雖然這不合強調內顯的後現代精神)。在一個理想的社會裡,真偽、善惡是十分確定的,並不需要有一個專責批判或異議的部門存在。而當這個涵括社會整體的確定性喪失的時候,文學以及其他現代學科就從這個整體獨立出來,接收了確定意義的責任。也就是說整體所失去的確定性,是以窄化、深化的方式,由部分收回來。哈山顯然認為這個分裂、離散的過程一旦開始,就很難終止。所謂一切整體都是專制、極權,便是說整體的意義是用確定的規矩來掩蓋不能確定的真實。社會整體的價值既然難定,文學整體、作品整體、作家整體等等何能獨善其身?任何由整體獨立出來的次整體遲早都會被原來的整體同質化而落入被懷疑的命運。於是不確定的範圍愈來愈大,提供確定功能的對立面則愈來愈緊縮。可以想見,這個過程發展到最後,扮演對立角色的自律部門終會完全失去存在空間:不斷懷疑的結果便是懷疑者本身也受到懷疑而消失。對立批判的精神(「創造意義的欲望」)不斷從整體離散出來,終至無所依歸,只能像無廟可棲的散仙那樣,一切存查而轉入意義的嬉遊。這就是所謂「逍遙離散」(ludic dispersal)了。 哈山顯然不滿意這種歷史告終、意義也告終的結局,所以在晚期改採實用主義的多元論,要在局部實況中重建確定性,但同時保存由各種實況的差異所構成的不確定性。這等於是說,後現代精神在到達否定一切的終極困境之後,必須回頭轉向,重尋確定的意義。這裡的問題是,意義分裂、離散的過程是由現代精神的內在規律所推動的,它一旦逆轉而重走聯結、聚合的老路,這內在的動力是不會因為理論家的主觀意志而停留在某一「局部」層次的。從哪裡喪失的確定性,就會從哪裡找回來:既然某些局部實況可以有整體的意義,那麼為什麼不能把社會整體也當成是一種實況,賦與它確定的意義?理論操演固然可以就實況的層級作種種(經驗論的)分辨,但只要理論本身是自律部門的一部分,它所內含的可能性終究會按孔恩式(Kuhnian)科學典範的發展規律,獲得實現。這等於是把後現代反統合、反整體的漂遊觀又重新還原為超然客觀的現代精神。有朝一日,我們又會發現,原來存查院也可以變回監察院。 這種以後現代面目出現的現代精神,在實用主義多元論的立場中已經可以看出端倪。表面上看,實用主義既保全了後現代尊重局部實況的精神,又可避免陷入虛無空洞的反現代的嬉遊,似乎是後現代理論的合理歸宿。其實,實用主義常被認為是一種過度保守的主張,並不是沒有理由的。多元論的前提是:此狀況的真實與彼狀況的真實不同,但可以並存(一個典型的說法是:「我不同意你的說法,可是我支持你說話的權利」);然而多元論既然是以理論的形式出現,這個前提往往會一般化而變成這樣:此狀況的真實與彼狀況的真實可以並存,但不能相同(「我支持你說話的權利,可是不管你怎麼說,我都不贊成你的說法」)。也就是說,多元論者所占的是一個高高在上的地位;他可以決定各種實況的界限,判斷由其中確定出來的意義是否合法,然而他自己卻是不受任何實況限制的超然旁觀者(只有他才能決定別人有沒有說話的權利)。在哈山討論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時候,這個傾向表現得特別清楚: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是在過去的實況中產生出來的,所以不能把自己當成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其實,這是非常形式化的規矩;真正值得考慮的應該是:過去的實況與當前的實況有沒有一些相通的因素,可以為後來者借鏡?馬克思主義者顯然是認為有。那麼反對馬克思主義者就必須針對事實來討論各種實況之間可不可以相通的問題,而不是跳出實況,斷言所有追求普遍性的理論都是意識形態。這裡哈山的表現多少會令人懷疑,所謂實用主義的立場是否就是要切斷實況與實況之間的連繫,以多元存查的方式達成社會體制的超穩定化? 透過離散與聚合的循環變形,哈山抹除了現代與後現代的差別。然而,如果實用主義就是最後的結果,我們也許應該重新考慮,這套解釋是否有什麼遺漏。我的看法是,在現代精神裡面,文學或其他文化部門具有批判、理議的功能,應該不是問題。問題在:批判而必形成批判部門(監察而必成立監察院),就開啟了批判走向反批判(監察走向存查)的路程。不管是確定性或不確定性,都不可能只存在於某一特定的部門,而是散布在社會整體的各個部分,接受各種現實狀況的制約與決定。文化部門的獨立是現代學術發展過程中的事實,但這並不是說,獨立的結果就必然會產生一個形態確定,負有固定任務,與現實條件完全脫離互動的自律體。哈山既然認為西方文學有一主流,必然是要就文學的內在規律來發展他的思考。結果,社會整體並沒有向文學所提出的對立面理想演變,反而是文學本身(或者說哈山的敘述)不得不按內在規律走入自己的反面。 如果說反本質是後現代的一個特徵的話,那麼這種部門獨立,角色獨立的思考格局恰恰是陷入了文學本質的舊套。但是我們也常聽到 (不限於哈山),後現代就是反這個,反那個,或者是後現代具有三點特徵、五點特徵等等的概括性說法,這一類的「定格畫面」難道不也是有關後現代本質(或內在規律)的,非常確定的描述嗎?這些都是因為形式概括而造成意義必須走入反面的例子。後現代主義者當然也可以有「有時反有時不反,才是真反」之類的詭辯,但是要真正解決問題,恐怕由內顯走向外繫,根據實況引入形式、規律之外的決定因素,才會有更具建設性,更實用的結果吧。 第一章 沉默的文學 文學中前衛的觀念在今天看來似乎已經顯出了不合時宜的天真。我們看慣了危機,也失掉了頗為自信的方向感。何去何從?文學掉過頭來反對自己,渴望沉默,留給我們的只是說明憤怒和啟示錄式(outrage and apocalypse)的種種令人不安的通告。如果說我們這個時代還有某種前衛的話,那就很可能是想要通過自殺去發現什麼的傾向。這樣,反文學(anti-literature)這一術語就像反物質(anti-matter)一樣成了一種象徵。它不僅象徵了形式的顛倒,而且也象徵了意志和能量的顛倒。那麼,對所有那些以文字為業的人,未來意味著什麼呢?難道竟是無休無止的漂泊和災難嗎? 儘管我不相信語言能夠窮盡精神的各種可能性,然而我卻要承認,災難的來去自有其狡詐的規律。神祕家們總是說,黃泉之路就是出路,事物的終結必將引出新的開端。正如我們今天所說,負面的超越(negative transcendence)也是一種形式的超越。因此文學中的沉默未必預示著精神的死亡。 這裏要談的新文學的要點顯然與過去的文學不同,不管它究竟 「新」在哪裏,我們都無法用過去衡量「前衛」文學的社會標準、歷史標準和審美標準來衡量它。新文學中有一種逃避或者無視傳統的力量,這種力量相當激烈,它摧毀了文學之樹的根基,引出了一種隱喻意義上的巨大沉默。這種力量還沿著它的主幹向上,直達枝葉,綻放出一簇音調混亂嘈雜的花朵。在這許多雜亂的音調中最響亮的是憤怒的呼喊和啟示錄式的調子。亨利.米勒和撒繆爾.貝克特就頑強地唱著這種調子,傳達著沉默的信息。他們的聲調空洞無謂,使用的手法也不再是奇特的比喻。他們是當代想像力的一面鏡子,反映了這一時代的那些特別的公設。用一句老話說,他們是當代前衛派的大師。 要談米勒和貝克特需要首先對沉默的成分做些澄清。我想先談談「憤怒」。「難道藝術總是憤怒,或者從本質上說必然是憤怒嗎?」勞倫斯.達雷爾(Laurence Durrell)有一次想到米勒時這樣問道。我們可以同意這樣的說法,即藝術包含著危險甚至顛覆的成分,而無須說一切藝術都是憤怒。現代文學中一個特殊的類型似乎證實了達雷爾的觀點。它處理的人生經驗使他驚愕,那是一種具有形上反叛意義的經驗:如果太陽侮辱了亞哈(Ahab),他也會反擊太陽;伊萬.卡拉馬佐夫(Ivan Karamazov)把生命之券歸還給上帝。這既是一種形上的反叛,也是一種形上的投降,即對虛無的渴望。正如阿爾伯特.卡繆(Albert Camus)講的那樣,心靈的呼喊被它本身的反叛耗盡了。在憤怒中人的本質存在(the very being of man)受到考驗,隨即產生了一種暴力的辯證法,魔鬼般的行動和魔鬼般的反動被壓縮在一個最終變成零的可怕的統一體中。 這種和新文學緊密相關的暴力顯然是一種特殊的類型,它預設了達豪(Dachau)和廣島(Hiroshime),當然不限於這兩個地方。認為這種暴力沒有意義和價值的想法是荒唐的。這種暴力的作用是把人變成物,在它的作用下,人的變形是逐級而降的,往往最終變成貝克特筆下的蟲、巴羅斯(William Burroughs)筆下的蟲人和知覺的滲出物。這種暴力不是時間的,而是空間的,不是歷史的,而是存有論的。它是一幅風景畫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弗里德利克.霍夫曼(Frederick J. Hoffmann)在《致命的不》(The Mortal No)中說,這一暴力的景象說明「無論施暴者還是受害者都已沒有人的味道,二者都是這幅風景畫的部分」。這一把暴力比做風景畫或內在特質的隱喻是我將要討論的暴力定義的一個極端。在百老匯改編上演的米勒作品《北回歸線》和《南回歸線》(the Tropic books)中,我們可以看出這幅暴力的風景畫是怎樣形成的。當暴力在貝克特的《終局》(End-game)或《怎麼會是這樣》(How It Is)空空蕩蕩的空間中最後變成死亡時,我們可以看出這種暴力給我們留下了什麼。在這些場景之上總是籠罩著一片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靜。 正是在這一點上,沉默的文學中能夠產生一種相反的動機、一個新的術語。既然憤怒是對虛無(void)的反應,為什麼不可以是對存在的召喚呢?如果這種說法能夠成立,憤怒就會引出相反的動機,那就是啟示。這種轉化明顯地表現在黑人文學中。在這類作品裏傳統的抗議轉變成現代的憤怒,而現代的憤怒又轉變成神的啟示。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為自己一本頗具威脅性的文集題了一個含有啟示錄意味的卷首語:「上帝給挪亞彩虹作標記:今後不再有洪水,可下一次將是烈火。」他還以《下一次是烈火》作為這本文集的標題。勞倫斯(D. H. Lawrence)認為,在那些遭受壓迫的人心目中,含有啟示錄意味的暴力正是對敵人應有的懲罰,甚至千年至福王國在他們看來也是權力而不是愛。就最近其他的文學類型而言,在啟示錄式的隱喻之後往往表現出更為複雜的情緒,隱含著某種近乎全盤否定西方歷史和文明,甚至全盤否定人的本質特徵和人為萬物尺度的傾向。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說:「我要成為一架機器。」不論這是否在開玩笑,他畢竟替貝克特筆下那些肢體殘缺的人、米勒筆下那些貪淫好色的人、巴羅斯筆下那些癮君子說出了他們要說的話。的確,對西方本身的極度厭惡比對其歷史和文明的否定更深刻地動搖著它的基礎。當這股極度厭惡的情緒在狂歡鬧飲式的毀滅中找不到圓滿的歸宿時,就很可能轉向佛教禪宗、帕塔費西學(Pataphysics)或群居雜交。 對自我的極端厭惡是現代啟示錄中介於毀滅衝動和幻想衝動之間的中間環節,也是再生的準備。所以勞倫斯相信,「只要我們和太陽在一起,一切都會慢慢地發生的。」無論太陽多麼遙遠,畢竟在我們的視野之內。惠特曼(Walt Whitman)在某種意義上對我們的心情更有預見性,指出千年至福王國的完滿不在未來,恰恰在永恆的現在: 也沒有比現在更多的青年或老年, 將來也不會有比現在更多的圓滿。 神的啟示就是現在!這個術語(apocalypse)恢復了它的本意,從字面上講,就是向人們揭示祕密和真理,讓幻象穿透一時的迷惘,直達光的中心。用現代的話說,就是一種非道德的唯信仰(antinomian belief),這種信仰有時可稱作意識的改變(alteration of consciousness),我們可以在阿卜特(Alpert)和李爾瑞(Leary)以迷幻劑產生刺激的實驗中,在金斯堡(Allen Ginsberg)的詩歌中、在梅勒(Norman Mailer)對性高潮的賴希式考察中、在諾曼.奧.布朗(Norman O. Brown)的心理—神祕啟示作品中看到這種意識的改變。意識的改變是梅勒畢生的願望,他曾在自己那些啟示錄式的長篇大論中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意識的改變也是貝克特滑稽模仿的目的,從他作品中那些笛卡爾式的獨白中很容易看出這一點。他們倆人的作品都呈現出無言之美的對立狀態。可見啟示並不存在於薩滿教式的迷狂或精靈附身式的恍惚中。正如萊斯利.費德勒(Leslie Fiedler)在《等待終結》(Waiting for the End)中所說:「我們無須開一槍,也無須建構一個三段論式的邏輯體系,只須改變自己的意識就可以看到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而且改變的方式輕而易舉,……」這是一個革命的夢想,旨在結束一切革命或者說一切夢想。 這樣,憤怒和啟示錄就為當代的想像提供了鏡子的形象,這些形象包含了我們經驗中生機勃勃和危機重重的部分,它們正是米勒和貝克特反映截然相反的兩個世界時採用的形象。貝克特給我們展示了一個了無生趣的世界,除非發生巨大的變化不能使這個世界復甦。在這樣的世界裏我們處於一種幾乎沒有憤怒的狀態。米勒給我們展示了一個混亂迷狂的世界,這個世界處於不斷轉變的邊緣上。在這樣的世界裏我們成了啟示錄熱的見證人。這兩個世界的共同點是都有不同程度的沉默,因為人在恐懼和狂喜的狀態下是講不出話的。 如果說憤怒和啟示錄的極端反應能夠說明新文學的總體面貌,那麼另外一些觀念則有助於說明沉默是新文學的核心。這些觀念中最重要的也許是「荒誕的創造」(absurd creation),這一觀念迫使作者反對甚至蔑視自己的活動。卡繆說:「創造或不創造都不能改變什麼,荒誕的創造者並不獎賞自己的作品,很可能始終拒絕承認它。」這樣,想像力就丟棄了古老的權威,不是在被詛咒詩人的浪漫遐想中,而是在那些把空白頁裝訂成冊的無詞作家的嘲弄中找到了自己的極致。 當作家屈尊把言詞寫在紙上時,他便傾向於把反文學看作單純的行動(pure action)或者無用的遊戲(futile play)。我們知道,藝術是行動的觀點在讓—保爾.沙特(Jean-Paul Sartre)的《什麼是文學?》(What Is Literature?)中獲得了明確的表述。沙特指出,講話就是行動(To speak is to act),我們所命名的每一樣事物都喪失了自身的天真,成為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的一部分。倘若說藝術具有價值,那是因為藝術公開宣稱自己是一種大眾的需求。卡繆(則在《西西弗斯的神話》[The Myth of Sisyphus]中)頌揚理解生命的知識(savoir-vivre),把它置於獲得行動的能力(savoir-faire)之上。可是他們的這些觀點在帕洛克(Jackson Pollock)的行動繪畫(action paintings)中受到了奇特的挑戰。帕洛克不把藝術看作大眾的需要,而是把它看作創造的過程。按照他的看法,這個過程即便不完全是隱私的,也是個性化的。它的價值對它的創造者比接受者更可貴。米勒的觀點與此意外地相似,他認為寫作就是寫自傳,寫自傳就是治療,也就是對自我採取行動的一種方式。他說,「我們應該檢查自己的日記,這樣做不是為了尋找真實,而是把它看作盡力擺脫對真實執迷不悟的一種表達方式。」這樣做的權利自然屬於記日記的人,但當行動導向外界時也屬於詩人。米勒說:「我不認為那些寫詩(不論是有韻體還是無韻體)的人是詩人,我把那些能夠深刻地改變世界的人稱作詩人。」 可是對貝克特來說,寫作就成了荒唐的遊戲。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的全部作品都可以看作是對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那個著名論點的滑稽模仿。維特根斯坦這一論點說,語言是一套遊戲,近於原始部落的算術。貝克特的模仿充滿了自怨自哀,顯示了一種反文學的總趨勢。休.克納(Hugh Kenner)對這個問題有精彩的論述,他說:「當今佔主導地位的智性類比不是從生物學和心理學(儘管這是我們正在研究的兩門學科)做出的,而是從一般的數字理論(general number theory)做出的。」這樣,處於封閉領域的藝術就變成了一套排列組合的荒唐遊戲,好像馬洛伊(Molloy)在海邊啜石頭那樣。格奧爾格.施泰納(George Steiner)把這種情形稱作「從語言的撤退」,這樣的遊戲把語言簡縮成了單純的比率(pure ratio)。 十分有趣的是,文學作為遊戲和行動的觀念還產生在另一種富有沉默意味的形式中,它就是文學上的猥褻(literary obscenity)。猥褻這個術語聲名不佳,除了法庭斷案之外很難界定。這裏我用它主要是指那些把猥褻和抗議結合起來的作品。我們不難理解,在一個性遭到壓抑的文化中,抗議完全可能採取帶有猥褻意味的形式,因此,展示這種動機的文學就是一種反叛文學。然而,猥褻是極端簡縮的,它的語言、場所和慣技非常有限。當它背後的怒火冷卻下來之後,猥褻便變成了排列組合的遊戲,可仰仗的詞語寥寥無幾,而行動則更是少得可憐。顯然,這正是我們從薩德(Marquis Sade)的作品獲得的雙重印象:一方面,他的抗議異常強烈,另一方面,他的遊戲竟最終變得麻木。今天許多人都把他看作前衛派的第一人。他的作品表現出奇特的寧靜,作品中的猥褻和不斷出現的暴力窒息了語言。他把色情美學(pornoaesthetics)遺贈給了文學,也把它傳給了海勒和巴羅斯之輩,使他們能夠對性暴力進行滑稽模仿。不過,梅勒筆下的性英雄行為看來仍然太天真,尚難認識到自我滑稽模仿的潛力,而貝克特則對大便排泄的迷戀進行了充分的自我滑稽模仿,同時排斥一切形式的愛。在猥褻中和在滑稽模仿的遊戲中一樣,起制約作用的是反語言(antilan-guage)。梅勒和貝克特在這方面形成鮮明對比,暗示了色情中生殖器和肛門兩種不同的方式。 沉默的文學還以另一種方式成功地否定了文學以時間為特徵的功能,那就是渴求一種不可能實現的具體性(impossible concreteness)。這種新的傾向產生在施托克豪森(Karlheinz Stockhausen)的具體音樂(Musique concrete)、從杜象(Marcel Duchamp)到勞申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的雜物拼湊畫(collage)、施維特斯(Kurt Schwitters)的環境雕塑(environmental sculpture),以及在施維特斯和阿波里奈爾(Guillaume Appollinaire)影響下形成的具體詩(concrete poetry)中。這種具體詩是語言和視覺兩種效果雜交的形式,主要依靠字母形成圖畫。此外,在杜魯門,卡波特(Truman Capote)的《凶殺》(In Cold Blood)中也可以感覺到那種不甚分明地渴求具體性的傾向。卡波特摒棄想像的魅力,自稱要絕對忠於事實,寫出了他所謂的第一部「非虛構小說」。在歐洲文學中,這種新寫實主義(neoliteralism)有時不是和報導文學聯繫在一起,而是和埃德蒙.胡塞爾(Edmund Husserl)的現象學聯繫在一起。胡塞爾曾對沙特和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這樣不同的人產生過重大影響。他的思想十分難懂,要想加以概括而又不嚴重歪曲它是幾乎不可能的。然而我們仍然可以說,他的哲學界定了主觀意識的一種純形式,這種意識形式既不是由部分構成,也永遠不會成為經驗的對象,而是通過一系列的「還原」(reductions)被隔離出來,它已經不再是包含著普通人事、感情和感覺的日常世界的一部分。我們通常接受為自我的東西必須置於「括號」中或者被懸置起來,作為一個經驗的統一體,經過最終「先驗的還原」產生純粹的意識。所以,粗略地說,自我是不可知的,或者像貝克特筆下的反英雄那樣,是不可命名的。 這一結論對小說究竟有什麼樣的影響呢?因果論、心理分析、象徵關係這些中產階級小說曾一度心安理得地遵循的原則現在開始瓦解了。貝克特的《馬洛伊》可能是用全新的觀念寫的第一部小說,當然,沙特的《惡心》(La Nausee)也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從洛根丁(Roquentin)身上我們看到一個對世間萬事萬物都極度冷漠的人,看到事物和語言之間完全脫了節,主觀和客觀之間也完全脫了節。後來,阿爾.羅勃—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出來,反對沙特的泛人類中心主義(pan-anthropcentrism),摒棄了沙特的人道主義,開創了新局面。羅勃—格里耶認為,如果人期望孤獨,拒絕和宇宙交流,如果人證明自己不是斯芬克斯(Sphinx)那個永久之謎的答案,那麼他的命運就既不是悲劇的,也不是荒誕的。他快活地爭辯道:「物就是物,人也只是人。所以我們拒絕和客體的一切同謀關係……也就是說,我們必須拒絕一切預先安排好的思想。」按照這樣的觀點,小說家只能是拘泥於字面意思的人,只是給事物命名,或者遊戲於純粹的意象之間。法國薩格特(Nathalie Sarraute)、布托爾(Michel Butor)和羅勃—格里耶就是這樣的小說家,他們的反小說(antinovel)沒有人物、沒有情節、沒有隱喻和意義、沒有假裝的「內在性」(interiorness),就像新電影(the new cinema)一樣,旨在獲得默片的效果。哈洛德.羅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講的好像完全不是文學、視覺藝術:「法國所有的煉金術士(alchemists)追求的都是同一樣東西,即總是通過使語言沉默來獲得新的現實。」 新文學中的沉默還可以通過激進的反諷(radical irony)獲得。這種反諷指所有帶反諷意味的自我否定。克里特人宣稱所有的克里特人都是撒謊者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廷格里(Jean Tinguely)的機器是另一個例子,這種機器除自我毀滅之外別無用處。換言之,激進的反諷需要的不是一堆東西的雜湊拼貼,而是一片空白的畫布。它的現代淵源可以追溯到本世紀文學的一些主要人物,特別是卡夫卡(Franz Kafka)和托瑪斯.曼(Thomas Mann)。卡夫卡表述的是一種近乎空白和凍結的空間感,而托瑪斯.曼喜歡表達的是一種反諷的調子,這種調子能通過滑稽的自我模仿取消自己,他認為這才是藝術的唯一希望。埃里希.海勒(Erich Heller)說得好:「在《浮士德博士》(Doctor Faustus)中,藝術悲傷地為自己神祕的喪失而哀悼,而在《費利克斯.克魯爾》(Felix Krull)中,藝術則高興地向宇宙警察局報告了自身神祕的喪失。這種傾向還可以更早地溯源到德國浪漫派和法國象徵派那裏。近來,這種激進的反諷也大量出現在詭辯哲學中。海德格所謂的「湮滅的神祕」(mystery of oblivion)的思想、勃朗肖(Maurice Blanchot)關於文學是一種「遺忘」(forgetfulness)形式的觀點都說明反諷在理論上獲得了進展。說得具體一點,梅勒的《一場美國夢》(An American Dream)用坦率而諧謔模仿的手法把小說變成了通俗藝術,事實上否定了小說這種體裁。納塔莉.薩格特的《黃金果》(The Golden Fruits)是一本關於小說的小說,小說中的小說也題為《黃金果》在閱讀的過程中這部小說中的小說漸漸湮滅,從而取消了自己。這種反身的技巧在貝克特的作品中可以說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甚至達到了極致。他最近的一部小說《怎麼會是這樣》(How It Is)實際上講的是「怎麼會不是這樣」(How It Wasn''''''''t)。這樣的手法並非瑣屑無用,因為藝術利用藝術來否定自己這種看似矛盾的做法植根於人在意識中將自身既看作主體又看作客體的能力。在人的心靈中有一個阿基米德點,當世界變得忍無可忍時,心靈就會上升到涅槃的境界,或下沉到瘋狂的狀態,或者採用激進的反諷來說明藝術處於窮途末路的情形。因此,在貝克特那裏,文學起勁地毀滅自己;在米勒那裏,文學變幻無常地假裝具有生命。更使人難於辨認的是,激進的反諷往往用假象掩飾對藝術的進攻。通過反諷藝術家向繆斯表示最後的忠誠,同時也褻瀆了她。這種既愛又恨的矛盾情感在貝克特相米勒的作品中隨處可見。 最後,文學還力圖通過機會和即興之作獲得沉默的特徵。在這種情況下,不確定性是主要原則。這樣的文學拒絕一切秩序(不論是強加於人的還是人自願接受的),因此也排斥目的性。所以它的形式是無目的的,它的世界是永恆的現在。讀這類作品使我們重新感到原始的質樸和天真,一切錯誤和修正都無關緊要,不再存在。作品中的一切都毫無目的,隨遇而安,彷彿禪宗寺院裏的踏腳石那樣隨處拋置,無所用心。約翰.凱奇(John Cage)的作品證實了我們的這一印象。凱奇既是作曲家也是詩人,他比薩蒂(Erik Satie)更讓公眾震驚。他的作品有極大的隨意性,給人以神聖感。他在《沉默》(Silence)一書中說:「我們的目的是肯定現在這種生活,既不想從混亂中引出秩序,也不想在創造中實現改善,只是要清醒地意識到我們現在過這樣的生活,一旦人們的心靈和欲望離開了它,讓它按自己的意願行動,它就會變得非常美好。」在米勒的作品中、金斯堡的詩歌中、克魯亞克(Jack Kerouac)的小說中、塞林奈(J. D. Salinger)後期的短篇之作中都可以看出這種無目的性和隨意性。但與凱奇不同的是,這些作家在把自己的精神生活輸入文學實踐時卻顯出了膚淺。例如,米勒雖然很喜歡「道」和彌拉惹巴(Milarepa),卻總想做出一副喋喋不休地敘事的姿態。他作品中那些看來隨意的拼湊雖然不是精心設計出來的,卻也是經過處理的。多年以前,達達主義者和超現實主義者幾乎要瓦解一切文學形式,可他們缺乏良好的精神素質。我們今天的一些隨意性作家像雷蒙.奎諾(Raymond Queneau)、馬克.薩波塔(Marc Saporta)和威廉.巴羅斯之輩也是如此。在《無數的詩》(Cent Mille Milliards de Poems)中,奎諾建造了一架「詩歌機器」,十頁十四行詩相互搭接,每一首的每一句都可以和其餘的詩行形成種種組合,這樣,要想「讀」完這些詩就得用兩億年。在《第一號》(Number 1)中,薩波塔要讀者每次讀他這些小說時以洗牌的方式創造出自己的作品來。這種「洗牌式小說」(shuffle novel)顯然是他的一種策略,它提示在文學經驗中機會是一個合法的成分。巴羅斯相信講話就是撒謊,因此力圖通過「布利昂.吉辛的剪碎法」(The Cut Up Method of Brion Gysin)來逃避虛假,這樣就自然回到了達達主義者特利斯坦.查拉(Tristan Tzara)的滑稽伎倆上。巴羅斯解釋說: 方法是簡單的:從你自已的作品或者從活著的,已故的作家的任何作品中取出一頁左右的篇幅,可以是書面的也可以是口頭的,然後用剪刀或彈簧折刀將其隨心所欲地剪成小片,在反覆的觀察中把它們重新安排,寫出結果。 剪碎法的應用可以是無限的,可以不受時間的限制。古老的文字把你侷限在古老的框框裡。用剪刀剪出你自己的路子來。可以剪紙剪電影剪磁帶。想剪什麼就剪什麼,直至剪碎城市。 達達主義的雜湊拼貼、佛教禪宗、或者諾伊曼(John von Neumann)的遊戲理論可以同樣有效地使人們擺脫傳統的語言文字習慣。巴羅斯和貝克特有一些共同之處,他們都使用了減數機(subtracting machine)起落無常,極不流暢的節律。這種機器的目的無非是給語言動手術,從而減掉一切意義。 顯而易見,處在反文學核心的沉默是大聲喧嘩的、多種多樣的。不論它來自憤怒還是來自啟示,不論它出於單純行動還是單純遊戲的文學觀念,不論它表現為具體物品、還是空白頁或者雜亂拼湊,最終都是無關緊要的。我們認為重要的是這樣一點,沉默是文學對自己採取的一種新態度,是說明這種新態度的一個隱喻。這種新態度對文學傳統論述方式的特別權力和優越性提出疑問,對現代文明的許多公設發出挑戰。 從總體上看,這種新態度並沒有對英美批評家產生足夠的影響,這一點頗使人迷憫。英國人看問題明智、務實,而美國人則長期陷在那個費力的形式主義中,這也許可以部分地解釋他們對這種新態度冷漠的原因。此外,在英美兩國,反文學的思潮往往使那些人文主義思想相當牢固的批評家們不滿,也使那些篤信某種現實主義觀念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反感。 法國批評家很可能也像別國的批評家那樣盲目教條或狹隘偏執,但對反文學的思潮卻表現出例外的熱情。沙特在《什麼是文學?》中用較多的篇幅討論了本世紀初達達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的語言危機。十年之後,他在為薩格特的《無名氏畫像》所寫的導言中說:「就其生動性和全部否定性而言,這部作品可以說是一部反小說。」這樣就為本世紀中期的批評詞彙庫中增添了一個新術語(anti-roman)。莫里斯.勃朗肖在《未來的書》(Le Livre a venir)中把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看作沉默傳統中的始作俑者,說他「熱衷於寫反寫作(contre l''''''''ecriture)的東西」。他認為文學正在接近「沒有話語的時代」(l''''''''ere sans parole),像貝克特和米勒的某些作品就只能理解為一系列連續不斷的聲音。所以按照勃朗肖的看法,文學正在接近自己的本質,那就是消失。羅蘭.巴爾特也持有類似的觀點,他的《寫作的零度》(Le Degre zero de l''''''''ecriture)主題就是缺失(absence)。他認為「現代性始於對不可能存在的文學(litterature impossible)的探索。」,而探索的結果便是奧菲斯的夢:「出現一個沒有文學的作者」(unecrivain sans litterature)。克洛德.莫里亞克(Claude Mauriac)似乎是第一個把米勒和貝克特放到一起來討論的批評家,他在《新文學》(The New Literature)中說:「經過韓波(Arthur Rimbaud)的沉默、馬拉美(Stephane Mallarme)的空白詩頁、阿爾托(Antonin Artaud)無言的呼喊之後,非文學(aliterature)終於消解在喬伊斯(James Joyce)的頭韻中。……而對貝克特來說,所有的詞說的都是同一個意思。」可見,儘管法國人頭腦也很清醒,但卻並沒有對文學的沉默提出責難。 但我還是懷疑僅有思想的清晰是否足以實現批評的偉大目標。我們越來越感到批評應該在澄清和解釋之外做更多的工作,應該具有感官和精神的智慧。我們要求批評像文學一樣使它自身處於危險中,從而證實我們的處境。我們甚至希望它能承受啟示的重任。這一希望引導我們提出這樣的假想,它應該成為啟示災變的工具,從而使我們產生應有的警覺。至少它應該對啟示錄的隱喻抱有同情心,以便考驗反文學的直覺。萊斯利.費德勒的《新的變異》是美國批評中討論批評重任的一篇珍文,此文說明他能充分理解文學想像和沉默、猥褻、瘋狂、甚至近於神祕恍惚的後性狀態(post-sexual state)結合在一起時產生的複雜性。他懂得,對我們這個時代至關重要的是「這樣一種意識,文學首先孕育一個可能出現的未來,……然後以歡樂和可怕的預言裝備那個未來,這樣,就使我們所有的人為未來的生活做好準備。」 反文學可以導向未來,然而批評的心靈仍要求歷史的保證。沉默的文學會回憶起第一個歌手奧菲斯被肢解的情形嗎?會顛倒那個把文字轉變成血肉的聖經式奇跡嗎?難道人類在經過漫長的史前期之後必須屈從於一個無言的事嗎?完全相反,新文學可以是極端的,它的夢可以是啟示錄式的、憤怒的。它是為生活而生的,而生活,我們知道,有時要經受暴力和矛盾。 神話中有一種說法,說奧菲斯被酒神狄奧尼索斯(Dionysus)的狂友們(Machads)根據她的命令撕成了碎片。還有一種說法,說他是被她們在無法控制的嫉妒中殺死的,因為自從他的妻子歐律狄克(Eurydice)死後,他就不近女色而寧願與青年男子作伴,故而引起了那些狂友們的嫉恨。不管是哪一種說法,有一點是共同的:作為一個超常的創造者,他是酒神原則和日神精神衝突的犧牲品。前者以酒神的狂友們為代表,而後者則是他作為一個詩人崇拜的對象。奧菲斯被肢解之後,他的頭依舊在歌唱。在他的肢體被謬斯們埋葬的地方,夜鶯的歌比世上任何地方的歌都甜美。奧菲斯的神話可以成為某些時期藝術家的寓言。由於文明總是要對酒神精神加以壓制,因此酒神精神在一些時期往往威脅要進行凶猛的報復。這樣,在這個報復的過程中,精力就可能壓倒秩序,語言就可能變成狂嚎、母雞的叫聲和可怕的沉默。形式也就可能像可憐的奧菲斯那樣被無情地肢解。然而問題依然沒有解決,難道詩人的頭不是必然會像那狂暴的日子在色雷斯(Thrace)山中那樣被砍下以便繼續他的歌唱嗎?讓我把問題提得更直接些:難道生活不是必然會定期地壓制藝術以便保證人的健康和生存嗎?難道語言不是必然會渴望寧靜嗎? 文學史上不乏這樣的例證,早先就有過關於沉寂和解體的警告。羅伯特.馬丁.亞當斯(Robert martin Adams)在《不諧的旋律》(Strains of Discord)中恰當地找到了一種結構,認為它是時下反形式(antiform)的前身。他說:「開放的形式」(open form)是一種有意義的結構,它「包含一個主要的,不可解決的衝突,旨在展示這種不可解決性。……在它的左邊,一條不明確的、定量的線把它和無形式以及不確定性(反常的或一般的)分割開;在它的右邊,一條同樣不明確的,定量的線把它和雖然含有開放成分但卻仍是完好的封閉形式分割開。」從諾思羅普.弗萊(Northrop Frye)得到啟示的那些嚴肅的類型學家可能希望說明,正因為文學似乎是從神話模式發展到反諷模式的,所以文學形式似乎是從封閉發展到開放,然後再發展到反形式的。當我們把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伊底帕斯王》(Oedipus the King)和歐里庇得斯(Euripides)的《酒神的伴侶》(The Bacchae)對照閱讀時,便可以清楚地看出封閉形式和開放形式之間的差別。亞當斯的看法無疑是正確的。他認為《伊底帕斯王》力圖解決衝突,使觀眾產生一種局部寧靜的心態,但《酒神的伴侶》卻給觀眾留下了一種無法緩解的痛苦。作為一個封閉的形式,《伊底帕斯王》表達了一種保守的、宗教的世界觀和集體經驗,而作為一個開放的形式,《酒神的伴侶》卻表達了激進的、懷疑的世界觀和個人經驗。如果按照這一圖式大膽推論,我們不妨說,貝克特的《等待果陀》(Waiting for Godot)是一種反形式,暗含著一種反諷的、虛無主義的世界觀和一種完全隱私的經驗。 不過,我們不必拘泥於嚴格的類型學,這樣就可以看到,從《酒神的伴侶》到《等待果陀》之間,西方文學中有大量的作品表現出不斷增長的斷裂感和扭曲變形能力。僅以戲劇為例,我們就可以提出如下序列: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Hamlet)、歌德(Goethe)的《浮士德》(Faust)、畢希納(Buechner)的《沃伊采克》(Woyzeck)、梅特林克(Maetelinck)的《青鳥》(Blue Bird)、斯特林堡(Strindberg)的《夢劇》(A Dream Play)、加里(Alfred Jarry)的《于比王》(Ubu Roi)、皮蘭德婁(Luigi Pirandello)的《六個尋找作者的劇中人》(Six Characters in Search of an Author)、熱奈(Jean Genet)的《黑人》(The Blacks)、尤涅斯柯(Eugene Ionesco)的《殺人者》(The Killer)。看來戲劇形式似乎是從不可解決的矛盾走向象徵主義的逃避,然後從象徵主義的逃避走向超現實主義或表現主義的扭曲,最後從這種扭曲走向荒誕。儘管歷史上有過無可辯駁的例外,這種從形式向反形式的發展是西方的主流,它不僅表現在戲劇中,而且表現在藝術的整體中。 也許這樣講大抵是公正的:風格主義、浪漫主義和現代主義的先後出現標誌了形式運動的三個階段。風格主義是文藝復興的風格在形式上的消解,正如韋利.賽弗(Wylie Sypher)在《文藝復興風格的四個階段》(Four Stages of Renaissance Style)中所說,是張力和遲疑不決的一個標記。在風格主義藝術中「心理效果脫離了結構上的邏輯」。對我們一般所說的開放形式,賽弗的看法是: 在風格主義精心設計的技巧後面往往有一種個人的不安、一種激發出形式和詞藻的複雜心理。當我們考察繪畫、建築和詩歌裡風格主義結構中的張力時,我們就必然會清醒地意識到風格主義氣質中這種禍害或者說流沙。風格主義是技巧的實驗。它採用的技巧有:破壞比例和打亂均衡、Z字形和螺旋形的穿梭運動、旋渦般或狹巷般的空間、傾斜的或流動的視點、奇特的甚至是不正常的、只能產生近似而不是確定效果的透視法。 這不正是我們閱讀莎士比亞的後期劇作、詹姆斯一世時期的戲劇、玄學派(或譯形上派)詩歌時的感覺嗎?不正是我們觀賞提香(Titian)、丁托列托(Tintoretto)、埃爾.格列柯(El Greco)的繪畫時的感覺嗎? 浪漫主義者由於在朦朧的心緒中總是渴望著無限,因而進一步走向了不穩定的文學形式。《浮上德》正站在這一時期的門檻上,它混合著來自異教和基督教的雙重影響,在結構和主題兩方面變成了對生活中憤怒的矛盾的請求——只有歌德那光輝閃爍的天才方能把這樣的戲置於藝術的控制之下。這群陰暗的、浪漫主義的英雄們——浮士德、恩底米翁(Endymion)、阿拉斯托(Alastor)、唐璜(Don Juan)、于連.索黑爾(Julien Sorel)、曼弗雷德(Manfred)、阿克塞爾(Axel)——總是威脅要衝出束縛他們的樊籠,高傲地反對他們的創造者。自我、夢和無意識都在這一時期的文學中強烈地表現出來。諾瓦利斯(Neval)和奈瓦爾(Nerval)、霍夫曼(Hoffmann)和愛倫坡(Poe)、克萊斯特(Kleist)和畢希納、柯勒律治(Coleridge)和濟慈(Keats)把語言引入靈魂的暗夜之中,或者說培植出聲名不佳的浪漫主義反諷,從而在每一個表述中表達自己的反面。在另一些情況下浪漫主義堅持乖戾反常的性情,從而使自己失去了和諧和穩定的可能性。它探索薩德主義(性虐待狂)、惡魔主義(對惡魔的信仰)、神祕主義(cabalism)、對屍體的性迷戀(necrophilia)、吸血主義(vampirsm)和變狼狂症(lycanthropy),在毫無人性可言的情況下探索人的定義。難怪歌德認為浪漫主義是病態的形式,雨果(Victor Hugo)要把它看作古怪的東西。當然,我很清楚,這裏強調的是浪漫主義運動中黑暗的衝動,然而現代文學正是從這種衝動中獲得了動力,也正是這種衝動(倘若你願意,也可以稱這種衝動為巨痛)幫助摧毀了古典的文學形式。馬里奧.普拉茲(Mario Praz)在《浪漫主義的巨痛》(The Romantic Agony)中說:「浪漫主義的本質在於無法言表。.…‥浪漫主義把藝術家抬到了很高的地位,而藝術家卻不能賦予自己的夢一種物質形式——詩人面對著永久的空白詩頁欣喜若狂;音樂家傾聽著自己心靈中的音樂會而無意把它們變成樂譜。把具體的表述看作墮落和污染正是浪漫主義的態度。」可見,浪漫主義是沉默的源頭,是無言文學(aliterature without words)的源頭,或者更確切地說,是那種鄙視一切而只願意以最原始、最神祕的方式使用語言的文學的源頭。法國象徵主義者是現代運動的直接祖先,他們為現代運動的發展提供了典範。馬拉美的十四行詩設計了自我消滅的句法:韓波的《靈光篇》(Illuminations)打亂了語言的指示作用,意在使官感發生紊亂。勞特萊蒙(Lautreamont)的《馬爾多羅之歌》(Maldoror)為超現實主義開闢了道路。諾曼.奧.布朗說得好,在後期浪漫主義中,酒神重新進入了文學的意識。可以更加肯定的是,浪漫主義從語言的二重撤退是很明顯的。這撤退發生在馬拉美反諷的、自我取消的方式中,也發生在韓波不加區別的、超現實主義的方式中。在前一種情況下,語言渴望走向虛無,在後一種情況下,語言渴望囊括一切。前一個的關聯靠的是「數」,後一個的關聯靠的是「行動」。在前一種情況下,文學恰如勃朗肖所說正在走向自身的消失,也許馬拉美、卡夫卡和貝克特正屬於這一類型,在後一種情況下,文學恰如加斯東.巴歇拉(Gaston Bachelard)所說正在把自我重新組合成「熱烈的生活」(la vie ardente),也許韓波、勞特萊蒙、勞倫斯和米勒的部分正屬於這一類型。這兩種類型都在恐怖中找到了自己的源頭(所以兩者都包含在一位更早的前衛派作家薩德的思想裏,薩德懂得,憤怒和祈禱最接近文學的中心。),都最後走向沉默,切斷了語言和現實之間的一切關係。 在現代主義中,有組織的混亂(organized chaos)是制約一切的因素,正如葉慈(W. B. Yeats)在一首充滿啟示錄精神的詩中所說的那樣: 再也保不住中心, 世界上到處放縱著混亂無序, 血色暗淡的潮流奔突洶湧。 在有限的篇幅中要把我們這個世紀主要作品中表達的解體與重新組合的情形說得一清二楚是不可能的。喬伊斯曾是少數相信語言的作家之一,他在世時相信語言可以取代世界,在《芬尼根們的守靈》中卻以一個獨眼巨人的雙關語說明語言的終結。卡夫卡冷靜地確立了文學能夠具有的可怕的不確定性,說明了愛或恐怖最終將阻止語言發揮任何作用。未來主義以馬里內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為代表轉向另一個極端,文學成了一個想像的強盜,用鎢和斧劫掠城市。馬里內蒂假裝站在世紀的最前沿,向空氣發表演講。對達達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現在尚難做出全面評價。這兩個運動把生活和藝術中所有虔誠的東西徹底翻了個兒。它們仍是我們這個時代每一位作家必須面對的挑戰。因為雖然他們用我們通常不用的語言講話,但他們的目的仍然是為了生活和進步。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開始發表作品的作家們從總體上看不那麼雄心勃勃,可劉易斯(R. W. B. Lewis)還是看出了他們和前代作家之間的區別。他指出,馬侯(Andre Malraux),卡繆、葛拉姆.葛林(Graham Greene)這一代作家和那些把審美經驗看待至高無上的前代作家是完全不同的。他在《流浪的聖哲》(The Picaresque Saint)中說,這些年輕一代作家們的「主要經驗是發現作為一個作家的意義和活著的意義是什麼」。他的結論是「批評在審視這個世界時將會陷入更激進的思考中,思考生與死,思考人充滿渴望的、罪惡的本質。」至於我們當代的文學,弗蘭克.克默德(Frank Kermode)講得很中肯,他說比起早先的各式現代主義文學來,我們的文學更「分崩離析」,對奧菲斯的肢解表現出更大的熱情。文學走向反文學,並在此過程中創造了愈來愈瘋狂、愈來愈混亂的形式:新流浪漢小說(neopicaresque)、黑色滑稽作品(black burlesque)、怪誕作品(grotesque)、哥德式小說(gothic)、噩夢式的科幻小說(nightmarish science fiction),不一而足。最後,混雜在沉默中的便是表達憤怒和啟示的種種反形式。 歷史畢竟不能保證給人任何慰藉。安東尼.阿爾托在1938年出版了一本書,後來被譯作《戲劇及其替身》(The Theatre and Its Double)。他在這本書中說道:「如果我們這個時代還有一個該死的、地獄般的東西,那就是我們對形式高超的戲弄,這種戲弄比犧牲者被綁在火刑柱上焚燒,通過火焰傳達信號的把戲更令人痛恨。」奧菲斯不僅被肢解了,而且他的四肢被燒灼出白熱的光。歷史把我們帶到一個時刻的門檻上,給我們留下了一些棘手的問題。為什麼對這個文明的厭惡竟把文學逼到這樣一個極端的地步,使它陷入如此可怕的沉默呢? 在對我們的弊病作出全面的診斷之前,我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只能是間接的。也許線索仍舊在奧菲斯的神話中,在阿波羅(日神)和狄奧尼索斯(酒神)永無休止的鬥爭中。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對此提出了頗有說服力的見解。他在《文明及其不滿》(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中說明,社會建立在本能壓抑的基礎之上。對這一點我們一直有同感。但我們並未能時時意識到的是,我們生活中的每一個棄絕行動都為進一步的棄絕開創了道路。不僅如此,佛洛依德還爭辯說,文明最核心的動力「要求越來越多的壓抑」,這一過程所付的心理稅是多方面的,它的含義對文學至關重要。諾曼.奧.布朗在他那本頗具影響的著作《生對死的抗拒》(Life Against Death)中從佛洛依德結束的地方起步,提出一切崇高必然意味著對生命本能某種程度的否定。他的結論是:「崇高裏否定的力量鮮明地表現在(語言、科學、宗教和藝術中的)象徵和抽象不可分離的關係上。所謂抽象,正像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告訴我們的,是對經驗的生命器官也即一般生命體的否定。……」那麼,這裏的邏輯——我不知道它是否像布朗和佛洛依德表達的那樣無情——便是:壓抑產生文明,文明產生更多的壓抑,更多的壓抑產生抽象,抽象產生死亡。我們現在正在沿著一條純理智的道路前進,弗蘭采(Frenczi)把這種純理智看作一條瘋狂的原則。那麼,對人類還有任何拯救的辦法嗎?布朗提出了下面的想法: 人的本我(ego)必須面對酒神精神的現實,因此需要做大量自我改造的工作。尼采說得好,日神精神保存自我意識,而酒神精神毀滅自我意識。只要本我的結構是日神的,酒神體驗就只有以本我的解體為代價才能獲得。這種爭端也不可能以「綜合」日神式的本我和酒神式的本我加以解決,因此,已故的尼采竭力鼓吹酒神精神。……而建構酒神式的本我要做大量的工作。但有跡象表明,這些工作正在進行。假如我們能看清酒神式的女巫在現代歷史中釀成的種種變亂——薩德的性和希特勒的政治——我們也就能夠看清在浪漫主義的反動中酒神精神進入意識的情形。 對新佛洛依德主義者來說,問題是壓抑和抽象,解決這個問題的途徑是建立酒神式的本我。他們認為語言最終變成了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所謂的「身體的自然言語」(the natural speech of the body)。 這裏布朗對尼采的引述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尼采的確是我們這個時代理智史上的一位關鍵人物,他既是佛洛依德主義者的祖先,也是存在主義者的祖先。他還是這兩個運動之間的一個活的中介。他對西方文明的分析類似佛洛依德的,也許更有說服力。在他看來,現代世界罪惡的根源不僅來自對本能的壓抑,而且來自人有意識地追求意義的虛無主義。在對十九世紀做了深層的考察之後,他宣稱上帝已經死亡,同時提出現代人的危機是價值危機。「為什麼虛無主義會到來?」在《權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一書中他提出了這一問題,他的回答是,「因為虛無主義代表了我們最大的價值和理想的邏輯歸宿,在我們能夠看出這些『價值』究竟有什麼樣的價值之前,我們必須體驗虛無主義。在某些時候我們需要新的價值。」尼采像當代存在主義者一樣,認為根本的問題顯然是一個意義的問題。(但與大多數存在主義者不同,他是一個「烏托邦主義者」,認為通過超人豐富的生活經驗可以解決問題。)按照這樣的觀點,語言的理想變成了行動、姿勢,因為意義的創建不僅是一個語言過程,更是一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過程。有一位名叫尼古拉.貝加耶夫(Nikolai Berdyaev)的基督徒則對這個問題做了完全不同的解釋,「歷史內在的啟示表明:歷史上的上帝之國即意義是不能實現的。」但我們發現,這一問題依然是一個意義的問題。 世俗主義(secularism)、怠惰(acedia)、犯罪和虛無主義可能只是在深層失去意義的一些象徵。人正在失去自己內心的空間,就像赫伯特.馬庫色(Herbert Marcuse)在《單向度的人》(One Dimensional Man)中所說的那樣,人獨特的世界已被高度擠壓,難怪傳統上曾是人們在公私場合表情達意最大倉庫的語言也大為貶值。我們這個時代的預言家和烏托邦主義者也未能提出贖回語言價值的辦法。他們把崇高在未來的作用縮減到最小,也就把語言的作用縮減到最小。人類中將會出現的酒神或超人並不是那種健談的生物,因此,現代對語言表述的反叛說到底是對權威和抽象的反叛:日神主辦的文明已經變成了極權的文明,他給人類提供的賴以生存的工具已變成了以抽象為燃料的機器。因而無意義(meaninglessness)便是抽象的相關物。具有反諷意味的是,文學中對語言的反叛反映了但也滑稽地模仿了技術統治中從語言的撤退。這一點正是格奧爾格.施泰納在《從語言撤退》(The Retreat from the Word)中有所忽略之處。當然從其他方面說此文還是重要的。他說: 十七世紀之前,語言幾乎覆蓋了經驗和現實的所有領域,可今天它的範圍變得狹窄了,它不再是表述行動、思想和情感的主要工具。大片的意義和實踐領域屬於數學、符號邏輯、化學方程式或電子關係式等非語言範圍。還有一些意義和實踐的領域則屬於非具象藝術(non-objective art)、具體音樂等亞語言(sub-language)或反語言的範圍。語言的世界已經萎縮了。 然而,我們不能把我們的弊端歸咎於上帝的死亡或技術,那樣就過於簡單了。包括阿爾蒂采(Charles J. Altizer)、漢密爾頓(William Hamilton)、凡.布倫(Paul M. Van Buren)在內的更年輕的神學家把上帝的死亡看作文化肯定和精神肯定的一個挑戰性事件。一些搞技術的預言家像馬歇爾.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和巴克明斯特.富勒(Buckminst Fuller)等則從「地球村」(global village)看到了神奇的可能性,認為地球已經完全處在新科學和新技術的控制下。但即使麥克魯漢也認識到,在從印刷語言的視覺文化轉入電子技術的「總體」文化這一過渡時期中,我們必須面對可怕的危險。他在《古騰堡星系》(The Gutenberg Galaxy)中這樣說:「恐怖是任何口語社會(oral society)的正常狀態,因為在這樣的社會中每一件事物與每一件事物之間無時不相互影響。」同時,「我們最普通、最一般的態度好像突然扭曲成古怪的、荒誕的形狀,熟悉的體制和關係好像突然變得恐怖邪惡起來。」不論沉默的原因是什麼,也不論它採用什麼樣的形式,它已經成了文學的一種態度,也成了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事實。 ● < TOP>
Bounds of reason:game theory and the unification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作者: (美)赫伯特·金迪斯著;董志强译
简介: 博弈论对于理解人类行为至关重要,且与各门行为学科――从生物学和 经济学到人类学和政治科学――关系重大。然而,正如《理性的边界》所论 证的,单靠博弈论并不能彻底解释人类行为,应辅之以各门行为科学所尊崇 的关键概念。 赫伯特?金迪斯指出,离开渊博的社会理论,博弈论不过是唬人的技巧 ,而离开博弈论,社会理论则只是一项残破的事业。《理性的边界》带领我 们重新审视博弈论工具的有用性,并教授我们运用恰当的分析工具,来打通 各门行为科学的经脉。
作者: 罗曼·克兹纳里奇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2018年01月
简介:
几千年来,我们一直注重向内看,认识自己。现在,是时候向外看了,我们需要走出自我,探索他人的生活与视角。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外观时代,而外观时代的核心就是同理心。
从销售管理到婚恋家庭,从社会关爱到政治行动,在人生的很多竞技场上,同理心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理心是21世纪值得拥有的关键能力,正以看不见的方式深刻影响着我们的发展。
罗曼·克兹纳里奇在《同理心》一书中指出,同理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是人类成就自己的核心所在。作为同理心领域的权威研究专家,作者提出了高同理心人士拥有的6个习惯,这些习惯能够让你更好地理解他人,迸发创意。同理心不仅可以成就个人事业,而且正在引发全球变革,改变我们的生活。
【目录】
前言 同理心:从根本改变的力量 VII
二十几岁的年轻设计师穆尔,摇身一变成了85岁的老太婆,让她从全新的角度设计商品。她的“同理心模式”启发了一整个世代的设计师,让他们更了解使用者的感受。
人际关系的革命 VII
培养高度同理心的6个习惯 XII
高同理心人士的6个习惯 XIV
解决同理心赤字的问题 XVII
“内观”到“外观” XXIII
同理心的挑战 XXIX
习惯1:打开你的同理心开关 001
你的童年与青少年经历如何影响你发挥同理心的能力?你认为从以自我为中心转变为将心比心的关键是什么?原因为何?
科幻小说还是科学事实? 003
人本来就自私,不是吗 005
为何有人会冲进火灾现场救素昧平生的人 010
三山实验——两三岁小孩即有同理心 013
越常被冷落的孩子,越有暴力倾向 017
挑战达尔文:演化显示合作与竞争一样重要 020
为什么看恐怖电影时手心会冒汗 026
我们能借助学习让自己更有同理心吗 033
重新架构你的心智 039
习惯2:进行想象的跳跃 043
回想你试着为他人设身处地地着想的一段经历。你因此获得什么改变?你对哪种人难以拥有同理心,原因又是什么?你该如何靠同理心跨越你们之间的鸿沟?
如果同理心对我们有好处,我们为什么不多使用它? 045
偏见:贴标签逻辑 046
权威:平凡的邪恶 050
距离:无法看见自己的行为后果,所以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054
否认:过多信息造成同理心疲乏 057
辛德勒的转变:开始把犹太人当人看 060
同理心小练习:每一天有多少人参与你的生活? 065
找出你跟他人共有的部分,以及你跟他人的差异 069
对敌人投以同理心 076
成为蝙蝠是什么感觉? 083
习惯3:探索与实践同理心 085
你打算如何善用假期,接触来自不同文化或社会经历背景的他人?想一下哪个人的政治或宗教立场与你截然相左,你该如何让自己更理解那个人的观点?
成为丹尼尔·戴–刘易斯 087
融入:成为一名隐秘同理心者 089
探索:同理心的旅程将如何改变你 101
曼德拉:我爱我的敌人,我痛恨的是令我们相残的体制 105
旅行,驱散偏见迷思的*好方式 108
合作:为什么应该参加地方合唱团 112
学习同理心的语言 119
习惯4:锻炼对话艺术 121
你跟陌生人的哪次谈话*出乎意料且发人深省?你家中*的压力与误解来源是什么?你该怎么促成谈话,让彼此更了解对方的感受与需求?
谈话危机 123
对陌生人充满好奇 125
积极倾听 134
卸下面具 140
关心他人 145
怀抱创意精神 150
保持大胆无惧 151
你对自己有同理心吗? 154
习惯5:坐着椅子旅行 157
哪部电影、小说或其他作品特别激发了你的同理心,改变了你为人处世的方式?数字文化如何影响到你的心境、个性与人际关系?减少上网会让你更能发挥同理心,还是适得其反?
你有办法在自家客厅改变世界吗? 159
戏剧与电影:用敌人的眼光看待战争 160
摄影:影像的政治力量 169
文学:我们能从小说中学习同理心吗? 175
在线文化:从数位革命到同理心革命? 181
颂扬出神作用 191
习惯6:激起同理心革命 193
想出一个你非常关心的社会或政治议题,思考该如何诉诸同理心,唤起更多民众关注那个议题并采取实际行动?你该对生活做出哪些改变,借以加深你对自然界的同理心?
全球携手发挥同理心 195
英国*多陌生人彼此接触的时期 196
*波浪潮:人道主义在18 世纪风起云涌 201
第二波浪潮:人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渐提升 208
第三波浪潮:人际关系在神经科学时代渐渐深化 213
生物同理心的未来展望 221
推动革命浪潮 226
结语 同理心大未来 229
你未来*可能培养这6个习惯之中的哪一个?而在接下来的48小时以内,你会踏出怎样的*步?
同理心谈话 230
高同理心人士的六大习惯 231
同理心博物馆 233
致 谢 243
注 释 245
参考文献 265
【免费在线读】
科幻小说还是科学事实
星历3196年。星舰企业号在寇克舰长指挥下,奉命前往贾纳斯六号行星上的矿业殖民地进行调查。据报当地出现奇怪生物,近来杀死50名矿工,而且破坏珍贵的设施。寇克舰长与他信赖的瓦肯人大副史波克,在地底深处的隧道里遇见了这个生物,那生物看起来像一团熔化的岩石。寇克与史波克对它发射光束枪,它负伤逃脱。不久,寇克跌进一个房间,里头到处是圆形的小硅石,数量约有数千颗,那个奇异生物也在里面。但现在那个生物已经受伤,看起来无法带来什么威胁。寇克希望能跟它沟通,以了解整个暴力事端。史波克主动表示他能帮忙。
“舰长,你知道瓦肯人有联系两个心灵的能力吗?”史波克说完,慢慢将手伸向那个生物,他闭上眼睛,聚精会神地连接生物的心灵。
“痛!痛!痛!”史波克突然大叫,踉跄地退后。
从这段短暂的同理心接触中,史波克得知这个生物自称霍尔塔, 她因为矿工无意间压碎了她的孩子而感到痛苦,她的孩子本来即将从这些遍布于矿坑的圆形小硅石里孵化。霍尔塔攻击矿工的*理由就是为了保护这些蛋。
得知这点后,寇克舰长告诉矿工不要碰触霍尔塔的蛋,而霍尔塔也会让矿工自由挖掘这里的珍贵矿产。《黑暗中的恶魔》(TheDevil in the Dark)是星际迷航原初系列的经典,于1968 年推出,故事*终圆满结尾。史波克的瓦肯人“心灵结合”能力再度化解了一场纷争。
这是科幻小说还是科学事实?人类也许不具有像瓦肯人那样的同理心能力:只要将手指碰触对方的头骨,就能与对方的思想和情感相通。然而,现代科学有一项*令人振奋的发现,那就是我们远比自己想象的更像瓦肯人。传统达尔文观念认为驱策人类的主要动机是自利,以及为了自我保存而产生的好斗驱力,也就是说,人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动物,但我们*好将这种观念抛诸脑后。根据对人性的*理解,人类是有同理心的动物,天生具有与他人心灵相通的能力。
要发展同理心能力,首先必须掌握一个现实,那就是我们是谁。我们必须挖出潜在态度(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称之为“世界观”),偏偏认知自我内在的这部分长久以来一直不受西方文化重视。如果我们一直认为自己不过是利己的动物,那么我们将不会有机会做出改变。想改变自己,*好的办法就是认识到这项令人惊喜的发现,也就是人类是有同理心的动物。本章将介绍这则至今鲜为人知的故事,表明我们是如何发现自己拥有同理心的自我。这则故事从一名17世纪哲学家的理论开始,然后一路来到*的关于镜像神经元的脑部研究,其间将历经对心理学历史的考察、针对失去父母的幼儿的研究,以及对黑猩猩情感生活的调查。
高同理心人士的*个习惯是“打开你的同理心开关”,也就是更深入了解人性中体现同理心的一面。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了解两件事。首先,同理心能力是人类祖先遗传给我们的,也就是说,同理心历经了长久的演化过程。其次,同理心可以在我们的人生中不断扩展,因此我们随时都可以加入这场同理心革命。将同理心深植在我们的心灵中,可以作为日后培养其他5个同理心习惯的完美基础,使心灵做好准备,设身处地为人着想。
我们要从哪里开始学习大脑的同理心能力呢?首先,我们要探索人类文化*强大的一种说法,并且了解这种说法的根源:人类本质上是自私的。
人本来就自私,不是吗
我们对人性感到悲观,甚至发表一些愤世嫉俗的看法。西方各国进行的调查数据显示,我们刻板地认为“绝大多数人不可信任”且“绝大多数人只为自己着想”。1 人性自利的假定如此深植人心,以至我们几乎未曾注意到它的存在。“喔,这是人性。”人们总是用这句话来描述卑鄙、以自我为中心或负面的行为。另一方面,当看见有人做出关心与慷慨的行为时,我们却从未耸耸肩说:“嗯,你觉得意外吗?慷慨本来就是人性。”2 同理心、仁慈与其他慈善行为向来被视为人性的例外。
然而,这种人性观点如此根深蒂固并不让人意外。它确实反映了一部分现实,人的确生性自私好斗。但这种人性观也仅是一则人性故事,300 多年前经由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宣扬才流传至今,这是我们的文化遗产,一种逐渐渗透到我们的集体想象中的意识形态。找出谁该为此事负责,可以让我们重新发现自我的同理心。主要“嫌犯”有 4 位。
在近代西方思想中,人性自利的说法始于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他在1651 年出版的作品《利维坦》(Leviathan)中指出,如果人类处于“自然状态”,也就是不存在任何政府形式的状态,结果将是“所有人对抗所有人的战争”,而人生将是“孤独、贫穷、卑鄙、残酷而短暂的”。霍布斯的结论是,像人类这种天生喜爱追逐私利与诉诸暴力的生物,需要权威的政府加以限制。虽然霍布斯试图提出普世性的说法,但他的观念终究属于他生存时代的产物:他对人性的负面看法,无疑受到他所处时代的影响,当时霍布斯正处于英国内战的血腥动荡中。尽管如此,《利维坦》依然成为西方思想*重要的作品之一。20世纪80年代,当我攻读政治专业时,《利维坦》依然排在书单的前列。
18世纪,自利的意识形态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中找到了新的支持者,那就是思想家亚当·斯密。在这则故事中,他也是个不寻常的人物,他决定了我们理解同理心的方式。然而,斯密对同理心的看法,却完全被他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的激进自利理论给掩盖过去。斯密认为,在经济市场上,当买家与卖家都致力于追求个人利益*化时,商品与劳务将会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有利于整体社群的状况下进行分配。斯密写道,“在提升社会利益方面,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通常要比自己实际追求社会利益更有效”。这个想法的力量在于,它为自利行为提供充分的经济与政治理由,这有助于解释斯密在工业革命时何以深获商业与政治精英的欢迎。之后,“看不见的手”成为新古典经济思想的支柱。新古典经济思想在20世纪后半叶成为主流,而且在撒切尔主义与里根经济学的市场意识形态中获得政治表达。这个经济思想的领导人物,如奥地利贵族哈耶克,他呼应斯密的说法,主张“尽管只是追求己利,却能为同胞带来*的利益”。3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出版于1859年,书中肯定了霍布斯与斯密的说法。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理论强化了人类天性自私的观点:推动人类演化的驱动力是竞争而非合作。事实上,达尔文的人性观没那么简单,但这种被简化诠释的达尔文观念后来被“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加以普及,例如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他创造了“适者生存”一词。斯宾塞认为,富人不需要因为自己的财富而感到罪恶,因为这是他们的才能与优越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斯宾塞的作品在美国特别畅销。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写道,“斯宾塞是美国的福音,因为他的观念符合美国资本主义的需要”。4 20 世纪70 年代,达尔文的理论出现不同的诠释,演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表示,人类其实是“传递基因的机器”。5 他的隐喻“自私的基因”成了著名的科普用语,尽管道金斯从未主张基因拥有自主意志,却刚好与思想史的悠久主题遥相呼应,强调自利潜伏在我们人类的心灵深处。
*后一位关键人物是弗洛伊德,他的作品把人性自利的观点深深固结在西方人的心灵中。在《文明及其缺憾》(Civilizationand its Discontent)中,弗洛伊德试图去除所有对人性的浪漫幻觉,特别是当时的欧洲已经经历了*次世界大战。“人类不是温和的生物,”弗洛伊德写道,相反,人类有“好斗的倾向”。即使是婴儿,也会无情地寻求自己的利益。与霍布斯一样,弗洛伊德相信,如果没有适当的控制,人类会变成“野蛮的兽类,要他们体贴同类是不可能的”。人类受到性欲与好斗心的驱使,不会爱人如己,而是会“不征得他人同意,向他人发泄性欲,抢夺财物,羞辱他人,让他人痛苦,折磨并且杀死他人”。6在这个性欲主导的人性观里,人就像怪物一般,没有同理心容身之处。
所以,身处21世纪初的我们,已经有300多年的时间完全浸淫在这个主导一切的信息里:自利*终决定了我们的面貌。而毋庸置疑,这个信息已完全被吸收到西方文化之中。我们的语言表现方式更是强化了人性黑暗的一面,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与“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经济学课程假定人是理性而自利的行动者。翻开报纸,你常看到的是冲突的报道而非合作的新闻,同理心的行为很少登上报纸头条。好莱坞电影充满了暴力血腥,却美其名曰“动作片”。孩子从阅读农场动物故事,快速跳升到玩计算机游戏,游戏的内容通常是打打杀杀,仿佛陷入霍布斯的噩梦之中。然而我们似乎觉得这很正常。
霍布斯、斯密、达尔文与弗洛伊德,在这4位强有力的思想家以及他们的追随者的持续思想攻击下,我们一直相信同理心与自利一样,都是人性的一部分。这当中*的悲剧是,人们至今只认识到人性的一部分,也就是强调自利的自我,以为人性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因此,今日当我们听到这么多有关“同理心的人”的讨论时,我们的感受是什么?而我们又是如何发现自己拥有一个具有同理心的大脑?
为何有人会冲进火灾现场救素昧平生的人
令人吃惊的是,当我们在西方文化中追溯同理心思考的根源时,这些源头作品的作者居然与自利心叙事的作者是同一人。斯密在《国富论》中宣扬追求自利对社会有利,但他另一本比《国富论》早 17 年出版的作品《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Sentiments), 却对人类动机提出更复杂与更完整的描绘,而这部分是针对霍布斯悲观的自然状态所做的响应。7斯密在《道德情操论》的开头写道:“无论人有多么自私,在他的本性中显然存在着一些原则,使他关注他人的命运,使他人的幸福成为他的必要之物,虽然他无法从他人的幸福得到分毫好处,但光是看到他人幸福,就足以令他感到愉快。”在这句话之后,斯密开创了世上*篇论述完整的同理心理论——当时还称为“同情心”——他指出,我们生来有能力站在别人的立场思考。而斯密把这种能力描述成我们可以“想象自己是那个受苦的人”。斯密的观点获得同时代的苏格兰哲学家休谟的支持,休谟认为,“在我们被揉成人形的过程中,加入了一些鸽子的微粒,又添入了一些野狼与毒蛇的成分”。
达尔文也清楚察觉,日常生活并非总是充斥着张牙舞爪的自私者,他认识到人其实有善良的一面。达尔文注意到许多哺乳类动物具有社会性,举例来说,狗与马会因为与同伴分离而伤心难过。他因此相信人类一定也存在着“社会本能”,这解释了为什么有人会冲进失火的建筑物去救素不相识的人,即使这么做可能危及他的性命。在《物种起源》出版多年之后,达尔文已转而相信合作互惠跟竞争一样,也是演化过程的重要环节。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中强调同理心,可惜当时未获重视,我们只能从现在开始恢复其应有的价值。8
斯密与达尔文无法忽视这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人是社会动物,人会关心其他人,并且为其他人的利益而行动,即使这么做有可能损及自己的利益。斯密与达尔文可以从人们对自己的家人与朋友的关切看出这一点,但18、19世纪兴起的人道主义组织(例如反对童工的组织)也让他们有更深的体会。然而,社会的主流人群鲜少有意愿聆听他们提出的人有同理心的说法。自利的故事无疑更让政治人物与实业家我行我素,前者对人类福祉毫不在意,后者只关心如何让工厂获得便宜的劳工。
直到20世纪初,心理学成为显学之后,同理心的概念才获得应有的关注。英文empathy (同理心)这个词的根源可以溯至德文Einfühlung ,后者字面上的意思是“神入”(feeling into)。Einfühlung 在19世纪因为德国哲学家西奥多·利普斯(这位哲学家现已无人提起,但当时曾获得弗洛伊德大力赞赏)的提倡而大受欢迎。利普斯把 Einfühlung 视为哲学的审美概念,指人投入艺术作品与自然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可以让人对艺术作品与自然做出情感上而非理性上的回应。1909 年, 美国心理学家爱德华·蒂奇纳认为英文也应该拥有对应 Einfühlung 的词汇,于是他创造了 empathy 这个词(根据古希腊文 empatheia 所创,意思是“in”加上“suffering”)。此后,empathy 的意义就经历了一连串的变化,带来复杂的语言学遗产,必须加以阐明才能理解其中的内容。
心理学家很快就将同理心从艺术领域挪用来表示模仿的形式。在一本20 世纪30 年代广泛流行的心理学教科书里有一张照片,一名撑竿跳选手成功跃过横杆,而底下的观众无意识地抬起双腿,脸上露出纠结的神情,仿佛他们自己也在进行撑竿跳。这张照片的标题叫“同理心”。作者接着提到听众经常会模仿台上演讲者的表情,举例来说,当演讲者微笑,台下的听众也会不自觉地跟着微笑。这是同理心的经典例证。9
然而,从1940 年之后,同理心的两个早期意义,即艺术的鉴赏模式与情感上的模仿,逐渐转化成另外两种取向。这两种取向,大家在今日的心理学教科书中都可以查到:首先,同理心是视角的转换(有时又称为“认知同理心”);其次,同理心是分享的情感反应(又称为“情感同理心”)。那么,这两种取向的意义是什么,这两种概念又是怎么来的?
三山实验——两三岁小孩即有同理心
在认知同理心方面,巨大的突破出现在1948年,瑞士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公开了一项实验成果,这项实验被称为“三山实验”。他让不同年龄的孩子站在立体的山脉模型前,他要这些孩子描述模型里的小人儿在不同位置看见的山是什么样子。4岁以下的孩子在描述时总是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完全没考虑到小人儿的视角。相反地,4岁以上的孩子已经能从小人儿的视角来描述景物。皮亚杰认为,这说明了在一定年龄以下的孩子,还没有能力思考他人的观点。
同理心研究领域目前达成的共识,是以皮亚杰开创的视角研究为基础,认为孩子大概在两三岁的时候开始产生基本的想象能力,可以想象他人的视角。10关于这一点,我从我的双胞胎子女身上看到实例。当他们才18个月大的时候,如果哥哥哭了,那么妹妹会试着安抚他,方法是把自己的玩具狗交给他。但是,等到他们到了24个月大的时候,如果哥哥哭了,此时妹妹不会把自己的小狗交给他。她已经了解,如果她拿哥哥喜欢的玩具猫给哥哥,那么哥哥会更开心。这就是认知同理心或视角转换(有时又称为“心智理论”)的要旨。它牵涉到想象跳跃与理解其他人有不同的喜好、经验与世界观。从童年初期,也就是幼儿开始认识到自己与他人的不同的时期,自然发展的认知同理心可以看出,人类天生是社会动物,同理心是与生俱来的。同理心并非如同史波克所做的那样,单纯地读取他人的心智。
第二种同理心,“情感同理心”,主要不是以认知能力理解“他人的想法”,而是分享或反映他人的情感。因此,如果我看见女儿悲伤哭泣,而我也感到悲伤,这就表示我产生了情感同理心。另一方面,如果我注意到她的悲伤,但我自己感受到的却是别的情感,例如怜悯(“喔,可怜的小东西。”),那么我显示的是同情心而不是同理心。同情心一般指的是情感的响应,但并非分享对方的情感。你也许留意到我一开始为同理心下的定义结合了情感与认知元素:同理心牵涉到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理解他人的情感(情感方面)与视角(认知方面),并且运用这个理解来指引我们的行为。实际上,这两种形式的同理心经常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同理心的双重定义包含了同理心的认知与情感形式,这有助于我们厘清两个常见的混淆。首先,经常有人批评同理心,认为同理心可以用来“操纵”人。例如,连续杀人犯也许试图了解受害者的想法,然后再引诱并且杀害他们。但疯狂的杀人犯只是采取认知的步骤,理解他人的想法,他从未分享他人的情感,也不关心他人的福祉。使用认知的洞察力来操纵人,以满足自利的目的,从同理心本身的合理与完整的定义来看,这显然不能说是运用同理心来操纵人。
第二个混淆是人们经常将同理心与怜悯(compassion)这两个词互换使用。这两个词虽然在某些方面的意义有交集,但两者毕竟是截然不同的概念。怜悯的拉丁文字源意思是“与他人一同受苦”。这与同理心不同,同理心不仅能分享痛苦,还能分享喜悦。此外,怜悯强调与他人的情感联系,意即感受他人的情感。但怜悯通常不包括认知上的跳跃,理解与自己不同的他人信仰、经验与观点。怜悯通常指的是同情的情感响应,例如可怜对方与慈悲心,但同理心完全不是如此。尽管存在这些差异,在某些文化与宗教传统中,同理心与怜悯却是紧密交织的。举例来说,佛教的怜悯观念经常强调以同理心理解他人的视角与世界观。不过,整体来说,我们在使用同理心与怜悯时必须加以区分,不能混为一谈。
认知同理心与情感同理心的区别,有助于我们思考这个经常引起讨论的话题:女性是否天生比男性更具有同理心。心理学家巴伦– 科恩肯定这种说法。他发现在标准同理心测验上,女性普遍比男性得分高,他因此大胆认定:“女性的大脑倾向于发挥同理心,而男性的大脑倾向于理解与建构体系。”根据他的观点,女性比较擅长处理人际关系与情感,而男性相对擅长处理分析与机械性的任务。性别差异从童年初期就能明显看出,这绝不是文化力量所能解释的,比如带有性别刻板印象的玩具广告反复不断地播出,或者是父母的行为与父母对子女的期待。11
这是否表示你应该把现在读的这本书丢到一旁?如果你是男性, 那么你努力让自己有同理心也没意义,如果你是女性,那么你原本就擅长发挥同理心。当然不是如此。首先,巴伦–科恩的研究并不是说所有的女性比所有的男性都更有同理心,而是指平均值,从整个范围来看,有些男性具有高度的同理心,正如有些女性很缺乏同理心。其次,大部分的测验只能测出情感同理心而非认知同理心。这些测验的焦点主要放在我们响应他人情感的能力上,因此测验通常会问到这样的问题:“你是否能辨别对方隐藏了自己真实的情感?”或者“如果你看到有人因新计划而受损害,你是否会感到难过?”12很少有证据显示,男性与女性在视角转换的认知同理心上有明显差异。*后,我们面对性别差异时必须非常谨慎,事实上,真正的重点不在于你生来有多少同理心,而是你愿意发挥多少同理心。通过他人的眼睛来增强你了解世界的能力,这要比你是男是女来得重要。
越常被冷落的孩子,越有暴力倾向
我们接下来重新介绍,现代心理学如何发展出同理心的概念。就在皮亚杰进行三山实验的同时,另一批研究人员有了令人吃惊且不安的发现,那就是人类的情感与社会性在婴儿初期是如何发展的,特别是情感同理心能力。1945年,奥地利裔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勒内·施皮茨进行了世界上*个母亲与情感剥夺研究,这个实验在美国两个非常不同的儿童之家进行。*个地方是孤儿院,这里环境卫生而且食物充足,但是这些婴儿与照顾他们的人却维持*程度的身体与情感接触,而在当时普遍是这样照顾弃婴的。护士很少抱婴儿,而每张婴儿床之间还隔着床单,以避免细菌传染。婴儿几乎一整天都保持孤立状态,没有人给予刺激。*后的结果是:尽管受到良好的照顾,91 个婴儿中还是有34 个在两岁前死亡。另一个儿童之家在监狱里, 但身为受刑人的母亲每天都能获准看望她们的孩子,她们可以抱孩子、与孩子玩耍。监狱里的卫生标准也许不像孤儿院那么高,但没有婴儿死亡。两年后,施皮茨在一部影片中更生动地表现这项差异:弃婴刚送到孤儿院时还能咯咯笑,但几个星期之后,婴儿就变得茫然孤独,他们会咬自己的手,体重也减轻。几个月后,他们变得憔悴衰弱,既不会表达,也没有动作,仿佛徒具人形的物品。13
施皮茨令人震惊的研究,显示人类情感在维持生命存续上,也许比食物与庇护更为重要,或至少在人类需求阶序上是与食物和庇护同等重要。英国精神科医师约翰·鲍尔比将施皮茨的工作更推进一步,他提出“依附理论”来解释施皮茨的发现。20 世纪50 年代,鲍尔比揭示孩子早期与母亲(或*初的照顾者)的关系,对于孩子情感与心智的发展有关键性的影响。如果婴儿未得到深厚的情感,特别是在一岁时,“那么就有可能危及婴儿未来的幸福与健康”。14 这是婴儿开始学习基本的人类沟通技能的基础时期,例如解读面部表情,以及辨识与约束自身的情感。一旦婴儿被剥夺了安定的依附关系,或婴儿开始产生恐惧感,害怕失去依附的对象如父母,那么往后他们可能发展出一定程度的问题行为模式,从焦虑与情感分离,到好斗与反社会人格。因此,如果一个人在婴儿时期面对的是毫无响应或未付出情感的父母(例如,父母在苦恼时只是任婴儿啼哭),那么很可能冲击他们对压力的感受,导致暴力行为的发生。15
鲍尔比的发现对弗洛伊德学派来说是个直接的挑战,许多弗洛伊德学派学者依然执拗地相信,人类主要由个人的物欲与性欲所驱动。与此相反,鲍尔比改变了对人性的看法,认为需要伙伴与社会性才是人性的核心。或者,如心理治疗师休·格哈特所描述的,“每个人生来都会寻求情感联结,而且想依附于能提供保护的成人身上,也就是能关心他与回应他的人”。16鲍尔比的研究,连同其他心理学家如玛丽·安斯沃思的发现,给我们提供了两个重要的视角,有助于我们了解同理心。首先,缺乏安定的依附关系,将阻碍同理心的发展,特别是会损害与他人建立情感关系的能力,而这正是情感同理心的基石。其次,培养情感能力(例如让孩子产生同理心)的*有效做法,就是让孩子看见父母的同理心。心理学家艾伦·斯洛夫解释道:
你如何拥有具有同理心的孩子?想拥有具有同理心的孩子,靠的不是教导孩子或告诫孩子要有同理心,而是身为父母的你必须对孩子有同理心。孩子对人际关系的理解,完全是从他体验到的人际关系中得到的。17
鲍尔比的依附理论尽管在当时饱受争议,但今日已得到儿童心理学家与育儿专家的广泛认同。然而,对于想发展同理心的人来说,依附理论反而成了令人沮丧的消息。如果我们在婴儿时期并未浸淫在情感与同理心之中,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到了青少年或成年阶段将很难有机会扩展我们的同理心?据估计,每三人就有一人在成长过程中缺乏安定的依附关系,对这些人来说,要成为具有同理心的人是否为时已晚? 18
别担心。即使幼年时期是大脑专注而密集发展同理心回路的时期,但成年之后我们仍有可能扩展我们的同理心。只是这么做稍微困难了点儿,因为我们已经养成了固定的响应、思考与行为模式,这些模式会抗拒我们进行同理心的想象。如鲍尔比所言,“我们一生随时都能改变”,只要有对的环境,有对的刺激,我们就能克服不安定的依附所加诸的限制。19 好消息是我们每个人都有隐藏的同理心潜力, 这是长期演化与基因遗传赋予我们的。而这也引导我们来到下个阶段:我们是怎么发现有同理心的人存在的?随着20 世纪四五十年代心理学的进展,过去20 年来,演化生物学与神经科学已经对同理心的起源与性质有了爆炸性的全新理解,说它们在同理心研究上居于前沿也不为过。
挑战达尔文:演化显示合作与竞争一样重要
1902 年, 既是无政府主义的革命分子, 也是著名科学家的彼得·克鲁泡特金写了一本《互助论》(MutualAid:A Factor ofEvolution)。他反对正统的达尔文物竞天择的观念,主张在演化过程中,合作互助与竞争一样重要。绝大多数的动物,从蚂蚁到鹈鹕,从土拨鼠到人类,都显示出合作的倾向,会分享食物、保护彼此免受掠食者的攻击,因此能够存续与繁衍后代。举例来说,野马与麝香牛会以幼兽为中心围成一个圆圈,以防止野狼攻击。20
当《互助论》出版时,克鲁泡特金被大家当成怪胎,因为他的思想比他的时代超前了一个世纪。今日,他的观点已成为演化生物学的主流,许多演化生物学者相信,同理心是理解动物合作行为的关键。主张此说的不乏知名学者,如荷兰灵长类动物学家弗兰斯·德瓦尔,他曾被《时代周刊》(Time)票选为世界100位*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一名黑猩猩研究专家何以能获得如此高的赞誉?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他的研究成果使传统的霍布斯与达尔文人性观完全改观。他发现,对许多动物来说,如大猩猩、黑猩猩、大象、海豚,同理心是一种天赋,人类更是如此。德瓦尔提醒我们,人是有同理心的动物,他为了证明这件事所做的努力,全世界恐怕无人出其右。
我问德瓦尔,为什么他对同理心的演化这么有兴趣?“没有人否认人类是好斗的。事实上,我认为人类是*好斗的灵长类动物。”他对我说。21尽管如此,他认为我们也要当心,不应该把人类简化成会杀人的猿猴。“我们被灌输太多的荒谬思想,例如人天生好斗,注定自相残杀。”他说道。德瓦尔指出我们的基因与爱好和平、类似嬉皮的倭黑猩猩非常接近,倭黑猩猩比其他灵长类动物如黑猩猩更具有同理心。德瓦尔说:“同理心是我们的第二天性,如果有人想去除自己的同理心,我们会认为这个人相当危险,或者精神有问题。”22
德瓦尔认为,同理心对人类来说是极为基本的东西,而且鲍尔比与皮亚杰的心理学研究都证明同理心在人类幼年时就开始发展,因此不可能在人类与猿猴在世系上分离之后,才在人类身上出现。人类与猿猴有着共同的祖先,我们可以研究我们的灵长类亲戚,从中学习人类漫长的演化历史。
德瓦尔向我解释,其他物种的同理心证据非常多。“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其他学者以及我的小组已进行了许多研究,我很难在此一一加以详述。我们观察黑猩猩进行的所谓的安慰行为,竟多达数千例。只要群体中有黑猩猩感到悲伤,也许在打斗时败下阵,也许从树上掉下,也许遇到了蛇,其他黑猩猩就会过来安慰它。它们会拥抱悲伤的黑猩猩,或试着亲吻与理毛来让它恢复平静。”这种情感的感受力正是灵长类学家黛安·福塞所观察到的,她曾于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中非维龙加山脉的雾蒙蒙的雨林里,与大猩猩一起生活了13 年,她在大猩猩身上发现这种能力。
但是,我们如何确定这些反应真的源自同理心,而非其他情感?德瓦尔对此毫不怀疑,他认为这是同理心的作用。他提出一则故事作为例证:英国特怀克罗斯动物园里有一只名叫库妮的倭黑猩猩。一天,库妮发现一只鸟撞上它的玻璃围栏,鸟因此受了伤。库妮把鸟带到树上,想让鸟自由,它在把鸟丢出栅栏之前,还刻意地张开鸟的双翼。然而这只鸟没办法飞,库妮于是守着这只鸟直到天黑,直到鸟终于顺利飞走为止。对德瓦尔来说,这是个完美的证明,显示倭黑猩猩确实有站在其他生物角度思考的能力。“在看过鸟儿飞翔无数次之后,库妮似乎察觉到怎么做对鸟是好的,我们因此看见倭黑猩猩表现出斯密说的那句话,‘想象自己是那个受苦的人’。”23
德瓦尔也跟我提到,他*的实验显示同理心能驱动利他的行为。他把两只卷尾猴放在一起。其中一只需要用小塑料代币与研究人员交换东西。实验关键的部分来了,德瓦尔给卷尾猴两枚颜色不同的代币,而这两枚代币分别代表不同的意思:其中一枚代表“自私”,另一枚代表“具有社会倾向”。如果负责交换的猴子捡起自私的代币,并且将代币还给德瓦尔,那么这只猴子将可获得一颗苹果,但它的搭档什么也得不到,而具有社会倾向的代币则能让两只猴子都有苹果吃。逐渐地,猴子选择具有社会倾向的代币次数越来越多,显示它们确实关心彼此的福祉。德瓦尔解释说,猴子这么做,不是因为害怕可能的后果,因为研究人员发现*支配性的猴子,也就是猴群中*无惧的猴子,实际上也是*慷慨的猴子。
这项实验与早期一场极为著名的证明动物同理心的实验非常类似。1964年,精神科医生朱尔斯·马瑟曼提出报告说,如果拉扯链子可以获得食物,但同时也会让同伴遭到电击,那么恒河猴就会拒绝拉扯链子。有一只猴子因为看见另一只猴子遭到电击,而拒绝拉扯链子达12 天之久,实际上已经等同于宁可饿死,也不愿让同伴遭受伤害。24
德瓦尔研究灵长类动物数十年,他认为人类发展出同理心,理由可能有两个。首先,为了确保我们能回应子女的需要:如果母亲无法对孩子由于饥饿而啼哭做出适当的反应,那么婴儿的生命可能陷入危险。德瓦尔说:“哺乳类动物在1.8 亿年的演化过程中,母亲能响应子女要求的哺乳类动物,要比母亲表现出冷淡与疏离的哺乳类动物,更有机会存活。”其次,也呼应了克鲁泡特金的说法,互助有利于个人与团体的存续。举例来说,在艰苦的原始环境中,同理心使人类彼此合作,确保团体内的每一个人都有东西可吃。“有效的合作必须以情感与目标一致为前提。”德瓦尔表示。25 他认为在演化过程中, 合作是促使物种成功存续的重要因素,而他的这个想法也获得其他说法的支持。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合作也存在于细胞的层次上。*初的细菌有些会构成线形,在每条线上的某些细胞会自行死亡以供应氮给相邻的细胞。26
德瓦尔并不就此满足,他不希望自己的发现只发表在学院的学术期刊上。他的前辈克鲁泡特金认为,社会应该在更强调共同性与合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才能反映人性中的合作倾向。德瓦尔也这么认为。他相信自己的研究成果的内涵,可以让他设计出使人类欣欣向荣的社会模式:
我无法忍受美国保守派以生物学为根据而提出的各种说法。他们只是拿生物学作为自己政策的托词,认为既然自然界是以“适者生存”为基础,那么我们的社会就应该以自私与竞争为中心。这些人其实是用自己的私心来解读大自然,我认为我必须指出这些人的错误。自然界有许多动物仰赖合作才得以生存,我们人类尤其是仰赖远祖的彼此依靠才得以存续至今。同理心与连带感是我们的天性,因此我们的社会也应该反映人性的这一点。
根据德瓦尔的观点,自由市场经济显然也不是“自然的”。他表示,“你需要把同理心从人的天性中除去,才有可能做到*资本主义的立场。”27德瓦尔也相信,同理心能侵蚀掉我们的暴力与种族主义文化,而且能扩展我们道德关注的疆界。“同理心是人类库房里的一项武器,可以解除我们身上的仇外诅咒,”德瓦尔说,“如果我们能把其他大陆的居民视为我们的一部分,大家一起过着互惠与具有同理心的生活,我们将能培养——而非破坏——我们本性中固有的东西。”28
德瓦尔的研究是一种典范转移。在17世纪,伽利略证明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太阳与其他行星并未绕着我们居住的地球转,他的说法震惊了欧洲社会。德瓦尔的说法也具有同样的革命作用:人性不只是绕着自利转。同理心才是我们本性的核心。具有同理心的人已经在地球上漫游了数十万年。我们的任务是创造一个能协助——而非阻碍——同理心自我发展的世界。
为什么看恐怖电影时手心会冒汗
心理学家与灵长类学家的研究成果,使我们在20 世纪对同理心的认识迈进了一大步。霍布斯的传统人性观点已经站不住脚,而且也不合理。不过,还有一项证据来源是目前为止尚未触及的,那就是我们大脑内部的神经活动。从20 世纪进入21 世纪,神经科学已经成为同理心研究中*创意的领域。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确认,即使是霍布斯的大脑,也必然能产生同理心。究竟,科学家在我们的脑壳里发现了什么?而他们的发现是否揭露了同理心在人体内的实际运作过程?
故事开始于1990 年8 月,地点是意大利帕尔马大学的实验室。贾科莫·里佐拉蒂率领的神经科学研究小组对猕猴进行实验,他们在猕猴的脑部植入一个跟头发一样细的电极。研究小组发现,当猴子捡起花生时,前运动皮质的区域会出现活化反应。然后,在某个特别的时刻(科学上的重大发现经常在不经意的时刻出现),小组发现当猴子碰巧看见研究人员捡起花生时,即使这个时候猴子没有任何动作,它们脑部的前运动皮质区也同样出现活化反应。大脑做出的反应,仿佛猴子自己亲手捡了花生似的。里佐拉蒂与他的小组简直不敢相信会有这种事。但接下来对猕猴的实验,以及对人类的实验——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全得到了一致的结果。
他们在偶然间发现了“镜像神经元”。当我们实际经历某事(例如疼痛),或当我们看见别人跟我们有一样的经历时,我们的神经元都会产生电脉冲。拥有大量镜像细胞的人,容易产生较强的同理心,特别是在情感的分享上。根据里佐拉蒂的说法,“镜像神经元使我们能捕捉他人的心智,但不是通过概念推论,而是通过直接的刺激”。神经科学家维莱亚努尔·拉马钱德兰把镜像神经元的发现,比拟成克里克与沃特森发现双螺旋结构:“我预言,镜像神经元对心理学的影响,将如同DNA(脱氧核糖核酸)对生物学的影响一样巨大。”29
当代镜像神经元研究*重要的人物之一是克里斯蒂安·凯泽斯,他也是荷兰神经科学研究所社会大脑实验室的主任,曾经是帕尔马大学里佐拉蒂小组的成员之一。我请他解释镜像神经元为什么这么重要:
我们*感兴趣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理解别人。通常,我只要看着我太太的脸,我马上就能知道她心情如何(我也因此得知我是不是惹上麻烦了……)。好莱坞的电影可以充当不错的解说例证:在电影《诺博士》(Dr. No)中,当你看见一只狼蛛在詹姆斯·邦德的胸口爬过时,你会心跳加速,你的手会出汗, 你的皮肤会随着狼蛛的脚踏在邦德身上而感到刺痛。你在毫不费力的状况下,就感受到邦德的感受。这是怎么办到的?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使我们找出其中的原因:我们的大脑反映了其他人的状态。理解他们的感受,然后也理解自己感受他们的感受。神经科学因此发现了同理心。
容我大胆地说,这项发现使我们得到全新的人性故事。尤其是西方人,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总是以个人为思考的中心——个人的权利、个人的成就。然而,如果你把自己大脑的状态称为你对自己的认同(我会这么做),则我们的研究显示的是,你的大脑绝大多数时间里反映的是别人心里想的事。我的人格因此是我的社会环境造成的结果。其他人的命运影响了我的情感,也因此左右了我的决定。我其实就是我们。神经科学把“我们”重新放回大脑。这么做不是为了担保(我太太也会同意这一点)我的行动并非出于以自我为中心与自私,而是显示以自我为中心与自私不是主导我们大脑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社会动物,而就在10 年前,绝大多数人还不认为如此。30
镜像神经元的存在,意味着人必须从根本上重新加以定义:人的自我疆界要延伸到人的皮肤与骨骼以外的地方。如果凯泽斯与他的同事是对的,那么就表示我们其实跟瓦肯人一样一直处于心智融合的状态,但我们自己未察觉到这一点,我们的大脑持续反映我们的感官所感知的周遭世界,也许我们看见的是一张孩子啼哭的脸,或者是一只蜘蛛爬上邦德的胸口。我们的神经线路也塑造了我们的伦理行为,例如遵守黄金律的能力。凯泽斯认为,“神经科学显示,人的自然同理心有其局限,‘别人希望怎样被对待,你就怎样对待他’的伦理要求,要比‘待人如己’困难得多”。
镜像神经元无疑很吸引人,但它只是理解大脑同理心的开端。事实上,有些研究人员相信,它们获得了过多的关注。而他们之所以有此感受,部分是因为镜像神经元主要用来说明情感的分享(情感同理心)而非视角转换(认知同理心),所以在神经医学层次上谈同理心如何运作,将会产生偏颇。用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平克的话来说,因为镜像神经元的发现创造出“巨大的宣传泡沫”。他指出:
神经科学家与科学记者把镜像神经元吹捧成语言、意图、模仿、文化学习、时尚流行、运动迷、代祷,当然,还有同理心等等这些事物的生物学基础。镜像神经元的一个小问题在于,我们是从恒河猴体内发现镜像神经元,但恒河猴这个脏兮兮的小物种,从它身上我们看不出任何同理心的痕迹。31
剑桥大学心理学家与自闭症专家巴伦– 科恩的批判不像平克那么强烈,但他也认为应谨慎看待。巴伦– 科恩表示,“有些人一下子就认定镜像神经元本身可以等同于同理心”。但实际上,镜像神经元系统“只能说是同理心的基础材料”。举例来说,镜像神经元牵涉到模仿,就像有人打哈欠,我们也不由自主地打哈欠,或者我们喂婴儿吃东西,他们张嘴,我们也跟着张嘴。但“同理心似乎不只是不自觉地反映对方的动作。”巴伦–科恩说道。相反地,同理心牵涉到主动地理解他人的情感与心智状态,以及他人与我们的关系。
巴伦–科恩的观念后来成为同理心领域的共识,重点在于,镜像神经元是更为复杂的同理心回路的一部分,同理心回路至少包含了10个彼此相互连接的大脑区域。如果这些区域中有任何一个受到损伤或未获得适当发展,那么我们的自然同理心能力就可能受损。一名著名的神经医学病人,名叫S. M.,他脑中的杏仁核受到损坏,无法从他人脸上辨识出恐惧的情感,尽管如此,他在其他方面都表现出正常的智力。同样地,有边缘性人格障碍的人通常缺乏同理心。这种人的杏仁核低于平均值,缺乏能接受血清素这种神经传导物质的受器,因此眼眶前额叶皮质与颞叶皮质的神经活动相对来说较不活跃。32
华盛顿大学的神经学家扩大了我们对同理心回路的理解。他们发现大脑核心区域紧密关联着认知或视角转换的同理心,而认知同理心会刺激后扣带/前楔叶区域以及右方的颞顶叶交界处使其活动。举例来说,当我们想到自己有根指头被门夹到时,我们大脑的特定区域就会活化。但是,当我们想到这件事发生在别人身上时,同样的痛觉处理区域也会活化,其他的认知同理心热点被开启了。根据这个研究,面对我们自身的疼痛与其他人的疼痛,我们大脑的反应方式显示“同理心不牵涉自我与他人的完全融合”,而且同理心“使我们区别对他人的同理心回应和对我们自身疼痛的回应”。33
既是神经学家同时也是经济学家的保罗·扎克进一步充实这项说法。他的研究显示,催产素(母亲在哺乳时会分泌这种激素,但这种现象也会出现在男性身上)可以产生同理心的行动。催产素以其产生的社会效果著称。根据研究显示,终身维持同一伴侣的草原田鼠,在交配时产生的催产素要比其他不终身维持同一伴侣的田鼠来得多;阻断草原田鼠催产素的分泌,将使它们停止形成长期的伴侣关系。就人类来说,在特定的状况下,例如看到有人痛苦,此时会触发大脑分泌催产素,以及其他的神经传导物质血清素与多巴胺,促使我们进行社会投入。扎克把这种现象称为“人类催产素促成的同理心”(Human Oxytocin Mediated Empathy, HOME)回路。巨大的压力会阻断催产素分泌,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扎克认为,因为“要是我们自己都处于危难之中,怎么可能还将时间与资源用来帮助别人”。但在一般的状况下,“催产素可以产生同理心,促使我们做出符合道德的行为”。缺少催产素的人,较为自私自利,而且较无同理心。虽然催产素与同理心看似紧密关联,但有些科学家强调,两者间的关系是因环境与人而异,因此不要以为只要对着刻薄的上司喷几剂催产素就能马上让他变成富有同理心之人。34
那么,这些研究究竟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必须了解大脑内部产生同理心的复杂过程。一些现象,例如镜像神经元,只是广大“同理心回路”的一环,要联结其他人的心智,光凭镜像神经元是不够的。神经科学出现了明显的进展:在两个世代之前,我们还无法想象能把主导同理心的大脑特定部位标示出来。然而即使是现象,我们对这方面的认识仍处于初始阶段,还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才能了解同理心的运转,以及同理心与日常行为的关系。35拥有脑部扫描机器的我们,就像17世纪的天文学家一样,可以通过功能强大的望远镜看见新的星球,但无法完全了解这些星球的质地,或者这些星球为什么及如何运动。相信日后我们对有同理心之人会有更重大的发现。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A Study of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i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
作者: (美)赫伯特 A.西蒙(Herbert A.Simon)著;詹正茂译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简介:作为决策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西蒙最重要的作品便是这部《管理行为》。 决策制定的过程是组织和管理的核心内容,西蒙在此方面的研究具有开创性,并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本书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 “有限理性”和”满意解”——现实生活中的决策判断取决于有限理性,这种条件下,人们寻求的是满意解,而非最优解。 决策过程理论——组织内部的活动分为经常性(程序化决策)和非经常性(非程序化决策),而经常性活动具有共同的决策过程。作为决策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西蒙最重要的作品便是这部《管理行为》。 决策制定的过程是组织和管理的核心内容,西蒙在此方面的研究具有开创性,并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本书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 “有限理性”和”满意解”——现实生活中的决策判断取决于有限理性,这种条件下,人们寻求的是满意解,而非最优解。 决策过程理论——组织内部的活动分为经常性(程序化决策)和非经常性(非程序化决策),而经常性活动具有共同的决策过程。作为决策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西蒙最重要的作品便是这部《管理行为》。 决策制定的过程是组织和管理的核心内容,西蒙在此方面的研究具有开创性,并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本书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 “有限理性”和”满意解”——现实生活中的决策判断取决于有限理性,这种条件下,人们寻求的是满意解,而非最优解。 决策过程理论——组织内部的活动分为经常性(程序化决策)和非经常性(非程序化决策),而经常性活动具有共同的决策过程。作为决策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西蒙最重要的作品便是这部《管理行为》。 决策制定的过程是组织和管理的核心内容,西蒙在此方面的研究具有开创性,并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本书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 “有限理性”和”满意解”——现实生活中的决策判断取决于有限理性,这种条件下,人们寻求的是满意解,而非最优解。 决策过程理论——组织内部的活动分为经常性(程序化决策)和非经常性(非程序化决策),而经常性活动具有共同的决策过程。作为决策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西蒙最重要的作品便是这部《管理行为》。 决策制定的过程是组织和管理的核心内容,西蒙在此方面的研究具有开创性,并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本书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 “有限理性”和”满意解”——现实生活中的决策判断取决于有限理性,这种条件下,人们寻求的是满意解,而非最优解。 决策过程理论——组织内部的活动分为经常性(程序化决策)和非经常性(非程序化决策),而经常性活动具有共同的决策过程。
作者: 克里斯托弗·布曼
简介:
在各位手上的第二版中,我们进一步发展了基于身份的品牌管理的理念,基于行为的高度重要性,我们将品牌附件作为品牌管理的重要心理学目标。此外,我们还涉及了许多品牌管理领域的现实发展,例如数字时代的品牌管理,增加了电子商务和综合渠道营销的内容。在关于网上业务的新增章节中,我们用大篇幅介绍了社交媒体中基于身份的品牌管理。
由于近年来很多品牌成为盗版的牺牲品,我们特地增加了基于身份品牌保护的章节,它来源于不莱梅大学刚刚毕业的卡斯腾·凯勒(Carsten Keller)博士的博士论文,该论文由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很可惜只有德语版本。在《品牌管理:基于企业内部的视角(第2版 引进版)》的第二版中,我们还新增了国际品牌管理的章节,除此之外,我们还对第1版进行了大量的删减和改写,以使得《品牌管理:基于企业内部的视角(第2版 引进版)》更加通俗易懂。
Qualitative interviewing:the art of hearing data
作者: 赫伯特·J. 鲁宾(Herbert J. Rubin),艾琳·S. 鲁宾(Irene S. Rubin)著;卢晖临,连佳佳,李丁译
出版社: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
简介: 本书主要讨论了研究设计、访谈实施和数据分析三大部分,每一部分 都提出了相应的工作 目标和实施路径,并在讨论的过程中结合了大量的研究实例,详细明确地 提供了不同种类 的研究展开操作的可行办法。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本书,建议读者在阅读 的过程中,带着 自己的研究兴趣,根据书中提供的指导,具体思索并回答有关这一主题在 各仑阶段应解决 的问题。 本书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研究指南,既适合质性研究的初学者作为入 门的指导,也适合正 在做研究的学者作为研究参考。
20世纪外国文学史.第五卷,1970年至2000年的外国文学
作者: 吴元迈主编;钱善行,冯植生卷主编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4
简介: 概论 70年代以后各国文学的丰富多彩,总起来说,恰恰在于它的多元化状态,在于一批极有天赋,然而有着不同年龄和学识,不同文化背景、思想内涵和表现形式以及不同成就和影响的文人的集合,使一切思想、主义、流派都要在这个时代展现,所有卓尔不群的大家都要分享这方文学胜地的一角秀色。 首先是在欧洲,因为它拥有众多的文学大国和优秀作家。这30年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31名作家中,欧洲便有19位,占了近三分之二,可谓人才辈出。虽然欧洲各国的情况不同,文学面貌各异,甚或大相径庭,但它们在新时期、新形势下表现出的活力、创新和多元化倾向却十分相似。 七八十年代,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学取得了新进展,具有一股鲜活的生命力,各种题材、风格的作品大量涌现。同时,也涌现出众多驰名国内外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 1985年苏联开始改革,提出“社会进一步民主化”和“扩大公开性”的口号。1986年,苏联第八次作家代表大会在“民主化”和“公开性”原则下召开,会议气氛紧张,争论激烈,作家间的矛盾和分歧公开化。1987年,回归文学的“反思”冰山突现水面,直至1989年,反思和回归的热潮势头不改,大量被禁作品开禁,一时间洛阳纸贵,文学杂志订数猛增。这一年,主导苏联文坛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从作协章程中删除。1990年成为“索尔仁尼琴年”,各杂志纷纷抢登他的被禁作品。 1991年,风云突变,苏联党政高层领导斗争加剧,各种矛盾公开化,最终导致存在七十余年的社会主义苏联解体,苏联文学终成历史。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家由于多年来的积怨和不同政见被分成对垒的两军,口诛笔伐,俄罗斯文学迎来了寒冷的冬天。几年后,文学界的这场恶战始趋平息,各种作品百无禁忌、良莠不齐,纷纷破土而出。这些年,老作家们接连谢世,尚存者已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而那些40年代前后出生的作家逐渐成为文学中坚,一批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中青年作家则脱颖而出,给俄罗斯文学平添一抹春色。但是,俄罗斯文学欲现昔日的辉煌,恐怕还得“蓄芳待来年”。 东欧(现称中欧和东南欧)诸国与苏联情况基本相似。在波兰,哥穆尔卡任第一书记的两个五年计划(1961—1970)期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1970年底格但斯克等沿海城市工人罢工。70年代后期国家经济恶化,全国发生罢工浪潮,团结工会应运而生。1981年雅鲁泽尔斯基当选为党中央第一书记,同年12月波兰宣布进入战时状态,所有文艺团体被取消,所有出版机构被查封,文学刊物停刊,一些作家移居国外。1983年7月战时状态结束,1989年12月29日波兰人民共和国改国名为波兰共和国。 诗歌在波兰文学中占有特殊地位,尤其是诗人米沃什和女诗人希姆博尔斯卡获诺贝尔文学奖,更增添了波兰当代抒情诗的分量。除了这两位,享有盛誉的老一代诗人还有赫伯特和鲁热维奇,以及40年代出生的巴兰恰克和李普斯卡,青年一代则有奥哈拉派的希维特利茨基和波德夏德沃,古典化派的迪斯基和凯拉尔,先锋派的索斯诺夫斯基。几代诗人的诗歌特色、艺术形式和美学追求不尽相同,显示出波兰诗歌多元化的发展倾向。 匈牙利于1968年开始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导致国内政治生活的重大变化。1989年10月8日,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上该党终止工作,成立匈牙利社会党。同月,国会修改宪法,规定国家实行多党制,改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为匈牙利共和国。文学创作在七八十年代除了现实主义作家外,也出现了以沙布·玛克托、曼蒂·伊万为代表的“新月派”作家和以山陀·弗伦茨、弗耶什·安德烈为代表的“更新代”作家。 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导致苏联出兵,领导人杜布切克被捕;昆德拉等作家被开除出党,流亡国外;哈韦尔等被监禁;大批作家遭流放;由塞弗尔特任主席的作家协会被解散。1969年胡萨克任捷共中央总书记,1987年他辞去总书记职务,只任总统;1989年又辞去总统职务,同年捷联邦会议两院选举杜布切克为联邦议会主席,剧作家哈韦尔任总统。1993年元旦,捷克斯洛伐克分为两个独立国家:捷克和斯洛伐克。这一时期捷克斯洛伐克文学上最负盛名的是198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塞弗尔特和流亡国外、已入法国籍的作家米兰·昆德拉。 在法国,1959年至1963年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但工业的过度发展也激化了社会矛盾,社会不满情绪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暴露无遗。这次事件震撼了法国,创造了新的意识形态氛围,并导致1969年戴高乐退出政坛,结束了一个时代。因受语言学、符号学和心理分析学影响,彻底抛弃现实主义而盛极一时的新新小说派开始衰退,主将索莱尔斯于1980年与《如实》杂志彻底分道扬镳,法国文学进入一个没有中心、没有旗帜、没有流派的多元化时代,文学的通俗化趋向不可阻挡。 原为新小说派元老的西蒙,在法国文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于198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那匠心独运、“将诗人和画家的创作力与对时间的深刻意识结合在一起”的创作思想和风格,无疑使他成为这一时期自成一格的文学大师。1996年去世的杜拉斯,擅写日常生活,但她摈弃原先以情节取胜的传统方法,把故事写得扑朔迷离,人物的内心世界刻画得细腻感人。一部以少年时代初恋为背景的小说《情人》,缠绵悱恻,充满异国情调。同样拒绝传统的勒克莱齐奥,他的作品中无论是荒漠大海的神秘冒险,还是节奏疯狂的都市生活,细腻无序的描写总是与荒诞、寓意性的概括相依相融,传达出作者强烈的主观感受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图尼埃大器晚成,43岁时才发表处女作,但即获大奖,第二部作品《桤木王》又获龚古尔奖,确立了在法国文坛的地位。其作品想像丰富,荒诞离奇又充满象征,但它不同于通俗的科学幻想小说。莫迪亚诺的作品虚实相间,结构紧凑,语言明快。通过回忆与想像,以表现生活的不安定和潜伏的危险。 战后英国,其殖民帝国土崩瓦解,殖民地纷纷独立。1982年英军远征马尔维纳斯群岛,而1997年英国最后一个殖民地香港回归中国,最终结束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史。但“英语世界”的出现,使英语文学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个强大的话语体系。许多用英语写作的英联邦作家移民英国,亦给英国文学增添了绚丽的篇章。 这30年,英国文学前有卡内蒂(用德语写作)和戈尔丁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有出生于特立尼达与多巴哥的“后殖民”作家奈保尔再摘桂冠。这30年,英国文学既有老作家莱辛、戈尔丁、斯帕克、福尔斯宝刀不老、笔耕不辍,又有马丁·艾米斯、麦克尤恩、巴恩斯等中青年作家脱颖而出,日臻成熟;也有布鲁克纳、拜厄特、德拉布尔等女作家巾帼不让须眉,还有号称“移民三雄”的奈保尔、拉什迪、石黑一雄之崛起,蜚声国际文坛。这30年,英国诗坛异彩纷呈,新人辈出,多元化的开放格局造就了又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的西默斯·希尼。希尼的诗具有鲜明的民族背景和地方特色。品特的戏剧也成就斐然,1996年被授予终身成就奖,其戏剧作品语言幽默洗练,善用荒诞和比喻,富有象征意义。 德国在战后分裂成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一道柏林墙将一个民族分为东西两个阵营,走着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拆除,1990年两德统一,长达四十年的分裂历史终结。民主德国曾拥有三位一流作家,一位是女作家克丽斯塔·沃尔夫,她的《卡珊德拉》和《美狄亚》成功地运用丰富的艺术手段,集神话、象征、荒诞、梦幻于一体,将真实材料与文学虚构及主观评述有机结合,表达她对人类命运的忧虑;一位是剧作家海纳·米勒,他借助历史、神话和传说,并对戏剧表现形式进行创新,怪诞奇崛中显露出本人的悲剧史观和对历史与现实的批判;另一位是诗人布劳恩,他的创作简洁、冷静、客观,富于哲理,表现出对变革的渴望和对美好社会的追求。 联邦德国有两位作家海因利希·伯尔和君特·格拉斯获诺贝尔文学奖。伯尔“凭借他对时代的广阔视野,结合典型化的灵敏技巧,对复兴德国文学作出了贡献”;格拉斯“以他嬉戏般的黑色寓言描绘了被遗忘的历史面貌”。而以心理分析和细节描写著称的马丁·瓦尔泽,模糊了高雅文学和通俗文学界线的居斯金德,专写家庭生活、表现人的生存状态的女作家沃曼,通过荒诞手法表现现代人失落感的剧作家博托·施特劳斯等,都是当今德国文学的佼佼者。 奥地利1938年被纳粹德国吞并,后作为纳粹德国的一部分参加侵略战争。1955年,美、英、法、苏四方占领国同奥地利在维也纳签订条约,并于同年10月撤出占领军,接着奥国民议会宣布奥地利永久中立。文学上,奥地利属德语文学,约翰内斯·马梅尔与德国的海因茨·康萨利克同为当代德语文学中最负盛名的大众文学作家。托马斯·伯恩哈德和彼得·汉德克则是战后奥地利最重要的作家。前者主要写小说,主题常为疾病、灾难、死亡、绝望和沉沦;后者主要写剧本,创作完全违背传统戏剧,是一种没有情节、对白、场景、道具的“说话剧”。 瑞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战后政局相对稳定,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人均年收入居世界前列。文学创作分德语地区和法语地区,而用德语写作的作家更为著名,其中迪伦马特和弗里施成就最大,均为戏剧家和小说家。前者的戏剧立意鲜明,荒诞离奇而富哲理,情节完整而语言幽默;后者的剧作大多表现他对世界的悲观看法,并有极强的喻意性;小说多表现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和个性自我认同的困难。 意大利从战后至60年代初,经济发展较快,但后来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使它陷于困境。70年代后,实行严厉的经济紧缩政策,国民生产总值开始缓慢回升。80年代初又一次爆发的经济危机持续了三年多,高失业率激发了社会矛盾,恐怖活动猖獗,政府换班频仍,民众心理空前脆弱。文学失去了昔日新潮迭涌、流派更替的局面,一片凋零,70年代后始恢复元气,被先锋派否定的现实主义有所振兴,实验主义继续发展,风格独具的作品时时出现,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两次被意大利作家——蒙塔莱和达里奥·福摘取。前者的诗歌表达人的内心世界之细微感情,现代人那孤凄、哀婉、怨怼的情感隐逸于诗的艺术意象之中;后者集编剧、导演、演员、舞美设计于一身,发挥假面喜剧即兴表演的特长,兼收欧美现代派戏剧的各种表现手法,创造出独特的现代讽刺喜剧。埃科是位文艺批评家,也是位文学家,将自己对中世纪文化的研究成果融于结构繁复、情节曲折离奇的小说中。卡尔维诺在其寓言式小说中融现实、幻想、哲理为一体,凝重荒诞的哲理性内容和观念糅合在寓言故事所特有的神秘朦胧的美感之中。莫拉维亚遵循写实主义传统,以他那敏锐的观察力和精细入微的心理描写,力图揭示异化社会不同时期的特点和人们精神上的危机。 西班牙因佛朗哥的独裁统治而长期闭关自守。1975年佛朗哥去世,西班牙历史翻开新的一页。自80年代起,西班牙经济高速增长,文学也蓬勃发展。阿莱克桑德雷和塞拉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者继承西班牙抒情诗传统和现代派手法,对人生、爱情和当今社会的境况作了深刻探求和描述;后者的小说多围绕死亡主题展开,“以富有节制的同情”和充满悲剧色彩的叙事“勾画了孤独无助者令人心颤的形象”。 . 葡萄牙的情况与西班牙有些相似,独裁者萨拉查在葡统治长达37年,1970年病逝,1974年一些中下级军官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法西斯政权。但直到1986年苏亚雷斯当选总统,葡萄牙近六十年才有了第一位文人总统。同样,葡萄牙这时有了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萨拉马戈,他是位关心世界命运的作家,作品新颖独特,充满隐喻和暗示,“通过由想像、同情和讽刺所维系的寓言故事,不断使我们对虚幻的现实有所了解”。 北欧的丹麦、瑞典、挪威、冰岛和芬兰,在60年代经济发展较快,但70年代随着经济危机和失业人数增加,各国经济发展趋于不平衡。瑞典经济发达,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前列,教育高度普及,以现代福利国家著称。挪威的石油出口为其带来巨额利润。丹麦女作家索若普为丹麦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以写妇女的日常生活著称。瑞典1974年有两位作家雍松和马丁逊同获诺贝尔文学奖,但都在70年代去世。目前重要的作家为诗人古斯塔夫松和女小说家埃克曼。冰岛当前最受欢迎的作家为描写渔民生活、反映冰岛巨变的卡拉松和描绘一个充满欢笑和痛苦的世界的古德蒙德松。芬兰的阿尔波·鲁特为芬兰著名工人作家,以写赫尔辛基工人生活著称。 希腊有着古老的历史和文化。1946年爆发内战,1949年希共在内战中失败,大资产阶级掌权,实行白色恐怖。1967年军人发动政变,建立独裁政府。1973年废黜国王,确立共和制,1974年军政府垮台。1981年议会选举,由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执政,并进行了一些社会改革。1979年诗人埃里蒂斯因“从源远流长的希腊传统中汲取营养,以强烈的感情和敏锐的智力显示了现代人为争取自由、从事创造性活动而进行的斗争”获诺贝尔文学奖。 70年代后,亚洲各国经济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和繁荣,但地区冲突和民族矛盾不断:两伊战争,苏联入侵阿富汗,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美伊战争,中东战争,印巴冲突,巴以冲突,印尼和菲律宾的民族冲突……影响着亚洲地区的安宁,但总的趋势仍是和平与发展。与此同时,各国的文学也有新的发展,新的成就。 日本文学在七八十年代错综复杂的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影响下,出现了许多文学派别,如“透明族”、“作为人派”和“内向派”等。这些文学派别的出现,一方面打破了日本文学的旧传统;另一方面由于作家的反常心理和对现实的不满,他们的作品中弥漫着种种迷惘、失落、空虚和颓废情绪。到90年代,这些风行一时的派别渐渐风流云散,呈现出多样化和多元化的态势。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在接受萨特存在主义哲学和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同时,将自己的美学观和政治观融入日本传统美学中,“在荒诞的故事叙述里蕴藏诗意的抒情,对人类危机进行深刻的思考”,开创了另一番天地。 印度文学自50年代起盛行的区域文学流派长盛不衰,一直延续至七八十年代。作家们以边缘小村落为依托,以现实主义手法描写那里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90年代后,一批用英语写作的中青年作家,如阿鲁·乔希、维克拉姆·赛德、乌帕马尼亚·查特吉和女作家阿妮塔·德赛、帕拉蒂·穆克吉等脱颖而出,他们的作品集荒诞与现实于一身,将富有特色的印度文化传播至世界。 以色列自1948年建国后,大批犹太作家从世界各地聚集到此,共同创造了以色列文学的繁荣。五六十年代以色列文学的领军人物是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阿格农,他“从犹太人民的生活汲取主题”,创造出“深刻而具特色的叙事艺术”。60年代至90年代“大屠杀文学”的代表人物为阿佩费尔德,他的《为每桩罪恶》和《不朽的巴特法斯》为这一流派的代表作;而奥兹则是“新浪潮文学”的代表人物,主张以色列与巴基斯坦和平共处,共同发展。 非洲各国均属发展中国家,经济相对不发达,政局动荡;文学创作水平参差不齐,用阿拉伯语、法语和英语创作的国家和地区,水平相对较高。埃及是文明古国,1953年废除君主制,成立共和国。1967年中东战争,以色列占领西奈半岛。1978年,埃及通过谈判收回西奈半岛。1981年萨达特遭暗杀,穆巴拉克当选总统至今。他执政后,坚决镇压国内极端势力,继续对外开放,吸引外资,注意改善人民生活。1988年,小说家马哈福兹因“开创了全人类都能欣赏的阿拉伯语言叙述艺术”而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继承阿拉伯文学传统,又吸收和运用象征、隐喻、荒诞、非理性等现代手法,丰富小说的表现力。 尼日利亚原为英国殖民地,1960年宣布独立。独立后,历史遗留的地区和部落矛盾日趋尖锐,政局不稳,军事政变不断,至1985年共有六次大的政变,70年代成为非洲最大的产油国。1986年,剧作家兼诗人、小说家的索因卡,因“以广阔的文化视野和诗情横溢的联想影响当代戏剧”而获诺贝尔文学奖。他将西方现代戏剧艺术与约鲁巴传统艺术相结合,对发展非洲民族戏剧作出了重大贡献。 南非1961年退出英联邦,成立南非共和国,是非洲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但南非当局长期以来推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黑人领袖曼德拉被判终身监禁,直至国大党在大选中获胜。1991年,白人女作家戈迪默获诺贝尔文学奖。 澳大利亚在战后鼓励英国和欧洲人移民,1966年对移民政策进行修改,允许亚洲人移民定居,至80年代后移民人数激增,使澳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同时亦滋生丰富的物质生活和人的意识危机的矛盾。1973年小说家怀特因“以史诗般的气概和刻画人物心理的叙述艺术,把一个新的大陆介绍到文学领域中来”而获诺贝尔文学奖。一部《风暴眼》集中体现了他的创作思想和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写出了当代澳大利亚人的自私、冷漠、苦闷和迷茫。彼得·凯里是“新小说派”的代表人物,他的长篇小说《奥斯卡和露辛达》是受到赞誉最多的作品,而伊丽莎白·乔利是女作家中的佼佼者,她发表的许多表现女性问题的作品具有独特而强烈的艺术效果。 战后加拿大经济迅速发展,70年代以来魁北克省独立运动曾多次造成国内政治危机,1982年以《宪法法案》替代《英属北美法》,并确定法语和英语同为加拿大国语。加拿大民族文学在欧洲文学和美国文学的影响下逐渐走向成熟。加拿大英语文学的代表人物是女作家阿特伍德,其长篇小说《使女的故事》描写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荒诞世界,被认为是女权主义的代表作。她的诗歌一反传统诗的形式,以出人意料的意象,不带感情色彩的风格,表达对妇女生存状况的关注。迈克尔·翁达杰的作品带有鲜明的多元化特色,一部《英国病人》轰动国际文坛,被认为是“反殖民小说的经典之作”。法语文学作家安娜·埃贝尔以《卡穆拉斯卡》被称为“当代最优秀的魁北克小说家”。 美国在60年代由于卷入印度支那战争,并将越战升级,导致经济衰退。1969年上台的尼克松,1974年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美国爆发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1975年福特政府正式宣布侵越战争结束,但美苏两国军备竞赛越演越烈。1991年底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布什和克林顿政府一面试图加强地区间经济合作,一面充当“世界警察”角色,参加海湾战争,长期从各方面制裁伊拉克,在科索沃问题上干涉别国内政,大肆轰炸南斯拉夫。 这30年,美国文学如同它的政治经济一样变化很大。索尔·贝娄和辛格获诺贝尔文学奖,加上马拉默德和菲利普·罗思,使美国文学拥有四位犹太裔现实主义大作家。他们的构思、笔法、风格、哲理思辩各不相同,但都将细致描写与象征、荒诞、寓意性的概括相交融,创造出新的语境,来表现美国的社会现实和犹太人的生存与命运,传达出作者强烈的主观感受和对现实的悲剧性理解。 同样,厄普代克也以描写细腻和现象主义方法见长,在他创作中占主要地位的“兔子系列”,花费40年时间描写了不同时期的中产阶级人物兔子哈利·安斯特朗姆的经历和命运,反映出近半个世纪来美国社会的变迁。常以暴力和爱情为创作主题的女作家欧茨,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基础上兼容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神秘主义等手法,表现了美国现代社会的复杂生活。卡弗和贝迪描写平凡生活的细节,塑造各具特色的小人物形象,揭示世界和人生的荒诞,成为“简约派”的代表人物。 变化迅速的美国生活,促使一些作家用更新颖的手法来反映现实。巴思的作品充分体现了他丰富的想像力和实验精神;冯内古特发展了60年代海勒式的“黑色幽默”,融科学幻想为一体,对美国社会进行漫画式的嘲讽和揭露;多克托罗对历史和历史人物进行虚构和编织,用匪夷所思的情节来怀疑美国社会繁荣安定的真实性。品钦在“黑色幽默”的基础上,以各种艰深的现代科学、杂乱无章的内容和晦涩难懂的语言来营造当代社会令人窒息的梦魇般气氛。 这30年,美国文学亮点中的亮点,是黑人文学的崛起并融入美国的主体文学。哈里的《根》、艾丽斯·沃克的《紫颜色》、伊什梅尔·里德的《物神》、怀特曼的《隐匿地》以及桂冠诗人丽塔·多弗,剧作家奥古斯特·威尔逊等,都以他们出色的作品和非凡的才能让人刮目相看。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199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更为美国文学增添了一抹亮色,而1987年俄罗斯侨民诗人布罗茨基获诺贝尔文学奖,则多多少少让俄罗斯感到几分沮丧和无奈。 60年代西班牙语美洲文学曾发生震惊世界的“文学爆炸”,造就了一批蜚声世界的作家,魔幻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社会现实主义等流派纷呈。70年代以后文坛继续火爆,但进入80年代后,随着聂鲁达、阿斯图里亚斯、卡彭铁尔、科塔萨尔、博尔赫斯、鲁尔福、纪廉等一批文学大家凋谢,文坛显得静寂许多,到了90年代才又奇迹般复苏,新老作家开始新一轮冲刺。智利的巴勃罗·聂鲁达、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墨西哥的奥克塔维奥·帕斯分别获诺贝尔文学奖,他们的获奖既是西班牙语美洲文学的骄傲,亦给诺贝尔文学奖本身增添了荣光。而阿根廷的博尔赫斯虽未获此奖,但其声名并不在他们之下。他的散文和短篇小说清冽、明丽、灵动、精致,令人神醉情驰。在富恩特斯笔下,现实主义又重放异彩,历史和幻想在作品中交融、升华,组成一首深沉悠远的命运交响曲。擅长结构现实主义的巴尔加斯·略萨,个人情爱和社会重大政治问题在他的作品中交相辉映。卡夫雷拉·因方特注重文学语言的探索与革新,浪漫主义的爱情悲剧被他注入了独特的古巴音乐舞蹈成分。 文学爆炸后,拉美一些青年作家脱颖而出。智利的伊莎贝尔·阿连德以一部充满魔幻的《幽灵之家》演绎了一个国家风云变幻的历史;她的同胞埃德华兹1999年获塞万提斯奖,成为该奖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得主;墨西哥的劳拉·埃斯基韦尔的《沸腾》让读者再次领略魔幻现实主义的魔力;阿根廷的普伊格的《蜘蛛女之吻》重新回到情节,并在小说的叙事结构中融入影视手段;多产的波塞在《天堂之狗》中用艰深而高品位的文字展示落后的文明与文明的落后。 巴西受葡萄牙殖民统治长达三百余年。1964年军人发动政变,建立军人政权,三届政府均实行独裁统治。1979年文人政府掌权,实行大赦,改革经济,逐渐使巴西经济实力居拉美首位。特雷维桑为巴西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家,其作品短小凝练,意韵深刻。特莱斯为巴西最负盛名的女作家,文笔细腻流畅,揭露社会风气的败坏和道德的沦丧。卡布拉尔是战后巴西诗坛声望最高的诗人,具岩石般冷峻的抒情色彩。而维里西莫则是当今巴西最知名的专栏作家。 位于东加勒比海小安的列斯群岛上的一个小点——圣卢西亚,面积616平方公里,人口不足十三万,其中黑人占九成,原为英国殖民地,1979年始获独立,经济以香蕉种植业为主。如今小小的岛国,因它的子民沃尔科特获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而闻名遐迩。瑞典文学院称他的叙事长诗《奥梅罗斯》是“一部恢宏的加勒比史诗”,称他的大量诗作“散发出光和热,并深具历史眼光,是多元文化作用下的产物”。 20世纪末的世界文学乃至文化已显现出多元化和通俗化走向,这种走向也许还将对21世纪的世界文学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6年4月
简介:本书为读者介绍了金融风险管理中经常使用的数学工具与技巧,涵盖了风险管理所需要的线性代数与概率论基础、投资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VaR理论、时间序列分析、金融衍生品定价的基础理论、最大似然估计法、Delta方法、假设检验及极值理论等。本书将金融风险理论与严谨的数学推导紧密结合,能够使读者更为详细地对金融风险模型进行了解,不仅适用于金融从业者,而且也适用于研究相关模型的学者。
Eros and civilization: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
作者: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著;黄勇,薛民译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简介:本书共分两篇,十一章,内容包括:精神分析的暗流、被压抑个体的起源(个体发生)、压抑性文明的起源(属系发生)、现存现实原则的历史局限、幻想与乌托邦等。 赫伯特·马尔库塞(1898-1979),法兰克福学派左翼主要代表,被西誉为“新左派哲学家”。本书是其主要著作之一,声称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来“补充”马克思主义。 西方今天文明已发展到极点,然而文明进步的加速也伴随着不自由的加剧。集中营、大屠杀、世界大战和核武器都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人对人最有效的统治和摧残恰恰发生在人类的物质和精神成就高度发达到仿佛能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的世界的时刻。可见,高度文明的昂贵代价是人的不自由和对生命本能、对自我升华了的性欲-爱与的压抑。所以,反抗现代西方文明首先必须消除对人的本性的压抑,解放爱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