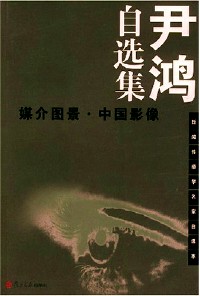共找到 5 项 “尹鸿著” 相关结果
- 全部分类
- 全部
- 文学
- 历史
- 哲学/宗教
- 法律
- 政治/社会
- 医学
- 教育/心理学
- 艺术/传媒
- 研究生考试
- 资格认证考试
- 公开课
- 语言
- 经济金融
- 管理学
- IT/计算机
- 自然科学
- 工学/工程
- 体育
- 行业资料
- 音乐
- 汽车机械制造
- 文档模板
- 创业
- 农学
- 生活
- 数据库教程
- 民族
作者: 尹鸿著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简介:本书为广播影视专业本科学生“影视艺术概论”核心课程的基本教材,同时作为高校开设“电影艺术导论”、“电影艺术鉴赏”等公共选修课、通识课的教材。本书主要分为上下两编,共15章。上编为学生理解电影艺术、认识电影艺术、甚至实践电影艺术提供基本的知识、理念和技巧。下编一方面为学生提供电影发展的历史线索和主要电影思潮、流派的知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帮助学生通过对电影历史上的名家名片名事能够更具体地理解电影艺术和体验电影艺术的魅力。全书突出专业性、易读性、实用性、前沿性、风格性与文献性,每个章节都有关键词提示、小结、小贴示、讨论与练习等内容,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教材和核心内容。全书还包括:百年电影大事记、电影主要名词解释、200部名片推荐、推荐阅读书目等附录。一书在手,长期受用。作者尹鸿,现任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兼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主要著作有《尹鸿自选集:媒介图景?中国影像》、《尹鸿影视时评》、《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影视文化》、《镜像阅读》、等10多种;主编“新闻与传播英文原版系列教材”、“欧美影视传播主流教材译丛”,“传媒产业与管理译从”;在国内外发表电影电视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200多篇,在各种媒介发表文化、影视批评文章200多篇,
作者: 尹鸿著
出版社:北京出版社,1998
简介: 世纪转折时期的 中国影视文化 跨世纪青年学者文库 90年代不仅是公元纪年意义上的世纪转折时 期,也是百年求索以后的中国社会重大的世纪转折 时期。本书阐释了处在这一特定时期的各种影视文 化思潮、形态、类型、创作现象以及具有个案价值 的影视文本,描述了90年代中国影视文化如何审慎 而艰难地确定自己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策略。从现实 主义到现代主义直到后现代主义,从谢晋到张艺谋 等第五代导演直到新生代艺术家,从《渴望》《北京 人在纽约》等流行电视剧到《心香》《民警故事》等 “作者电影”,都进入了本书的批评视野;当代中国 影视文化的历史局限、历史症候和历史的得天独厚, 均在本书中得到了反省性的解读。本书作为一部历 史备忘录,不仅记载了90年代喧哗与悸动的中国影 视文化风云,也表达了对走向新世纪的中国影视文 化的预期和希冀。
作者: 尹鸿著
出版社:海天出版社,1998
简介: 在都市的喧嚣和熙攘中,在纷扰的车流与人潮中,您是否还能闭上眼,享受一刻宁静的思? 诗人说,够了,让我享有缄默!在时尚扑面的嘈杂中,在斑驳陆离的霓虹的频闪中,哪里是可以独步的林中路?哲人说,林中氤氲的雾霭中,总有隐约的诗意漾出。我们活着……我们如此辛劳地奔行于这个世界……我们总得活着,焦灼、烦忙、疲惫而又倦怠……然而我们的婴儿依然充满激情地啼叫着坠地,我们的婆母依然为孩子们腌制过冬的咸菜……昨夜,我如此困顿、疲累、愤懑,乃至沮丧万分。而清晨,我擦一把脸,依然得驱车前行,匆匆地赶路。车窗外,偶尔一瞥,路旁的野茴条正恣意而蓬勃。
作者: 尹鸿著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简介: 尹鸿访谈录 尹鸿,作为近些年来活跃在学术讲坛上的一位学者,已有不少的报道引用展示他的学术见解、学术观点。而对于学术品格、学术立场这些对于学者来说应该最为宝贵的品质却鲜有关注。特别是对于像尹鸿这样一批年纪很轻就取得很高学术地位的青年学者而言,关注他们如何应对物质世界的诱惑、如何保持学术品格这一更深层面的论题可能尤为必要。在尹鸿一本著作的后记中偶然发现一句话:“用生命贯穿学术、用学术充实生命”,非常意外地给我提供了一个理解这一问题的现实文本和某些质感元素。由此,诞生了“生命学术与学术生命”的访谈主题。 尹鸿坚持认为自己是一名从事文化研究、影视艺术研究和媒介批评的“人文学者”,尽管这些年来他似乎也从事过一些关于影视产业、传媒政策等方面的实证性研究,因而,似乎更多地被人们注解为“一半人文科学,一半社会科学”。其实,从一开始,尹鸿就是一个人文研究者。他的学术生涯分为前后两个部分,起初做了10年的文学研究,研究过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西比较文学、美学、悲剧;接下来进行了10年的影视传播研究,追踪了十多年的中国当代电影,并对当代中国的电视媒介形态展开过深入研究,同时,还试图在媒介批评研究方面有所突破;这些共同构成了他学术生涯的另一半,而且为他注入了某些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人文视野与科学方法的某种融合,也许共同造就了现在的尹鸿。 问:您20多年的学术生涯,大概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划分的原因是什么? 尹:第一个阶段可以说是学习阶段,我是“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高考的首届大学生,那时的大学阶段正处于新旧交替时代,接受过很多无用的东西,同时,也接受了很多西方的观念。新旧交替、中西差异对我的冲击很多,但是也成为了一个很好的积累过程,给我提供一个思考的机会。接受任何新东西都是在与旧东西的比较中完成的,所以后来发现许多学术问题都经过了自己认真的比较和思考,〖JP2〗而不完全是从书本中读来的。在四川大学中文系的本科以及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学习,使我对中国现当代历史、现代西方文化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和了解。 后来考上博士,来到北京,当时正值美学研究的高峰期,于是学了很多哲学,开始对悲剧产生兴趣,通过对悲剧的研究又使我对中西文化有了进一步认识。博士论文是研究弗洛伊德与中国现代文学,受到当时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当时主要考虑到心理学思潮与现代文学的发展有深刻的联系,而此前这个领域的研究还相当缺乏。这段时间,自己还参加了一个项目,与人合作出版了一部国内最完整的研究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与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著作。这些研究,对于我在一个中西文化背景下研究文化,在大文化背景下研究文学艺术的思维方法和知识构成产生了长远的影响。我后来的研究思路与这段工作有密切联系。 问:您的研究好像总是将已有的理论和具体的文本创作,或者说具体的媒介现象联结起来,显示出一种非常“务实”的学术特色,但您是否会担心这样的批评,比方说对您始终未能建构起具有容纳力、概括性的理论体系的批评? 尹:实际上,我从来没有进行过空洞的理论研究,都是将理论与具体的文化现象结合起来的,也可能是我没有那么形而上的抽象能力。但这种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我研究成果的鲜活性,因此使我的研究更易被接受,更易被传播。 也许会有人批评我没有建构过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确实是这样的。主要是我觉得框架的东西不是我追求的东西,他容易束缚住人们的想象力,容易落入削足适履的教条之中。当然,也可能是我的研究还没有达到那样的抽象水平,所以目前还不能建构起一个更完整的能够包容万象的理论。 对我来讲,我不追求纯理论的原创性,我觉得我在学术上的建树可能更多是对历史进程、文化现象的分析,我的原创风格可能体现在这方面,而不是体现在理论建构和研究方法上的,将来也不大可能转向纯理论,因为我更关注研究对象的整个发生、发展过程。 问:如何评判您的这一学术风格? 尹:这样做可能使我的研究比较兼收并蓄,不走极端,坏处是可能不够深刻,因为我很少将一种学说、一种理论推向极端,常常难以达到一种由于片面带来的深刻,因此,很少能够给人振聋发聩的印象;但是因为比较客观,不走极端,比较开放、多元,所以我的学术观点可接受性比较强,一般来说引起强烈反对的比较少。 问:第一个阶段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方面,后来有什么变化呢? 尹: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我刚刚在北师大获得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博士学位。 当时的文学研究经过前一段的喧哗正处在一种比较困惑的时期。与此同时,媒介研究开始发展起来,但是当时的人文学者对这个领域还比较陌生。我在北师大,离电影学院、电影资料馆都很近,起初是当票友,后来发现从事媒介研究的人很少,但媒介对于社会的作用却日益增大,而且在20世纪后半期以来,影视媒介在西方可以说是许多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实验场,这些因素加上我个人对于电影这种视听语言本身的喜好,都促使我将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影视文化,以至于后来完全放弃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而进入了影视研究的新领域,并参与了中国高校第一个电影学博士点的创建。 我做电影研究以后,也没有走上纯理论的道路,依旧是用理论来分析当代中国影视文化。除了当代中国影视文化外,也有一些延伸,比方说中国电影史、外国电影史、媒介文化研究等,这些是为我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参照和背景。 电影与文学不同,它是一种媒介,不仅与艺术而且与技术、工业、市场、政治、流行文化等都有更加密切的联系,因而在电影研究中我意识到艺术和美学的方法已经不够用了,必须要积累一些传播学的方法、传播学的理论,从艺术背景到传播背景,于是我指导的研究生方向确定为影视文化传播而脱离了单纯的艺术研究。 正是有了这种转移,我才可能将电影的研究扩大到对电视媒介的研究。特别是我来到清华,进入传 播学研究领域以后,变化更加明显。虽然我关注的重点仍然是电影和电视,但研究过程中,更多的借助传播学背景而不是先前的艺术背景了,比方说我以前研究电视,主要是电视剧,现在更多的集中在电视节目形态、媒介产业化等方面,加入了更多的政治经济学的背景,即便是研究电影,与以往也有所不同,更关注电影工业、电影政策等方面的内容。 问:回头看这二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作为一个学者,对您自身而言有哪些收获?对于社会而言,或者说对于您所从事的这一领域以及相关层面,有哪些贡献?能否对您的学术成果进行一个自我梳理? 尹:在从事现代文学研究时,我当时研究过西方现代主义的几乎所有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在研究的广度、丰富性及相互关系的复杂性方面都达到了一定水准。另外,我的博士论文《弗洛伊德主义与中国20世纪文学》,就这一项目来说,我不仅仅是找到一种资料上的对应关系,主要是从观念上挖掘了弗洛伊德主义对中国20世纪文学的影响,我个人认为这一研究还是达到较高水准的。到现在为止,这些研究还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在台湾、香港地区以及国外一些大学,这些著作还被列入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文献,他们有人甚至不知道我是研究电影的,但知道我搞过比较文学研究,这些资料在中国来说也是比较完整的。 另外,我还研究过悲剧哲学和艺术,对于中西方悲剧艺术、悲剧意识做过比较系统的研究,特别是对悲剧与人生、与人生哲学的研究,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当然,我最主要的研究还是集中在“当代中国影视文化”。大概分为几个部分。一个方面是对当代中国影视文化与当代中国复杂的现实关系的研究,在这方面也提出过一些比较有影响的观点,比方对“一仆三主”的社会语境的分析,对主旋律的“伦理泛情化”、“家国主义”策略的分析,对商业娱乐电影与中国国情之间的文化冲突的分析,对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态度的分析,对中国电影新生代体验风格的分析,对好莱坞全球化策略的分析,对中国电影的政治伦理情节剧模式的分析,对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的分析,对中国电视文化多元性的论述以及对一些具体的影视形态和模式如“真人秀”节目的研究,应该说都做出了一些原创性的成果。我想,在中国复杂的社会历史语境之下把握中国影视文化的规律、走向和它的特质,是我的研究对于当代中国电影最有影响的方面。此外,我还做过一些中外影视文化比较研究,这些研究都是试图将中国媒介置于全球化这一大背景下,分析西方媒介文化如何被中国吸收、使用,以及这种吸收的合理性、合法性。也提出和阐述了市场、产业与文化的关系,引入了政治经济学的一些概念,具体分析了很多中国媒介经济、媒介管理等方面的现实问题。 此外,在近10年中,我还是一个比较活跃的影视评论者,是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参与影视评论的,形成了我作为一个批评者的位置。我对20世纪90年代许多重要电、电视文本和文化现象,都发表过批评意见,许多批评还产生过一些影响,作为当时影视文化的一种“文献性纪录”被保留下来。我做过多年的“年度电影备忘”和年度电视综论,对当年度电影电视的趋势、发展格局、走向作批评研究。因为一直保持着这样一种对当代中国电影的动态研究,而且是比较完整的动态研究,这不仅对于人们了解、研究当代中国电影会提供比较大的帮助,而且对于构建一种批评的氛围也起到了作用。 . 还有一方面,就是媒介文化理论。可能是我个人受批判学派影响比较深的缘故,我始终想建构一种媒介批判的视野、方法和立场,希望在市场、政府与人文传统之间,保持一种大众文化的开放性,保持文化的一个公共空间、公益领域,为文化提供一种伦理根据、一种价值尺度。1995年我从加拿大做访问学者回国以后,就提出了“媒介生态环境”的概念,目的是希望能够在中国建立起一个健康、公正的媒介文化批判体系。但是,这个工作至今仍没有完成。目前,我还在继续这个工作,随着媒介的市场化和功利化程度提高,媒介批评的重要性将更加显示出来,我希望我能够在这方面有一些理论的建树。 治学之道千千万,学问人生各不同。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将学问做得有格有致,可能是学者的一种无意识的追求。 问: “整合”和“原创”对于一个学者而言,分别意味着什么?您个体的经历如何? 尹:我理解,所有的原创都是在整合的基础之上的,没有整合的原创是自以为是的胡说八道。对于学术来讲有这么一个过程,一定阶段的整合研究是必要的。但关键是,可能目前我们会有些人为了整合而整合,将国外的搬过来沽名钓誉。其实,对于中国现阶段的传播学研究而言,从国外引进的过程已经达到一定的规模,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扎下去,将这些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从而在整合的基础上产生原创。 对于我个人而言,我的原创性体现在我阐释方面的原创性,也就是说我吸收别人的理论,但又不会被束缚,也不会将之推向极端,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对中国现当代历史、文化背景的认识来考察我的对象,提供一些原创的阐释方法、阐释视角。 问:在研究过程中您是如何平衡“感性”与“理性”的?个体经验在您治学过程中是个什么位置?应该处于什么位置? 尹:我始终怀疑“为学术而学术”。我一直强调做学术是我体验生命的一种方式,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我研究的前提是,研究对象能唤起我的热情,也就是说能唤起我的关怀。没有热情我是一般不会去做。 但是在研究过程中,我力求做到客观,从多方面来考察,因此研究的成果是相对客观的,是为人们接受的。但是在对研究成果的表述上,我不能,也不愿回避表达自己的主观性,因为这是我对生活表态的一种方式,如果不能这样,我就没有一种表达生活的可能性了。在表述时,我会带着自己的体验来表述,因此,我的教风、文风可能容易给人留下一种个性化的印象。而实际上我的研究方法、研究事实是客观的。当然,这样研究可能使一部分人因为接受我的风格个性而接受我的研究,甚至被这种表述的修辞所征服而放弃了理性的考察,也可能使另外一些人因为不喜欢我的文风而拒绝我的研究。但是,我想,学术研究也需要不同的个性、热情,才能形成它的博大和丰富,世界上没有所谓绝对的公正、客观,但是正因为有各种差异的呈现,我们才能够得到一个相对客观的可能性。个性的多样性是学术的多元化的前提。 问:其实您非常坚持地认为自己是一个人文学者,一个人文学者进行社科研究的优势在哪里?劣势在哪里? 尹: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人文学者。刚来清华最不适应的就是,时刻有一种被迫要变成社科学者的危机或压力。 人文学者的优势在于背后依靠的人文传统,人文传统带来的一种共同情感,这种东西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劣势在于,可操作性不够,比方说得出一个判断,可是这个判断如何变成一些可操作性的步骤或可操作的元素去实现它就很难。这与人文学者比较少或者没有接受过社科训练有关。 所以,我现在试图将这两种方法和态度作融合,虽然我知道这两者的立场和方法以及传统都很不一样,但是我认为也可以找到一些共同平台。中国的传媒研究需要这种方法论的综合和平衡。 问:如何做出学术研究的“品位”、“品质”、“品格”来? 尹:先说“品位”,就是不要媚俗,不要人云亦云。“位”首先牵扯到如何做人,如何给自己定位,如何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关系到用什么态度做学问,如果很俗气,他的学问不可能有品位。 “品质”的要求就是要有一定的方法论基础,做出来的东西要有质量,质量来自你的知识积累、你对方法论的认识和把握。也就是说,要有一定的专业素质,这是保证品质的前提。 “品格”就是要有一种思想,思想的前提是不仅要对对象有了解有研究,而且有判断、有阐释,有前瞻的东西去引导它。做出的判断要有影响,能够感染人、影响人。成为“格”的东西,一定是对自己研究的领域、对他人有影响的东西。这可能是一种比较高的境界。 非常流行的一句话“无知者无畏”,很想知道“有知者是否有畏”,作为当今学者,面对政治、面对市场,是否有所畏惧?是否应该畏惧?是否能够真的做到无所畏惧?一个学者,应以怎样的态度、怎样的立场、怎样的行动来确立自己的学术品格、建构自己的学术准则,从而做到无愧学术、无愧社会。关注学者的“畏”与“无畏”可能会找到解读的依据。 问:您觉得评判一个学者学术地位的标准应该是什么? 尹:标准?标准总是与一定的数量和一定的质量相关。质量在某种程度上源自一定的数量,因为没有一定的数量,本身就会限制你的研究的深度、广度,从而会影响到研究质量。 但现在可能由于量化指标对于学术评判要求越来越高,往往流于另一种倾向,追求数量而不追求质量,大家都在一个平面上抄来抄去,没有创新元素。 按我的理解,判断一个学者的标准可能有几个方面:一方面是他在自己的学科领域产生的影响力,具有一种公认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不在于他在学术机构有一个类似“会长”或“副会长”的职位,而是指他的学术理论的被引用率,被正面的引用率,以及他的学术观点、学术方法对他人的影响力。 问:除了在自己学科领域的影响力,是否还包括社会影响力? 除了在自己学科领域具有公认的影响力,另一个判断学者地位的标准,我认为,还在于他在所从事的专业领域取得的成就高低,或者说他在理论上、方法上、概念上、资料上所具有的公认的价值和原创性或者开创性。 问:您对您目前获得的这样高的学术地位是怎样看的?从质量、数量两方面来反观您的学术成果您的自我评价是什么? 尹:我目前的学术地位,还不能说很高。我能得到目前的学术地位,一方面在于我确实认真地做过一些研究,不论数量、质量方面都还不算差。特别是我对于当代中国影视文化的研究,我想我目前取得的成果还是得到国内外相关学术界的承认的。我在电视方面的研究,相对来说,体系性的东西不是很多,但在我已做过的包括电视品牌研究、西方节目形态、电视剧研究等方面,就项目本身而言,也还算处于前沿状态。这些东西给我提供了学术地位的基础。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之所以有这个位置,与这个学科领域整个的学术水准还不是很高有关,虽然我们有很多优秀的学者,但总体来讲,整个学科的学术水准还不是很高。因此,只要认真做过一些研究,特别是所做的工作又有些突破与创新,相对来说,获得一定位置比较容易,因为我们这个领域的学术规范、学术传统都还没有完全形成,不像在传统学科中,要想很年轻就获得一个很高的学术地位非常不容易。可以说,我选择了一个强手不那么多的领域来做这件事。 但换句话说,也说明这件事有一定难度,之所以大家不去做,是因为没有积累、没有传统,这些增加了在这一领域做出成就的难度,但是一旦做出成就,就很容易获得地位,我觉得我对自己的估价基本就是这样。实际上做的事情还很不够。 问:很想听听您对“学以致用”、“学术独立”的理解?特别是从您个人经历、个人立场的角度。 尹: “学以致用”,从我的立场来讲,它不是唯一的学术追求,但它是一种有价值的学术追求。学,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用。实际上我们很多的“学”,都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的。但是“学以致用”并不是急功近利,“学”要比“用”有前瞻性、引导性,“学”始终要让“用”在一个更开阔的空间上发展。 问:自身的经历呢? 尹:我可能属于比较“学以致用”吧,一方面,因为我是老师,直接将自己的“学”用于教学生;另一方面,与媒介接触比较多,大量的交流、评奖等活动,通过影响媒介从业人员来达到“用”的目的;还有就是通过大众媒体来间接地影响公众,因为我较多地在大众传媒上发表意见,这些东西可能会对公众的媒介认识产生一定影响。 问:学者该如何保持学术的独立? 尹:学术独立其实关键在于自己的品质,学术独立的核心是说真话。现在的“学术独立”虽然越来越困难,就像你刚才说的学术与市场、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日趋复杂,但这是一个尺度问题。其实任何一个人生活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可能会有妥协,但这个妥协还是有个“度”,有个底线问题,你想得到支持、得到发言空间的可能性,就像人与人交流,更何况是与一个比你有权力的人交流,你势必会做出一些妥协。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讲,任何妥协都有底线,虽然不是所有真话都可以说,不是所有想做的事都可以做,有可能做的事也不是自己最想做的事,说的话不是自己最想说的话,因为你受到体制、市场各种权力因素的影响。但有个底线是,绝不说完全违背自己愿望的话、绝不做完全违背自己愿望的事。而且绝不去主观上奉承,当然这样你可能有些话不能说,有些事不能做,但绝不可以做违背自己学术良心、道德良心的事情,这个对于我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底线了。我不能说我百分之百做到了,但是至少基本做到了,我不是说我做过的事都有价值,其实很多事都无价值,但是我绝不做违背自己学术良心的事。当然,在现在这样的背景下保持学术品格的底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毕竟诱惑很多,而且比压力更加有动力性,所以,提底线,本身就很悲壮,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坚守某些东西。 问:那么,你对眼下人们常常提到的学术腐败是如何看待的呢? 尹:学术腐败其实跟社会机制有关系。腐败的根源就是当人们发现不腐败的人得到名和利的机会小,而腐败的人得到名和利的机会大,而且腐败获得利益的风险、成本和代价都很低,而廉正获得利益的风险、成本、代价很高的情况下,腐败就会成为一种瘟疫,四处蔓延。 对于我来讲,我在学术环境比较正常的时候就比较早获得了一定的学术地位。虽然目前也面临种种诱惑,但是有一定的抵制诱惑的基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抵抗腐败的内在基础比较好。如果到现在我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获得,我估计这种腐败对自己的诱惑可能就更大。当目前为止,对于我来说,小腐败可能会有,但是人为的主动的大腐败肯定没有。最大的腐败可能是“一稿多用”(笑),我现在最大的忧患也在于此。虽然我明确告诉他们已经在哪里发表过,但是有时候想拒绝媒体都难,媒体总会强调我们这本刊物与那本刊物的受众群不同。一方面媒体有这种需求,一方面一个人精力有限,每年也就那么几个研究成果,被引用被转述的情况多了,客观上就造成了一种“一稿多用”的现象。我想,这之间可能还是个尺度问题,而且还有个观念问题。虽然现在也会有因为各种利益,放弃一点儿原则的时候,但我还是一直提醒自己,这些东西不那么重要,作为一名学者,让人尊重还是最重要的。 我一直追求让人尊重。这可能源于我一直在学校,一直面对学生。学生的尊重使我能够保持自己的这种生活状态和人格状态。学生不是因为你有权,或者因为你有钱而敬畏你,而是从骨子里尊重你,这种感觉是我最大的快乐。这么些年来,我上课从来不用点名,上课的学生永远比选课的人数多。正是有了学生的这种尊敬,即使遇到一些特别不公正的时候或者是别人利用不正当的手段影响我的时候,我也能够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所以,我几乎在每一本书的后记中,都感谢学生们给予我的支持,那是一种精神上的最大的力量。 问:您觉得20年的研究之于您所处的这一领域,或者说您学科本身的意义是什么? 尹:我觉得可能是两个方面。因为媒介文化自身在当代文化中扮演着一种极其重要的角色,而我的研究正好为这个相对研究比较薄弱的领域提供了一种比较完整的素材、相对完整的成果。有人说我的研究是个文化备忘录,因为我常常将研究置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将影视作品还原到社会状况中去,这样做不仅能为人们理解影视文化,而且还能为人们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提供一些相对完整的素材与研究成果。 另一方面,我在努力建构一种媒介批评态度,在媒介文化发展的情况下,一个人文学者对于媒介文化应采取何种态度和立场,是我一直思考并亲身实践的。我以为,一方面要积极参与,一方面要清醒地保持自身的人文价值、人文立场,不要媚俗。至少对我来说,在研究中都试图坚持这样一种立场。 问:您会如何用一句话概括您的学术成果? 尹:一句话概括我的学术成果?没有特别的想过。不过,我20多年所做的,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可能是通过解读媒介来体验人生、观照社会。解读媒介是我人生的一种体验,是我观照社会的一种途径。
作者: 尹鸿著
出版社: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
简介:《尹鸿影视时评》主要内容:尽管随着电影发行放映体制的改革,电影的产业性质得到了再一次的确立,但是近年来中国电影的产业化、商业化发展更多的是体现在发行放映方式上,并不是体现在电影的规划和生产上。1996年以后,不仅前一阶段中国电影产量迅速增加的趋势被减缓,而且以类型片为主导产品的商业电影的生产在数量上也急剧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