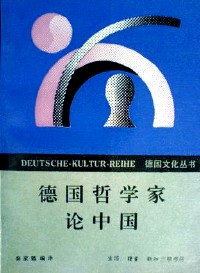共找到 1 项 “秦家懿编译” 相关结果
- 全部分类
- 全部
- 文学
- 历史
- 哲学/宗教
- 法律
- 政治/社会
- 医学
- 教育/心理学
- 艺术/传媒
- 研究生考试
- 资格认证考试
- 公开课
- 语言
- 经济金融
- 管理学
- IT/计算机
- 自然科学
- 工学/工程
- 体育
- 行业资料
- 音乐
- 汽车机械制造
- 文档模板
- 创业
- 农学
- 生活
- 数据库教程
- 民族
作者: 秦家懿编译
出版社:三联书店,1993.9
简介: 莱布尼茨和“儒学” 文:陈乐民 出处:读书 1996年第7期 平时在同朋友闲聊的时候,我曾说,时下有些文章把莱布尼茨与《易经》的关系说得很神,大有引古洋人为弘扬民族文化和重振儒学的助力之意,其实并没有理会莱布尼茨是怎样接触“儒学”,接触了哪些“儒学”,又到底为什么要接触“儒学”的。至少可以说是宽泛不审。那位朋友几次劝我写出来。我说写过了,即九三年第三期《读书》上刊出的《非作调人,稍通骑驿》。不过,我那篇小文虽然点出了不要夸大中国对启蒙运动的影响,现在看来确实不痛不痒、吞吞吐吐。近两三年又拿到些没看过的材料,如在汉诺威的莱布尼茨纪念馆根据馆藏手稿编辑的《莱布尼茨关于中国的通信集》等,使我的想法更明确了些。于是就决定写这篇东西;我不是专门针对本文开头提到的那种说法而发的;各有各的想法,我只写我的。恰好今年六月二十一日是莱布尼茨三百五十冥寿,就也算作纪念吧。 莱布尼茨首先是哲学家,说是神学家也许更恰当些。他在数学、力学等自然科学方面都有创造性的发现。称得上是大学者。但是他并不是所谓“汉学家”,“莱布尼茨与中国”在他著述等身的研究当中,也只占着一种“边缘”的位置;所以这方面的话题必须放在他的哲学体系的框架里。莱布尼茨的“中国观”,是附属于他的哲学体系的,我想强调一下并不是多余的。 据莱布尼茨晚年自述,他考虑哲学问题在少年时期就开始了:十五、六岁年纪,常常独自一个在莱比锡近郊的一片森林里漫步,满脑子都是该不该把经院派的“实体形式”(Substantial Forms)保留在自己的哲学里之类的问题。稍后开始上逻辑课了,他觉得:“这里面一定大有学问,我在范畴学里找到了极大的喜悦,它摆在我面前就像一本包括万事万物的花名册;于是打开各种‘逻辑学’的书,去到里面寻找最好的和最周详的那一种。我时常自问,也常向同学们讨教;这一事物或那一事物,该当归属在哪一个范畴或亚纲(sub-class)里。”莱布尼茨不停地思索着,渐渐地把注意力集中起来了,他要为数学和形而上学的结合找出一种“新方法”。这种“新方法”就是要找到或创造出一种能够表示人类思想的符号或字母,他称作“普通文字”(UniversalCharacteristic)。这些“符号”可以用数字来表示,因此是一种可以计算的算术符号;符号之间组成的各种联系,传达出各种信息,凡是掌握这种“普遍文字”的人,不管天南地北,都能<SPS=1256>然于心。这样就能够使理性哲学像算术那样准确明晰。这种过程,就叫做“数学—哲学的研究过程”。 把思想转化为“符号”,可以用数字的加减来计算,把语言的隔阂、思维的繁复都用简单的“符号”来解决,这连莱布尼茨自己也认为是“造化之谜”。但是,这种探索,终其一生也没有结果。二十年后他在给法国神学家弗尤士(Verjus,Antoine)的信中说:“我还有一项计划,是我从早年起就一直想着的……由于缺少足够的时间,又乏称职人手襄助其事,所以这项计划至今没能实施。这项计划就是要通过演算来发现和创造真理;那完全不等同于数学,却能使真理像数学和几何那样不容置疑。”这叫做“演算哲学”。 这并不是莱布尼茨的胡思乱想,因为根据他的哲学主旨《先定和谐论》(pre-established Harmony),世界本即是一个和谐的整体,这种“和谐”是神所“先定”的,能够把宇宙万事万物都和谐地统起来,任何矛盾、差异和冲突都可以在“先定和谐”中消解;除了神是绝对的,一切的一切都是相对的,所谓差别无非是“程度”(degree)的差别,而不是“‘类”(kind)的不同。只要发现了人人都能掌握的这种“符号”,世界上的任何人就都能用这把万能钥匙打开“真理”的锁。 莱布尼茨正在想这些问题的时候,在罗马遇见了从中国回来的耶稣会传教士,从此开始对中国的古老文明产生了好奇心;既然东方有绵延几千年的文明,那就一定早就存在着像“创世说”那样的普遍真理,一定有过表达普遍真理的原始文字。他推想,远古的希伯来人定会把真理传到了东方。于是他就在同耶稣会传教士的频频通信中——在当时这是了解中国的唯一渠道——如饥似渴地了解中国的、印度的、日本的,以及其他东方民族的语言文字、历史、宗教和哲学、物理、数学、博物等等。他根据这些材料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事》,他在“序言”中说:“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仿佛今天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汇集在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的欧洲——支那(人们这样称呼它)。”因而确信两大文明必然可以找到沟通的桥梁。 现在习惯说莱布尼茨受了中国哲学的影响,这样说实在太笼统了;既然有了接触,自然就有影响,问题是哪些影响。从许多封通信和他死前写的、但未发出的给法国数学家德·雷蒙(De Rémond)的长信《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来看,主要是两类内容:第一类是《易经》,其实是那张“伏羲八卦方位图”。第二类是中国古籍中出现的“天”、“上帝”、“太极”、“理”、“气”等概念和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 “八卦图”是法国传教士白晋(Bouvet,Joachim)寄给他的。白晋是路易十四派到中国的六教士之一(其中一人死在半路上,所以实到五人),白晋和另一传教士张诚(Gerbi11on,Jear-Francois)留在了康熙的宫中。白、张二人做了不少事,如给康熙讲几何学,用满文写了数学书,康熙亲自作序;他们还在宫里造了一个化学实验室,编了一本人体解剖学,等等。传教士的“本职”工作是传教,康熙对基督教比较宽容,所以多数教士都把他奉为“开明天子”。白晋奉谕学习《易经》,根据故宫档案,康熙是屡次过问的,还亲自讲解,让他作笔记,当作“作业”给皇帝看。不过,白晋究竟懂了些什么,只有天知道;康熙本人的水平如何,怕也难说。白晋没有接触过任何像黄宗羲、胡渭那类“易”学行家,看来他那点儿《易经》知识无非来自康熙和一些官僚而已。那作为“作业”的“易经稿”似乎很难产。据方豪从梵蒂冈图书馆抄来的十份有关馆存文件中的最后一件,康熙于五十五年闰三月初二日(合一七一六年)谕大臣赵昌、王道化等给白晋传话:“……白晋他的《易经》,作亦可,不作亦可;他若要作,着他自己作,不必用一个别人,亦不必忙;俟他作完全时,再奏闻。钦此!”白晋从第一天知道中国有个神秘而万能的《易经》起,至此时已经十来年了。从口气看,康熙给的分数不算高,也许是因为罗马教廷在中国传统“礼俗问题”上指手划脚惹恼了康熙,所以对传教士失去了前时的兴趣,连带着对白晋也有些冷淡了。 但是,白晋毕竟在这十来年当中断断续续地摆弄过《易经》,在脑子里总形成些印象,特别是邵雍传下来的那张“八卦图”,左看右看,莫测高深。白晋以为,那些阴阳两爻重叠组合,从数的排列上与柏拉图、毕多葛拉斯的“数”观念很相像,与莱布尼茨二十多年前发明的“二进位制表”也相当契合,足见造物主泽被寰宇,并无分东西南北的。白晋忽发奇想,以为或许伏羲就是中国的造物主,伏羲甚至不一定准是中国人,而是世界最早的古哲之一。在白晋眼中,《易经》就是“八卦图”,作者是伏羲,里面包含了开天辟地以来的上至天象、下至地理诸般学问。只是其原旨被后来的注家弄乱,在注释疏证里杂进了大量错误的和迷信的东西。白晋以上这些看法,直接影响了莱布尼茨。 莱布尼茨与白晋通信,大概是从一六九七年开始的。当时白晋正奉康熙圣旨自京返欧再物色几个传教士。十二月莱布尼茨给在巴黎的白晋写了一封长信。内容大体上是:一,称赞白晋给康熙讲哲学(即基督教)和数学,大有助于基督教进入皇帝和他的臣属的心中。二,极高兴从白晋处了解更多的中国情况,以补充先时编辑的《中国近事》。三,了解中国的语言文字,是了解中国历史的基础,所以希望寄赠中西文对照的字典以及左近东方各语种的字典。莱布尼茨认为东方诸语,必有相通处,沿中亚而西向,有些字根必随之而有传衍。四,需要一本详细的中国编年史,以观察和比较中西远古情况。五,莱布尼茨认为,中国的理论数学远远不能与西方相比,但是中国的长期历史实践,必然有可以为欧洲所需要的东西(指数学方面)。六,莱布尼茨设想,中西哲学必是相容的;他以“力”的理论代替笛卡尔“实体”的广延,不知在中国可有此解。总之,中国的各种情况,如历史、伦理、政法、哲学、宗教、数理、工艺、医学、天文气象,等等,无不在他的兴趣之内。 第二年二月,白晋给在汉诺威的莱布尼茨复信,第一次提到了《易经》,写了他对“八卦图”的看法。说它囊括了所有学科的原理,是一套完备的形而上学体系,不仅有助于“重建远古中国人的正宗哲学,而且可能使整个民族了解真神之所在”;这张图还有助于“在所有学科中建立起应当恪守的自然方法”。他认为,可惜的是,其中真义后来竟不得其传;如果能使中国人重振先人的哲学,则是中国人接受基督教的一条方便途径。 白晋寄出这封信以后不久又回中国了。莱布尼茨看到这封信,产生了一种很新鲜的印象,因为以前得到的知识都是零星的、现象的,白晋的信则涉及到形而上学,这正是莱布尼茨最关心的。他在给弗尤士的几封信中一再表示希望得到白晋更多的启发:“我一直认为必须尽可能地给中国人的实践和学说一个正确的阐释,就像圣保罗在雅典看到陌生的神祗圣坛时所做的那样。” 一七○○年十一月,白晋从北京托人转信给莱布尼茨,重申他对《易经》的看法,说远古的中国人从元始已有了“纯粹而洁净”的哲学,甚至比近代西方哲学还要“坚实而完备”。白晋认为,揆诸本源,伏羲之说与希伯来先哲是完全契合的。他在这封信里还以“八卦图”六十四卦的“数”字排列比附柏拉图和毕达格拉斯,来证明他是有根据的。 一七○一年二月,莱布尼茨函白晋,在讲过欧洲近来的许多科学发明之后,详详细细地介绍了他的“二进位制”,说一切数都是“壹”(unity)和“零”(zero)构成的,一如万物无一不是来自神和无。“壹”就是“1”,“无”是“0”。“一切数都是‘壹’和‘无’的各种结合,从‘无’可以得出各种各样的结合,犹如说神从‘无’中造成万物,而不必求助于任何原始材料;换言之,只有两个第一原则,即‘神’和‘无’:‘神’代表完备,‘无’代表不完备,或非实质。”这几句话很有些“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一类的味道。莱布尼茨在信里把“二进位制”的各种组合列成表,说这种“数”论一定能打动中国的哲学家们,甚至皇帝本人。 同年十一月,白晋函莱布尼茨,寄来了“八卦图”。白晋说,看了莱布尼茨的“二进位制表”,觉得与“八卦图”的原理丝毫不爽,如阳爻可释为“1”,阴爻可释为“0”,六十四卦的组合排列,恰与“二进位制”相符。因此,白晋说,莱氏关于“普遍文字”的设想与东方的古老文字符号的“真义”一定有共同的渊源。因为在神所决定的“自然而和谐”的秩序中,这一切都是必然的。 以后,莱、白还有些信函来往,大体脱不出上述的范围。莱布尼茨《论中国人的自然哲学》的第四部分“论中华帝国创始者伏羲的文字与二进位制算术中所用的符号”,就是根据这些通信提供的材料写成的。莱布尼茨把白晋的观点差不多原样接受下来,所以,莱布尼茨对所谓《易经》的看法,应该说是他和白晋的共同看法。莱布尼茨与《易经》的关系,大略就是这些。 莱布尼茨与中国哲学的第二类内容,是用神学眼光解释中国的“天”、“上帝”、“太极”、“理”、“气”等概念。他这部分知识也全是从传教士那里来的。莱布尼茨晚年看到了法国数学家德·雷蒙给他的耶稣会教士龙华民(Longobardi,Nicho1a)写的《关于中国宗教的若干问题》和方济会教士利安当(S.Marie,Antoine de)写的《关于赴华传教的若干重要问题》。德.雷蒙要求他写一篇评论,这就是没有发出的长信,即《论中国人的自然哲学》。当时,德·雷蒙还给他看了马勒伯朗士(Malbranche,Nicho1as)虚拟的《一个基督教哲学家和一个中国哲学家的对话录》,不过在这封长信中没有提及。莱布尼茨的“儒学”知识多来自龙华民和利安当两篇文章中引用的材料,写了长信的前三部分,但作出的判断和结论却与龙、利截然相反。 龙华民和利安当是反对利玛窦对中国文明的“调和态度”的,例如利玛窦认为中国经典中的“上帝”就是西教的“天主”,只是称呼不同而已。龙等认为中国根本就是“无神论”,中国哲学的概念终归说的是“物质”,并不知“神”为何物。莱布尼茨说中国与欧洲一样,同样是“有神论”;他用他的“先定和谐论”(在哲学、神学上)和“教派融和论”(新教与旧教的融合、东西宗教的融和)来解释中国哲学的那些概念和它们之间的关系。既然整个宇宙是神主宰的、“先定”的、“和谐”的秩序,那就没有什么是说不圆的。当时,莱布尼茨关于“单子”(monads)的理论,已经成熟;《单子论》(Monadology)写定于一七一四年,与《论中国人的自然哲学》同属莱氏晚期著作,两文讨论的都是上帝及其存在、人的灵魂、先定和谐等问题。后者没有使用“单子”这个词,但是“单子论”的影子通篇可见。两文可以相互参比,是“姊妹篇”。中国哲学中的概念,无分先秦、宋儒,无论“天”、“太极”、“太虚”和“理、气”,都一概涂上了莱布尼茨的神学色彩。莱布尼茨是用“单子”理论解释中国哲学,又用中国哲学来反证“单子论”。他和龙华民们用的都是“我注六经”法,只是注法相反,龙等注出了“无神论”,莱布尼茨注出了“有神论”。 所以,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的看法,是有这个哲学背景的。莱布尼茨哲学是个很大的框架,最顶上一层是顶大帽子,即“先定和谐”,下面几根立柱,分别是“普遍文字”、“二进位制”、“充足理由原理”、“单子论”等等。天道人性、精神物质,统统都在这个大框架里安身立命。 莱布尼茨终于在宋儒的“理”字上找到了可以把中西哲学沟通起来的桥梁:“理”相当于他的第一位的“简单实体”(simp1e substance),是内在的、高级的“单子”,是“气”这种低级“单子”之所由生;是精神,而不是龙华民所说的“物质”。至于那统率一切的“太极”则具备神的所有品质,它就是“GOD”。“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极”是万物的主宰和创造者。所以莱布尼茨发现,中西哲学相近相似处甚多,可以彼此遥契。陆九渊说,地无论南北东西,时无论千数百年,只要有“圣人出焉”,则“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莱布尼茨一定会赞同他的话。 莱布尼茨是自成体系的、神学家意义上的哲学家,他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带有很浓厚的神学气。在十七世纪接近启蒙时期的哲学家当中,他比不上斯宾诺莎。莱布尼茨通过神学接触了力学和数学,并从笛卡尔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但是,像微积分这样重大的发明却没有使他从原来的神学立场上后退一步。他比笛卡尔更为“有神”。他在一封信中说:“关于笛卡尔哲学,我毫不迟疑地绝对肯定它会导致无神论。”在另一封信里写道:他固然在许多方面很敬仰笛卡尔,但也“深信他的机械论充满错误,他的物理学过于粗率,他的几何学很有局限;他的形而上学则兼有这些乖谬。”莱布尼茨哲学的终极任务,是要非常坚定地以各种手段确证上帝的存在和全能。 一个像莱布尼茨这样好学、博学的人,虽然钟爱自己的哲学,但也善于从外界吸收营养。正如他晚年在信中说的,“每拿到一本新书,我就去从中寻找能学到什么,而不是先去找能批评什么。”他对于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正是抱着一种兼容和吸收的态度。不过要弄清楚:如果说兼容和吸收过来的中国文化(准确些说,他理解的“儒学”)对他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佐证”和加强了他的神学,而不是促使他更接近启蒙。 当然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莱布尼茨无疑是位“有功之臣”。在那种时刻有这样有容为大的学者胸怀,确实反映了欧洲走出中世纪樊篱、走向广阔天地的时代势向;只不过他没能抓住那跳动着的脉搏。后来的欧洲人在面对东方时,总不能绕过莱布尼茨的开拓之功。至于我们中国人,则常有一种特有的“自我中心”情结,喜欢听赞扬的话,不管那种赞扬出自何动机和是否在点子上,只要赞扬就好。所以在弘扬民族遗产的声浪中,对于着意倡导儒学的时贤来说,莱布尼茨和伏尔泰就常被提到,因为他们的话都比较中听;而像孟德斯鸠等虽也是从传教士那里了解到中国情况,看到的却是那极为不堪的一面,其实他提到的一些中华帝国的痼疾倒是比莱布尼茨、伏尔泰式的颂扬要真实得多,也辛辣和入木三分得多。把他的这类描写(如在《法的精神》里)拿来与鲁迅讲国民劣根性相对照,会感到惊人的相像。孟德斯鸠不曾“崇拜”儒学,在放言中国如何影响了欧洲的启蒙运动、并认为有过某种“东化”之势的时候,自然是派不上用场的。 一九九六年四月于芳古园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