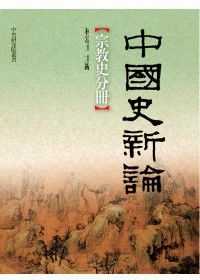共找到 1 项 “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0” 相关结果
- 全部分类
- 全部
- 文学
- 历史
- 哲学/宗教
- 法律
- 政治/社会
- 医学
- 教育/心理学
- 艺术/传媒
- 研究生考试
- 资格认证考试
- 公开课
- 语言
- 经济金融
- 管理学
- IT/计算机
- 自然科学
- 工学/工程
- 体育
- 行业资料
- 音乐
- 汽车机械制造
- 文档模板
- 创业
- 农学
- 生活
- 数据库教程
- 民族
英文共同题名:New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history
作者: 林富士主编
简介: 序 《中國史新論》總序 幾年前,史語所同仁注意到2008年10月22日是史語所創所八十周年,希望做一點事情來慶祝這個有意義的日子,幾經商議,我們決定編纂幾種書作為慶賀,其中之一便是《中國史新論》。 過去一、二十年來,史學思潮有重大的變化,史語所同仁在開展新課題、新領域、新方向方面,也做了許多努力。為了反映這些新的發展,我們覺得應該結合史學界的同道,做一點「集眾式」(傅斯年語)的工作,將這方面的成績呈現給比較廣大的讀者。 我們以每一種專史為一本分冊的方式展開,然後在各個歷史時期中選擇比較重要的問題撰寫論文。當然對問題的選擇往往帶有很大的主觀性,而且總是牽就執筆人的興趣,這是不能不先作說明的。 「集眾式」的工作並不容易做。隨著整個計畫的進行,我們面臨了許多困難:內容未必符合原初的構想、集稿屢有拖延,不過這多少是原先料想得到的。朱子曾說「寬著期限,緊著課程」,我們正抱著這樣的心情,期待這套叢書的完成。 最後,我要在此感謝各冊主編、參與撰稿的海內外學者,以及中研院出版委員會、聯經出版公司的鼎力支持。 王汎森 謹誌 導言 中國史研究的宗教向度 一、引言 2004年的春天,我允諾主編《中國史新論──宗教史分冊》之後,在編務上,立刻面臨兩個相互交錯的難題。首先,我必須決定要從中國史的角度看宗教,還是要從宗教的角度看中國史。前者,可以依循中國史的斷代和分期,探討每個時期的「主流」或「優勢」宗教,終極目標是要嘗試界定所謂的「中國宗教」(Chinese Religion)或「中國宗教文化」的特質。換句話說,必須打破以個別宗教作為敘述主體的做法,改從「信徒」、社會或政治的角度去看每個時期的宗教活動、宗教信仰、宗教生活、宗教空間、宗教組織等。後者,則必須以宗教為主體,探討各個宗教的發展軌跡以及彼此之間的競合與互動,側重於分析宗教的傳播與中國政治、經濟、族群、地域文化、日常生活、社會活動、社會形態之間的關係,其盛衰起伏往往貫穿傳統王朝的界限和中國的疆域。當然,這兩者並非毫不相干,更非彼此背反,但是,視角、焦點,與敘述的策略還是有很大的差異。 其次,我必須決定請誰來執筆撰稿。假如選擇要「從中國史的角度看宗教」,那麼,歷史學者將是首選。不過,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台灣,甚至世界漢學界,從20世紀以來,中國宗教史的研究者在歷史學界一直是少數分子,以宗教史為主的研究成果在整體歷史研究中也一向居於邊緣地位 ,要找到一批能勝任又有意願撰稿的歷史學者,恐非易事。倘若換個角度,「從宗教的角度看中國史」,那麼,除了歷史學者之外,便有為數不少的中國宗教的研究者可以選擇,不過,他們之中,或是以當代宗教為主要研究對象的人類學者和社會學者,或是傾向理論與教義探討的宗教哲學家,或是偏重文本與儀式分析的文學與宗教研究者 ,其研究取向與歷史研究畢竟頗有差異,其所能涵蓋的時間範圍和議題也和此書所設定的內容有點距離。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只好回歸到《中國史新論》整套書的編輯旨趣。《中國史新論》是為了慶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八十周年(1928- 2008)而編,也希望藉此書呈現史語所同仁最近一、二十年來在史學課題、領域及方向的墾拓成果,讓外界認識史語所的新發展和新風貌。既是如此,那麼,撰稿者當然是以史語所的同仁為主力。因此,我便向史語所的歷史學者發出邀稿函,並說明我對於《中國史新論——宗教史分冊》的編輯和撰稿構想,其大意如下: 一、時代分期採較寬鬆的方式,並側重於兩個分期之間的轉折。簡單的分是:上古至中古(先秦至秦漢);中古至近代(六朝至唐宋);近代至現代(宋元明清到目前)。每一個人可以集中於探討某個時期(或朝代)的宗教,但盡量簡略的交代其源流和後續發展。 二、每個時期只探討當時的「主流」或「優勢」宗教,至於主流或優勢的界定,可以從政府認可、信眾數量、社會影響力等方面著眼評估。當然,每個時期不一定只有一個主流或優勢宗教。 三、盡可能從研究課題、對象、角度、材料、與方法方面尋求創新與突破,尤其是以往較被忽略或爭論不休的課題,可以優先探討。 結果,我獲得了還算熱烈的回應,共有10位同仁提出了打算撰寫的題目,其時代恰巧可以涵蓋上述的三個分期 ,不過,最具中國本土色彩的祠廟信仰與道教,在近代中國相當蓬勃的「新興宗教」(或稱之為「民間宗教」、「秘密宗教」、「教派宗教」),以及與明清中國社會關係頗密的天主教,卻無人處理。於是,我便向史語所之外的歷史學界同行求助,也獲得康豹(祠廟文化)、莊宏誼(道教養生)、黎志添(道教科儀)、張先清(天主教)、王見川(新興宗教)五位朋友的正面回應。 在這之後,我們在2007年5月舉辦了「中國史新論?宗教篇與性別篇」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7/5/1-3),檢視大家所完成的初稿,並請同行的專家提出批評和建議,讓所有的撰稿人進行修正。當時,我非常樂觀,認為可以順利在2007年年底收齊所有修訂稿,然後展開送審與編輯作業,如期在2008年10月22日史語所所慶之前刊印。沒料到,所有出版前的集稿、審稿、改稿工作,一直到2009年年底才算完成。在編輯《中國史新論——宗教史分冊》的這四、五年之間,其實發生了不少意料之外的事。 先是柯嘉豪離職赴英任教,卓鴻澤辭職返回馬來西亞,我則被借調至國立中興大學任職。接著,康樂逝世,蒲慕州退休轉至香港,林純瑜也結束她在史語所的博士後研究。人事的變化與波動,不僅造成我情緒的起伏,也的確影響了此書的進度。尤其是我所敬愛、親近的康樂突然仙去,一方面對我的心理造成巨大的衝擊,讓我不由停步,重新思考生命的意義及走向。另一方面,康樂的遺稿未及修整並完成結論,我不斷依違於捨留之間。要捨,這畢竟是他去世前仍在勤奮經營中的稿件,恐怕也是他留給世人的最後一篇學術論文。要留,則必須有人賡續其業,代完其稿,可是,其專業領域又罕有人能窺其堂奧。不過,在長考之後,我還是決定收錄其遺作,在不變動其本文、原意的情形下,由我自己操刀,以續筆的形式補寫其結語。因此,除了3位撰稿人因另有考慮之外,此書總算在2009年收齊了12篇論文。 這12篇論文雖然遠不足以呈現中國宗教的各種面貌,也無法交代清楚任何一種宗教在中國社會的興衰起伏,但是,其所觸及的若干議題仍然值得中國史或及宗教史研究者省思。舉其大者而言,至少有下列四點。 二、宗教的定義 1920年代,梁啟超(1873-1929)在北京的清華大學講授「中國歷史研究法」時,曾針對中國宗教史研究提出一些極富爭議性卻影響深遠的看法 。他是將宗教史放在「文化史」的範疇來談,認為宗教和語言、文字、神話、學術思想、道術(哲學)、史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文學、美術同屬「人類思想的結晶」,但是,必須具備「超現實世界的」「教義」和「教會」這兩個條件,因此,梁啟超強烈質疑中國究竟是不是一個「有宗教的國家」。 同時,他也反對康有為當時所倡導的「孔教」運動,否定儒家是一種宗教 ,在先秦的流派之中,他只承認「墨家略帶宗教性」,但因沒有天堂及死後世界的觀念,所以,墨家仍不能算是宗教 。 基本上,梁啟超認為「中國土產裡既沒有宗教」,因此,「著中國宗教史主要的部分,只是外來的宗教了」。他所說的「外來的宗教」,是指佛教、摩尼教和基督教(包括景教、耶穌教、天主教等),而在這些外來宗教之中,他認為只有佛教「有很多精彩的書」,值得研究。不過,他還是覺得,佛教也不適合作為中國宗教史主要的研究對象,他說:佛教「應該擺在哲學史裡抑宗教史裡還是問題。為著述方便起見,擺在哲學史更好」,「中國宗教史祇能將某時代某宗派輸入,信仰的人數,於某時代有若干影響,很平常的講講而已。雖或有做的必要,卻很難做得有精彩。」 他唯一肯定的是「中國人對於外來宗教的一般態度」,「很值得一敘」。 不過,梁啟超也沒有忘記,中國還有一個「道教」。對此,他的態度顯得有點自我矛盾。他一方面覺得道教「很醜」,和中國社會無多大關係,對於「中國國民心理無多大影響」,令他覺得「羞恥」,可是,另一方面,他還是承認「做中國宗教史又不能不敘」道教,卻不交代理由。我想,他之所以不得不接受道教,恐怕是因為道教不僅有「教義」也有「教會」,完全吻合他對於宗教的界定。更奇特的是,他雖然質疑中國有沒有本土宗教,卻還是說「做中國宗教史」,「有一部分可寫得有精彩」。這個部分,就是「祭祀」,尤其是貫穿祭祀的核心觀念「報」,以及祭祀的對象「神」。他最後的結論是: 做中國宗教史,依我看來,應該這樣做:某地方供祀某種神最多,可以研究各地方的心理;某時代供祀某種神最多,可以研究各時代的心理,這部分的敘述纔是宗教史最主要的。至於外來宗教的輸入及其流傳,只可作為附屬品。此種宗教史做好以後,把國民心理的真相,可以多看出一點;比較很泛膚的敘述各教源流,一定好得多哩。 由此可見,對於梁啟超而言,研究中國宗教史應該以中國人所奉祀的「神」為主要對象,藉以理解中國人的「心理」(心態)。但是,光有「教義」而無「教會」,其實並不符合他自己對於宗教的定義。 總之,梁啟超針對中國宗教史研究所發的一些看似精彩卻又矛盾的言論,主要是因為他替「宗教」畫下了一個非常清楚的範疇,而他所依循的標準,即兼具教義與教會,基本是基督宗教的特質。若以此為普世的標準,在研究「非基督宗教」世界的「宗教」時,便會遭遇不少的困難,有些社會甚至會被認為沒有「宗教」。因此,要探討中國的宗教及宗教史,還是必須先說明我們對於「宗教」的定義。而針對這個課題,蒲慕州在本書中有相當精細的討論。他認為:「宗教是對於『人外力量』的一種信仰。這種力量可以主動或被動的作用於人和社會之上,從而改變其命運。由於這力量的運作必須經過某種媒介體,才能將力量作用於人和社會之上,這些媒介體就形成了一般所謂的信仰對象。他們可能是有生命或無生命的,也可能是自然或超自然的。他們可能是祖先、神靈、鬼魂,甚至草木鳥獸等具有某些獨立性格的個體,也可能是力量本身。」因此,舉凡鬼神、死後世界、禁忌、陰陽五行、巫祝活動、祠祀等,都可以納入宗教研究的對象。 臺灣多數的歷史學者應該可以接受這樣的論點,事實上,他們大多揚棄了有無「教會」這個判準,將一些「組織性的」(institutional)和「擴散性的」(diffused)宗教等量齊觀。不僅探討有教團、教會組織的佛教、道教、基督宗教、伊斯蘭教等宗教,也研究那些沒有特定組織的巫覡、民間信仰、官方祀典等。即連備受爭議的「儒教」,也有人深入探究。不僅如此,非漢民族統治中國時所帶來的傳統信仰,如蒙古、女真、滿族的薩滿教(shamanism),也受到重視。而從宋代之後,在中國社會不斷出現的一些混合型的「新興宗教」,如白蓮教、八卦教、天理教、羅教、齋教等,也有人投入研究。 三、宗教與政治 在中國社會,「政治」可以說是無所不在。從個人的生活、思想、舉止、信仰,到群體的組織形態、家庭結構、經濟活動、風俗習慣、生命禮儀、知識教育、文藝創作、科技發展、流行品味等,幾乎都無法避免「政治力」的介入、滲透、控制或影響,宗教也不例外。康樂在本書的論文中便稱中國為「政教合一制」(Caesaro-papaism)的國家,政治秩序與文化、道德秩序一元化。歷代的政權爭逐者無不想盡辦法,運用各種宗教的儀式或手段,將自己塑造成擁有「天命」的統治者,宣稱自己是在人間遂行「天」(神)意志的「天子」或中介者,甚至是「天」(神)化身或降世以治理天下。而一旦掌握政權,統治者便必須利用並控制宗教,使其有利於自己「支配」(統治)的「正當性」,而一旦挑戰或危及政權,便予以壓制或消滅。因此,任何宗教在中國社會的興衰起伏,往往視其與政治(尤其是君王)之間的敵友、親疏關係而定,而統治者也往往會選擇接受甚至信仰有利於鞏固其政權的宗教。當然,過度依附政權或仰賴統治者庇蔭的宗教,雖可取得一時的榮寵並擴張勢力,但一旦失去君王的寵信或政治上的特權,若無其他穩固的社會基礎,其衰微也會相當迅速,就以清代來說,天主教、道教(天師道;正一派)和儒教便前後失去統治者的尊崇,也造成其生存與發展的困境。 在本書的論文之中,林富士便以先秦「絕地天通」的神話、秦漢時期的「祀典」、以及巫者政治社會地位的陵替,說明中國古代統治者的宗教控制。其次,康樂詳述中國中古時期來華的印度佛教,如何放棄或放鬆「沙門不敬王者」的主張和論述,轉而以「一佛一轉輪王」及「轉輪王即佛」的觀念調和中、印之間的文化衝突,並以佛教的論述提供中國君主在取得政權及建立支配「正當性」時的理論依據或「天命」來源。劉淑芬則探討南朝政府對於社會的控制,包括禁碑令、符伍制,以及對中國佛教(經典的正統性)的控制。她認為這些措施造成南方絕少石佛像,沒有像北方那樣處處有僧、俗共同組成的信仰團體,也較少有中國撰述經典的流行。這也使得南方沒有以僧人為首腦的佛教徒叛亂事件,相對的,也沒有發生政府禁抑佛教的滅佛事件。此外,陳熙遠剖析「孔教會」以及許多以「孔」、「儒」為名的社團在民國初年大量出現的現象,認為這是孔教傳統因應權力結構的改變,試圖轉向民間社會以尋找制度性的出路的一種表現。而卓鴻澤則藉由明武宗正德皇帝(1506-1521)對番教(西藏佛教)與回教(伊斯蘭教)的宗教態度,指出中國皇帝宗教信仰的「透明度」問題。他認為,宗教信仰作為皇帝日常生活的部分,自有其純屬個人信仰上追求的理由,其中或有家庭文化的背景,而不具有民族與國家策略因素的考量。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或許也可以說,皇帝雖然也有信教的自由和個人的信仰偏好,但當其個人宗教信仰與國家「祀典」或統治階層、多數百姓的主流信仰歧異之時,其最佳策略似乎是「隱晦其事」。 四、宗教與基層社會 本書強調要從「信徒」的角度去看宗教的發展,因此,便格外重視宗教在日常生活(daily life)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宗教與社會組織之間的關係,而其交會點就在於所謂的「基層社會」或「地方社會」,有些學者甚至稱呼這種視野下的宗教為「社區宗教傳統」(communal religious traditions)。當年梁啟超說中國宗教史若研究「祭祀」會相當精彩,其實已指出中國宗教這個相當重要的特質或面向。「祭祀」一直是中國社會最主要的宗教活動,而這種活動的運作,主要是透過各種層級的政府組織,以及各種規模和性質的社會組織(如家庭、村落、學校、行會、宗親會等)。 蒲慕州在本書的論文中便指出,以時日的運行、季節的輪替為主軸所發展出來的宗教活動,以及因應生活中的生老病死所發展出來的信仰宜忌,從先秦到兩漢時期,一直是官方與民間社會生活的重心之一。其次,劉淑芬透過造像碑不僅揭示了南北朝時期佛教信仰的南北差異,還讓我們清楚的看到北朝基層社會的宗教結社與宗教活動。至於莊宏誼與黎志添二人有關道教的論文,一位是透過養生文化,探討宗教如何影響其信徒的身體修煉及生活禁忌;另一位則是透過科儀活動,探討宗教發展與地方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 此外,張先清探討清代乾、嘉、道(「百年禁教」)時期天主教的傳教活動,指出明末清初的天主教是在知識階層中透過科場與文社關係傳播;清代前期轉而以家庭為基礎組成的親緣網絡、以地域關係為基礎的地緣網絡,和以行業為基礎的職業網絡,作為傳播通路;乾、嘉、道時期,雖然朝廷禁止天主教公開傳播,但是以親屬、鄰里與職業構成的複雜社會關係網絡,仍讓天主教得以繼續在中國社會中保存並發展。而康豹(Paul R. Katz)則指出,從帝國晚期到現在,寺廟儀式一直與中國地區社會有著複雜且連續的關係。地方社會的寺廟儀式正好位於掌握權力的三群人(官員、地方菁英、神職人員)的三角網絡中心,他們相互連結,或是由上往下進行控制與改革,或是由下向上爭取合法性與主體性。換句話說,透過基層社會的宗教活動,我們往往可以看到各種社會階層、社會群體,及利益團體之間的權力爭衡和資源分配,也可以同時看到中央的政治介入和地方的文化認同與社會動員。 五、外來宗教 「外來宗教」(尤其是早期的佛教和近代的基督宗教)一直是研究中國宗教的學者無法忽視的對象和課題,其中,最受注目的議題包括:一、因宗教傳播而帶來的非宗教範疇的「文化輸入」,例如,物質文化、語言、文學、藝術、科技、生活方式等;二、入華之後對於中國社會所造成的各種衝擊和影響,例如,禮制衝突、風俗變化、宗教論爭、思想轉折、經濟活動、價值觀念等;三、「外來宗教」的「本土適應」、「宗教融混」或是所謂的「漢化」(sinification或sinicization)、「中國化」,例如,佛教的「疑經」(「偽經」)制作與「三教合一」論、天主教的「祭祖」與「尊儒」等;四、中國人對於「外來宗教」的負面態度與敵對反應,例如,早年的「滅佛」、近代的「教案」等。 在本書的論文之中,柯嘉豪特別針對佛教的「漢化」問題提出檢討。他認為佛教傳入中國之後,的確發展出不同於其原生地印度佛教的面貌,但是,這不能簡單的歸結為中國改造了佛教,或是說佛教征服了中國。在他看來,以「漢化」說立論並不適切,因為,這一方面預設了有一個原初或本質的佛教;另一方面,「漢化」概念的佛教研究極易忽略不同民族、地區、階級與性別的信徒在中國佛教史上所扮演的多元角色。事實上,在文化接觸過程中,雙方都是積極、有意識的在進行「涵化」(acculturation)。他認為,「中國人」一方面透過外來的佛教重新定義中國文化的意涵,並使佛教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佛教的思想、規範與物質文化也同時深刻的轉化了中國文化的內容。 此外,李尚仁針對19世紀來華的美國長老會傳教士倪維思(John Livingston Nevius, 1829-1893)的「驅魔傳教」,則具體的闡述了「外來宗教」在中國社會的「涵化」。他指出,19世紀基督教傳教士在中國遭遇到當地人被鬼附身的現象,而倪維思的著作記載了當時西方傳教士和中國信徒對於超自然現象的態度和看法。倪維思一方面討論基督教傳教士對中國傳統信仰的看法與批評,另一方面則透過對中國人著魔現象的探討來回應當代科學對基督教信仰的挑戰。同時,李尚仁也指出,驅魔之所以成為基督教傳道人的傳教策略,其實是立基於中國的傳統信仰。換句話說,當兩種文化接觸之時,即使是以宗教傳播的方式在進行,也很少是單向的傳輸、代換或征服,通常雙方都會因接觸而同時產生變化。 六、結語 想要以一本書或12篇論文就清楚的呈現中國宗教的風貌,或完整的交代中國宗教發展的歷史軌跡,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本書也不敢有此妄想。不過,誠如以上的介紹和討論所示,我們至少對於中國宗教有了比較明確的界定,對於中國宗教的範圍、內容和特質有了比較扼要的描述,對於中國的政教關係有了比較細密而多元的論述,對於宗教在中國基層社會及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了比較豐富的詮釋,對於外來宗教與中國本土文化之間的互動也有了比較均衡的看法。我相信,這12篇論文,至少可以提醒中國史的研究者,無論是要探討中國的政治、經濟,還是社會、文化,都不應忽略其宗教向度。 後記:本書得以完成,首先,必須感謝史語所前所長王汎森院士的囑託、提示、敦促和耐心的等待。其次,必須感謝所有撰稿人的「慷愾赴義」與「配合演出」。此外,本書在邀稿、集稿的過程中,林純瑜博士出力甚多,特此致謝;而在送審、編輯、校訂的過程中,陳藝勻女士多所襄助,無限感激。最後,謹以本書獻給供養我多年的史語所,以及未能看到本書出版就駕鶴西歸的康樂學長。 林富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