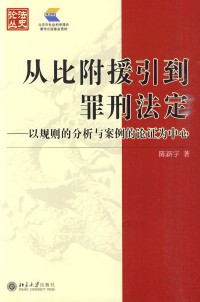共找到 4 项 “陈新宇著” 相关结果
- 全部分类
- 全部
- 文学
- 历史
- 哲学/宗教
- 法律
- 政治/社会
- 医学
- 教育/心理学
- 艺术/传媒
- 研究生考试
- 资格认证考试
- 公开课
- 语言
- 经济金融
- 管理学
- IT/计算机
- 自然科学
- 工学/工程
- 体育
- 行业资料
- 音乐
- 汽车机械制造
- 文档模板
- 创业
- 农学
- 生活
- 数据库教程
- 民族
作者: 【美】约翰 赛罗斯,陈新宇 著
出版社:21世纪出版社 2014-5-1
简介: 第一章 罗尼蔡斯死了快五年了。2月间,一个大风之夜,电话铃突然响起。此时罗尼的哥哥菲利普正在折叠沙发上睡觉。自打他从纽约搬回家住之后,家庭活动室就成了他的卧室。床单下乱成一团:他的铝合金拐杖、揉成团的面巾纸、电视节目指南、三个遥控器,还有一本卷了边的安妮塞克斯顿①传记,无绳电话也在里面。菲利普伸手在黑暗中摸索了半天,才抓住短粗的电话天线,拿起电话,按下通话键。“喂。” 一个微弱而有些耳熟的女声说:“菲利普,是你吗?” 菲利普正想张嘴问是谁,却突然打住,他知道她是谁了:梅丽莎穆迪,弟弟高中时的女友。菲利普脑海里只剩下毕业舞会那晚她身穿白色晚装的模样,白裙前摆上溅满鲜血。这回忆令他的嘴张得更大,老半天合不拢。从这个电话开始,这将是蔡斯一家人今后常有的表情。 “米茜②?” ①安妮塞克斯顿(AnneSexton,1928-1974),美国自白派女诗人。 ②米茜:梅丽莎的昵称。 “不好意思,有点晚了,吵醒你了吧?” 菲利普盯着墙上的老古董挂钟,自打他记事起,它就在这幢形状怪异的殖民风格老宅子里“滴答滴答”地走着,不过从没准过。此时挂钟的两根针指向午夜时分,其实现在只有十点半。在纽约,这个时间人们才刚刚吃过晚饭,或正在招手拦出租车,可在这宾夕法尼亚郊外,晚上八点后世界便死一般寂静。“我清醒着呢,”菲利普撒谎说,“好久没你的消息,还好吗?” “还行吧,我想。” 他听到电话里传来汽车飞驰而过的“嗖嗖”声,她的声音里有掩饰不住的颤抖,他觉得她一定过得不怎么好。“有什么事吗?” “我得跟你还有你父母谈谈。” 如果她想跟他父亲谈谈,她得追踪至佛罗里达,他跟现在的妻子霍莉住在那里,他母亲管那女人叫荡妇。不过菲利普懒得费神解释这么多,因为要说的实在太多,一下子没法说清楚。“你想谈什么?” 米茜还没回答,楼梯那边已传来沉重的脚步声,母亲下楼来了。不一会儿,她已站到折叠沙发旁边,那件老旧的白睡袍不雅地紧贴着她面团般的身体。前几天晚上,菲利普看了有线电视里播放的《心的方向》①的后半段。他想起凯茜贝茨泡进热水澡盆前全裸的场景—此时此刻跟那场景有得一比。他赶紧把视线移到母亲灰白的鬈发上,它们在她头上爆炸开来,张牙舞爪,令她看去像个疯婆子—还挺相称的,因为在菲利普眼里,她就是个疯婆子。 ①《心的方向》:美国电影,又译为《关于施密特》或《薯唛先生》。凯茜贝茨是影片中人物。 “谁打来的?” “稍等,”菲利普对着电话说,然后转向他母亲,“是米茜。” “梅丽莎?罗尼的女朋友?” 菲利普点点头。 此刻,那表情又来了:眉毛向上挑起,嘴张成O型,仿佛她也回想起了那可怕的一幕—梅丽莎的舞会晚装上溅满罗尼的鲜血。 她吃惊地问:“她想干吗?” 菲利普夸张地耸耸肩,接着回来继续跟梅丽莎说话。“抱歉,我妈刚醒来,在问是谁打的电话。” “没关系,她还好吧?” 对这个问题,他脑子有多种答案。他父亲离开了,这是每天不得不面对的事实;他母亲暴饮暴食,一天比一天胖;她吃数不清的药丸:治高血压的、治胆固醇偏高的、抗焦虑和抗抑郁的。然而他只说了句,“她还好。你想跟我们谈什么?” “我想当面跟你们说。我能找个时间过来吗?” “当然。” “那什么时间合适?” 菲利普想起他在纽约的生活,他住在东村①,公寓不过野营帐篷一般大小。一天中任何时候,他都可以邀请素不相识的人到他住所里来。对讲机坏了,他只好告诉每位来访者,让他们在街上喊他的名字。 ①东村:纽约地名。音乐人、艺术家、作家、演员和政治领袖人物的文化据点,曾经是纽约市波西米亚风和先锋艺术中心,现在是少有的几个前卫音乐爱好者与都市潮流先锋的基地之一。 “现在怎么样?”他听到自己对着电话说。 “现在?”梅丽莎说。 他等她说现在太晚了、太黑了、太冷了,可她的回答却让菲利普吃了一惊。 “实际上,我早就想告诉你们了,所以现在也好。” 他们互道再见之后,菲利普摁下通话结束键,把无绳电话往床上那堆东西中一扔。石膏下的皮肤很痒,他的两根手指挤进膝盖骨上方的狭缝中,拼命挠起来。母亲低头瞪着他,许多问题一股脑从她嘴里倾倒而出,仿佛她把吃过的东西全吐了出来,止也止不住:“你不打算跟我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吗?我是说,为什么过了这么久,那该死的姑娘还打电话来?她不知道这么晚给人打电话有多没礼貌吗?看在老天爷的分儿上,你就不能吭一声?” 菲利普不挠了,从石膏缝里抽出手指。这石膏一点也不像十年前他读高中时孩子们总喜欢在上面留下大名的那种纯白石膏,而是像被拉长了的滑雪靴,底部开口处露出他瘀青的脚趾。“如果你能闭嘴一秒钟,我就告诉你。” 他母亲双臂交叉抱在臃肿的胸前,夸张地表示她的沉默。有个晚上,菲利普看电视节目《演员工作内幕》,其中一个女演员有三个名字(他总是记不住那里面谁是谁),说她是专为后排观众表演的。这便是他母亲最近五年所过的生活,菲利普想,她的每个动作幅度都很大,坐在后排便宜座位上的观众也能看得一清二楚。 “她想跟我们谈谈。”他说。 “谈什么?” “我不知道。不管谈什么,她打算当面跟我们说。” “什么时候?” “现在。” “现在?她现在不能过来,深更半夜的。” “M。”他说。这个字母是他对她的昵称,自从一个月前搬回家后,他就这样称呼他母亲。她从没怀疑过什么,他想她肯定以为这个字母代表妈妈。但现在,明眼人能发现,这个字母还代表另一个M开头的词:疯婆子。只不过这是只有他自己才明白的小恶作剧而已。“两点钟才算是深更半夜。从技术上说,现在还只是傍晚。在纽约,人们刚吃完晚饭。” 提到纽约,她的嘴撅得像火山口一样,并抛给菲利普一个恶心的表情,令他想起她唯一一次来纽约看他时的情形。那是在警察打电话告知她菲利普住院之后,她搭火车、父亲从佛罗里达坐捷蓝航班去看他的那次。他们在圣文森特医院的十楼来了个蔡斯家庭聚会。菲利普躺在床上,受伤的脖子像木乃伊似的裹着纱布,他的腿刚刚包好滑雪靴般的石膏,被单下的身体青一块紫一块。 “这里不是纽约。”说完她转过身,“咚咚咚”上楼去了。隔着旧睡袍,他看得到她塌陷抖动的屁股。 难道这是“后视图”一词的最新定义?菲利普想。 菲利普听到她打开抽屉,又“砰”地关上。喧闹声中,他用拐杖支撑起瘦弱、伤痛的身子下了床。家庭活动室里的灯全熄了,可是四处都有微弱的光亮:电视机顶盒上的红点、手机充电器上闪烁不停的绿光、调光器开关上的点点橙色,它们合在一起,让菲利普模糊地想起晚间从飞机舷窗往外看的景象。他一瘸一拐地朝过道走去,脑袋里还想着那情景。他从餐厅穿过去,餐厅里摆着红木长桌和威尼斯玻璃枝形大吊灯,现在没人用了。他经过门厅走到楼梯下面的洗手间,那儿跟飞机上的洗手间一样狭小密闭。 镜子里映出菲利普的脸,他看上去比二十七岁苍老得多。他眼角没有鱼尾纹,脸上一丝褶皱也没有,没有任何明显的衰老印记,然而,眼睛里分明有种悲哀忧虑之情。这是张饱经风霜的脸。还有伤口—脖子上那道伤疤正在变成一道粗粗的红色拉链状疤痕,医生说它会慢慢变淡但不会完全消失。菲利普在洗衣篮最上面找到他的宽松套头衫,一把套进去,稍微遮掩了一下疤痕,接着梳了梳乱蓬蓬的褐色头发,刷了刷牙。当他正要走回过道时,不知怎么却又停下来,他打开药品柜,里面依旧原封未动,就像楼上他弟弟那间上锁的卧室。他伸手进去,拿出牙箍。罗尼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地包天。 “你在干吗?” 他转过身,看见母亲穿着图书馆的工作服,更准确地说是她当图书管理员时穿的那件衣服。哔叽大翻领毛衣,哔叽色裤子,这一定是在普鲁士之王商场里的加大码商店买的。菲利普想,她应该在那里再挑件新睡袍。 “我不知道。”他告诉她。 她走进来,带着一股女士除臭剂的味道,一定是她懒得洗澡在楼上喷的。因为吃药而浮肿的手一把从他手里夺过牙箍,放回原处,放在沾满灰尘的双氧水和一堆倾斜的黄瓜香皂中间。她关上柜门,镜中她的影子从他身边刷地闪过,吓得菲利普往后一缩。 “我不想你动他的东西。”她说。 他们以前为此吵过,现在他不想让自己再次卷入其中。梅丽莎随时会到,此刻他不想激怒母亲。他从她身边走开,径直走向厨房,“啪”的一声打开灯。虽然他在纽约见识过从怪人唐尼利弗姆那儿转租过来的公寓里那狭窄的厨房,可面对这凌乱不堪的样子,他还是有些吃惊。深色橱柜,嵌入式的照明灯,阴郁的瓷砖地面,仿佛它属于托斯卡纳修道院而非费城主线区①的一所房子。这四个星期来他们主要吃的是微波炉食品,但绝对没人猜得出来,因为洗碗池内锅碗堆积成山,花岗岩台面上碗碟一片狼藉,满是油渍、生着绿霉。前几天的一个晚上,他母亲的怪癖又发作了,而这次是豌豆汤。许多年前,他们家有过一位清洁女工,每周来两次,收拾这个乱摊子,由他父亲付钱。他父亲是布莱恩摩尔医院的心脏外科医生,薪水丰厚。现在再也没人收拾了。菲利普拉开冰箱门,拿出一纸袋咖啡,冲了一壶。以前在纽约,他在等某个陌生人从街上叫他时,也会这样冲一壶咖啡。 ①费城主线区:位于费城东南部,是费城的时尚区域。 “你在冲咖啡?”他母亲在他身后问。 这次,他没转身,而是舀了两勺咖啡放进滤网里。他想起以前他把钥匙扔出窗外后,听着“咚咚咚”的脚步声走上歪歪斜斜的楼梯时,心跳得有多快有多厉害。 “是的。” “难道你今晚不打算睡觉了?” “不。” 之后他们没再说什么。她从冰箱里的囤货中拿了一罐健怡可乐,又从橱柜里拿了一袋多力多滋玉米片,然后坐在木头凳上,靠着台面大嚼起来,还发出很大声音。菲利普把水倒进咖啡壶,回想起上次梅丽莎来访的情形。罗尼死后的那年夏天,她没打招呼就上门来。母亲躺在楼上卧室里盯着天花板,父亲在书房里打发时间,假装在读医学书,菲利普只好把手头上费城社区大学诗歌班的作业放到一边,把他们拉到家庭活动室,他们坐在那里,望着这个裹着绷带、伤心欲绝的金发女孩,最后,还是父亲送她到门口,跟她道别。 咖啡壶开始冒着热气汩汩地叫起来,有道灯光从窗外射进来。车道上传来摔上车门的声音。菲利普的心猛跳起来,就像以前在纽约时的那些晚上一样。他把手放在胸口,手指无意识地摸索着套头衫下的伤口,跟着他母亲一起往门口走去。厚格板门的两边各有一道长条玻璃。母亲把脸贴到右边那块玻璃上,用一种“她—怎—么—敢”的语调现场直播起来:“她怀孕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姑娘怀孕了。” 菲利普还没来得及提醒她梅丽莎绝对有权利怀孕,她又贴在玻璃上,开始没完没了地说起来: “你觉得她就是来告诉我们这个的吗?最好不要。我只想说这个。现在我最不想听到的就是她嫁给了哪个家伙,生活得有多快乐,而我儿子却在六尺深的地底下腐烂。” “M,”菲利普说,“为什么我们不能破例一次?在你大发雷霆之前,先等一下,看她想干吗。” 她转过身,直瞪瞪地看着他,前额上还有一块刚才贴在玻璃上留下的红印。
作者: 陈新宇著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简介: 近代中国法律改革,随着《大清新刑律》的制定,确立了西方近代意义 上的罪刑法定主义。围绕这一原则,更曾展开一场“比附援引”与“罪刑法 定”的论战。笔者的问题意识是:法律转型时期,从比附援引到罪刑法定, 是断裂抑或进化,有怎样的变与不变? 传统法中的比附援引,因为具有类推的性质,不符合近代罪刑法定之要 求,而多被诟病。但如果我们了解传统司法的要求和传统立法的特点,或许 会对比附有“同情的理解”。传统司法要求“引断允协”与“情罪相符”, 前者要求能够援引适当的法条,后者乃追求个案的公正;传统法条以“客观 具体化”与“绝对法定刑”为特征,两者间存在紧张关系。客观具体化的立 法使得法条过于僵硬,难以涵摄具体事实,“法无明文”的情况实际上是司 法中的常态;绝对法定刑与具体问题具体处理这种“实质正义”之间更无法 协调,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比附得以频繁地运用。比附不同于一般的类推 ,它更是一种发现、论证罚则的手段,有很强的创造性。它以“事理相同” 与“情罪一致”作为相似性的基准,在传统立法无法取得突破的情况下,去 发现、论证法条与罚则。这种判断建立在司法经验之上,并通过审转制度的 完善来加以限制。当然,作为传统“推类”思维的体现,它也有着缺乏形式 化的特征,进而有使刑罚裁量权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危险。 在这场论辩中,力主罪刑法定,抨击比附援引的晚清修律大臣沈家本对 比附态度的转变是法律史上颇有意思的现象。沈家本从学理、实践和制度三 个方面对比附进行批评,就笔者看来,第三个方面最为重要。正是由于对司 法独立的服膺,比附所依附的审转制度已经不符合沈氏所主张的司法独立的 要求,促使其走出废除比附的关键一步。笔者试图对传统中国的比附援引做 出进一步区分,即作为制度的比附与作为方法的比附。前者是沈家本在接受 司法独立观念后所摈弃的,后者则是沈氏编辑《刑案汇览三编》时所推崇的 ,两者并不在一个层面上。沈家本提倡法律的职业化,试图将近代罪刑法定 的种子,种植于司法独立的土壤里,这些努力,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有其先 进的意义。 不可否认,以“断罪引律令”为代表的传统法的确存在着法定主义的倾 向,不过从其政治功能上看,体现的是人主对司法的控制,而缺乏人权保障 的因素,加之传统实质主义的犯罪观之影响,传统中国的“罪刑法定’’关 注的是“此罪/罚”与“彼罪/罚”的区别。这与近代意义上罪刑法定以保 障人权为基石,并发展出系统的犯罪成立要素理论,侧重于“有罪”与“无 罪”的判断,有着相当的不同。民初大理院刑事判决例和解释例所反映的, 即是大理院的推事和总检察厅的检察官,试图以近代刑法形式主义的犯罪概 念,取代传统中国实质主义的犯罪观,从而实现近代罪刑法定主义的本土化 。在法律智识已经可以解决罪与非罪问题的同时,根植于传统的心理意识如 何在法律功能、法律责任认识上完成单一至多元之转化,将是法律近代化更 困难的任务。
作者: 陈新宇 著
简介: 晚清民国是中国法律史上的大变革时代,随着传统中华法系的解体,近代法律体系的建构成为时代迫切之主题。“有其法者尤贵又其人”,法律人是沟通法律规范与社会事实的重要媒介,本书着眼于近代法律人群体,关注了晚清民国时期章宗祥、董康、汪荣宝、瞿同祖、徐道隣、潘汉典等10位被人们遗忘了的法律人,书写他们各自践行的法律故事,还以历史公道,让历史长河中的每一朵浪花都绽放光彩。相对于制度变迁的冰冷无情,他们的故事却有血有肉,见证了法治中国的百年历程。